月黑风高夜,镇北王员外家后院的马厩里,张三哆嗦着往手心啐了口唾沫。油灯把马槽影子拉得老长,骡子突然打了个响鼻,惊得他后脖颈汗毛倒竖。"三姨太这遭忒险了……"他嘟囔着把草料叉往墙根一杵,破草鞋碾过青石板的声响在寂静里格外刺耳。
三更梆子刚敲过,西厢房窗纸突然透出暖黄。张三贴着墙根溜到海棠树下,鼻尖萦绕着三姨太身上那股桂花油香。窗棂吱呀开了条缝,递出半截水红绢帕,"快些个!"帕子角让月光照得透亮,晃得张三心跳如擂鼓。
"我的姑奶奶,这要让人瞧见……"话没说完就让帕子捂了嘴。三姨太斜睨着他,眼波流转间带着钩子:"老爷今夜里宿在城南庄子上,你且把心揣肚里。"说着反手带上窗,簌簌衣料摩擦声里混着银镯子脆响。
烛芯毕剥炸了个灯花,张三盯着三姨太卸簪环的侧影,喉结上下滚动。铜镜里映出她脖颈处一点朱砂痣,红得瘆人。"前日太太赏的茯苓饼,我藏了些在灶膛……"他摸出油纸包,饼屑簌簌落在锦被上。
"没出息的样儿。"三姨太嗔笑着拍他手背,腕上翡翠镯子撞在银钏上叮当作响。烛泪在铜烛台上堆成小山,突然"当啷"一声,窗棂让石子砸得直颤。张三蹦起来就往后窗窜,却让三姨太扯住腰带拽回床上。
"老爷回来了!"前院灯笼光映得窗纸发白,脚步声杂沓如骤雨。三姨太反手将绣鞋塞进床底,指甲掐进张三胳膊:"躲好了别出声!"床板吱呀掀起时,张三瞥见床下有团黄布包裹,露着半截乌木牌位。
王员外踹门的动静震得房梁落灰,三姨太裹着薄绸迎上去,鬓边金步摇簌簌发抖:"老爷怎的这时候……"
"太太遣人送信,说你不守妇道!"王员外举起信笺,火漆印泥簌簌直掉。张三缩在床底,闻着陈年檀香味里混着新漆气息,后腰硌着个硬物——竟是半块玉佩,雕着狰狞鬼面。
"定是有人要害我!"三姨太哭倒在拔步床上,钗环撞得床头柜咣咣响。王员外突然掀起床幔,张三屏住呼吸,听见自己心跳震得耳膜发疼。床底玉佩突然发烫,照得鬼面纹路泛青。
"这床何时换了?"王员外突然盯着床腿,新漆色与旧木纹格格不入。三姨太刚要开口,西厢房突然传来凄厉猫叫,接着是摔碎瓷器的脆响。
"我去看看。"王员外转身刹那,张三看见他后颈贴着黄符,朱砂符咒歪歪扭扭画着赦令二字。三姨太迅速摸出床底包裹,乌木牌位"当"地掉在地上,露出背面刻的"王氏列祖列宗"。

"快找!"前院传来家丁举火把的吆喝。三姨太把牌位往床底一塞,突然抓住张三手腕:"你可知老爷为何娶我?"她指尖发凉,张三盯着她突然泛红的眼角,想起马厩里那匹总在月圆夜嘶鸣的枣红马。
"三年前他续弦,迎亲队伍经过乱葬岗……"三姨太声音发颤,窗外月光突然大亮,照得她脖颈朱砂痣渗出细密血珠。床底玉佩开始嗡鸣,张三觉得后颈汗毛根根竖起。
"太太是晌午没的。"三姨太突然贴近他耳畔,吐气如兰,"她咽气前,在我手心画了道符。"床板突然剧烈震动,王员外怒吼声由远及近:"给我翻!连耗子洞都别放过!"
张三摸到床底另有夹层,刚掀开块青砖,三姨太突然拽他胳膊:"别动祖宗牌位!"她声音尖利得刺耳,张三瞥见夹层里躺着本褪色账册,封皮用朱砂写着"丙申年七月十五"。
"找到了!"家丁破门而入的瞬间,三姨太突然翻身压住张三,水红寝衣扫落烛台。火苗窜上床幔时,她嘴角勾起诡异弧度:"该醒了,张家三郎。"
烈火熊熊中,张三看见三姨太脖颈朱砂痣绽成血花,王员外举着黄符冲进来,符纸无风自燃。床底玉佩突然发出凄厉长啸,震得房梁瓦片簌簌坠落。张三最后看见的是三姨太消失在火场中的背影,和她手腕新添的淤青——分明是被鬼面玉佩烙伤的痕迹。
浓烟呛得张三直咳嗽,后脖颈让火舌燎得生疼。他摸索着摸到床腿,正撞见王员外举着黄符念咒,那符纸上的朱砂纹路竟泛着绿光。"孽畜还不现形!"王员外突然将符纸拍向火堆,霎时腾起冲天绿焰。
张三抄起掉落的铜烛台就往窗棂砸,玻璃碴子迸得满屋都是。三姨太的惊呼声混在火海里:"别管我!快带着账册走!"他这才想起夹层里的物件,摸出来时被滚烫的房梁砸中肩膀。
"他跑不了!"王员外突然扯开衣襟,胸口纹着个滴血骷髅,咒文顺着纹路流淌。张三踉跄着撞开后窗,冷月当空照得后院亮如白昼,马厩方向传来枣红马嘶鸣,声调凄厉得像是哭丧。
"驾!"张三纵身跃上马背,账册塞进怀里跟揣了块烙铁似的。王员外家养的三条黑犬狂吠着追上来,马蹄声惊起打更人铜锣翻倒。"捉贼啊!"更夫沙哑的吆喝声里,张三伏在马背上,闻见血腥气越来越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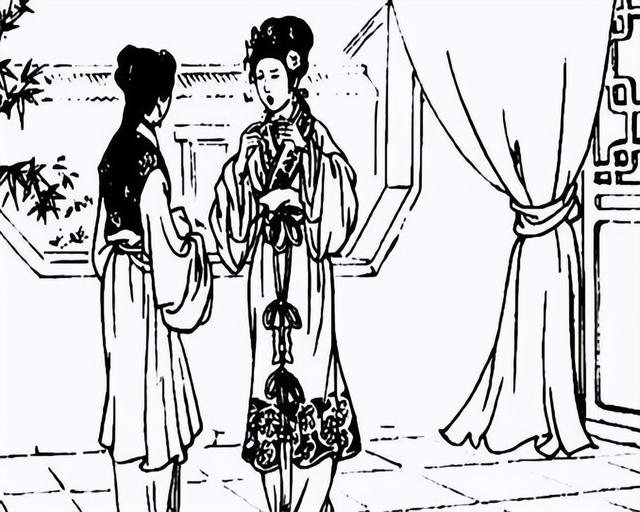
枣红马鬃毛突然炸开,四蹄翻飞如踏风火轮。张三回头望去,王员外家屋顶腾起丈许高的绿火,映得半边天都是瘆人的惨绿。怀里的账册突然发烫,他扯开系带瞥见扉页写着"七月十五子时生人",墨迹猩红如新血。
"往东!"马儿突然人立而起,前蹄指着乱葬岗方向。张三想起三姨太临别的话,后脊梁骨窜起股寒气。乱葬岗的野狗群突然齐声嗥叫,惊飞满林乌鸦,马儿驮着他直冲进坟茔圈子。
"吁——"缰绳勒住时,马儿前蹄正踩在某个土包上。张三举着火折子细看,碑文竟让黑血糊得严严实实。怀里的账册突然掉到地上,夜风翻开泛黄纸页,露出张泛潮的生辰八字。
"丙申年七月十五子时……"张三突然打了个寒颤,这八字竟与他同村早夭的堂弟一般无二。马儿突然咬住他衣角往碑后拽,露出的土坑里,半截绣鞋露着水红缎面——正是三姨太今夜的鞋色。
"谁在那儿?"巡夜的更夫举着火把逼近。马儿长嘶一声,叼着账册就往林子里钻。张三追着马儿踩过荒草,突然脚下一空,跌进个青砖暗道。火把照亮的墙上,密密麻麻刻着人名,最新一道刻痕还渗着血珠。
暗道尽头是间石室,供着尊无头菩萨。马儿把账册放在供桌上,用蹄子翻开其中一页。张三借着火光看去,王员外的大名赫然在列,后面跟着"贪银三千两,溺毙女婴二人"的血字。
"原来是这遭!"张三突然想起三年前王员外续弦,迎亲队伍经过乱葬岗时,确有个女婴的哭声。当时王员外命人挖出坟茔,说是不祥之物,后来那女婴再没人见过。
马儿突然用脑袋顶开暗格,露出个檀木匣子。匣中玉佩与床底捡到的那块严丝合缝,合璧处雕着狰狞的阴阳鱼。张三刚碰到玉佩,石室突然剧烈震动,供桌上的长明灯齐刷刷熄灭。
"王家祖训,得玉佩者承孽债。"阴恻恻的笑声从暗处传来,更夫举着火把探进头来,火光映得他半张脸血肉模糊。张三抄起玉佩就往他脸上砸,触手却是温热的人皮。
"三姨太?"张三倒退着撞上供桌,烛台翻倒点燃帷幔。浓烟中走出个披头散发的妇人,水红衫子渗着血迹,正是三姨太的模样。她脖颈的朱砂痣烂成个血窟窿,手里攥着半截黄符。
"你看见我娘了吗?"三姨太突然换成少女嗓音,说话间露出尖利的獠牙。张三想起账册里夹着张泛黄画像,画上的妇人抱着女婴,背后正是乱葬岗的碑林。
"你娘是当年那个女婴?"张三话没说完,石室突然塌陷。马儿驮着他冲出火场时,天已微亮,中秋的圆月亮得瘆人。怀里的账册突然化作黄纸灰,飘进乱葬岗的晨雾里。

王员外家此时乱作一团,下人们说看见三姨太的鬼魂在火场跳舞。张三躲在马厩给伤口敷草灰,突然听见枣红马打响鼻,喷出的气息带着新坟的土腥。
"三更时,西角门。"马儿用蹄子刨开干草,露出半截银镯子。张三认得那是三姨太常戴的款式,镯心刻着"王氏女婉君"五个小字。
夜色再次降临时,张三裹着蓑衣蹲在西角门。更鼓敲过三巡,雾气里走来个穿水红衫子的身影,手腕银镯叮当作响。他刚要开口,那人突然转身,露出和王员外一模一样的滴血骷髅纹。
"好侄儿,跟叔公还躲猫猫呢?"王员外狞笑着逼近,身后跟着举火把的家丁。张三转身要跑,却让三姨太的鬼魂拦住去路,她脖颈的血窟窿里往外爬蛆虫。
"账册在哪儿?"王员外突然扯开衣襟,胸口咒文流出血泪。张三摸出怀里的阴阳玉佩,玉面突然映出当年场景——王员外命人将女婴按进尿罐,血水渗进乱葬岗的黄土。
"原来是你害死我娘!"三姨太的鬼魂突然扑向王员外,银镯化作利刃插进他咽喉。王员外惨叫着往火堆里滚,咒文在烈火中发出尖啸。
张三举起玉佩,阴阳鱼在月光下转成金色。乱葬岗的坟茔突然裂开,当年被溺毙的女婴魂魄纷纷飞出,围着王员外家盘旋。晨鸡报晓时,王家的宅院塌成废墟,只余那尊无头菩萨立在焦土上。
"三姨太……"张三在废墟里找到半截水红衫子,袖口的针脚密匝匝绣着"婉君"二字。马儿驮着他往村口去时,晨雾里传来婴儿啼哭,像极了账册上记载的那个生辰八字。
后来人说,每逢七月十五,乱葬岗的碑林就会传出纺车声。有胆大的后生去瞧,月光下总有个穿水红衫子的女人,抱着银镯子坐在坟头上哭,脚边卧着匹枣红马,鬃毛白得跟雪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