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不得狄更斯的名著《双城记》在我的书架上放了多少年,今年的某一天,当我不经意看到书架上的这本书时,这本书的开篇之语就出现在脑海中,这是一个最美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糟糕的时代。
对于好与坏的理解,总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流逝而有更多的理解。这二年我总是在提时代,提时代性,当好与坏与时代相联时,总会让我有所感慨。可能是某种不经意的感觉,我决定读一下这本《双城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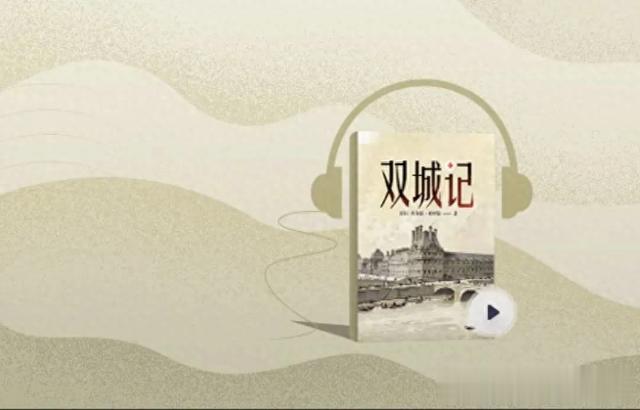
当翻开第一章《时代》时,我发现,狄更斯在开场语中,不止说了一个对比的话,而是说了一连串的反差,而且这种反差是那么的强烈,强烈到如同白天刺眼的太阳,与晚上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样令人印象深刻。然而当我读完《双诚记》后,我能够体会到作者使用这些对比的那种强烈的感情,也能够体会到每一个对比中所包含的力量,在那样的时代,好与坏是如此的极端,以至于他说,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因此,我觉还是有必要引用双城市的开篇第一句话,这句话长达一段: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个睿智的年月,那是个蒙昧的年月;那个信心百倍的时期,那是疑虑重重的时期;那是阳光普照的季节,那是黑暗笼罩的季节;那是充满期望的春天,那是让人绝望的冬天;我们面前无所不有,我们面前一无所有;我们大家都在直升天堂,我们大家都在直下地狱——简而言之,那个时代和当今这个时代是如此的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权威们也坚持认为,不管它是好是坏,都只能用“最”来评价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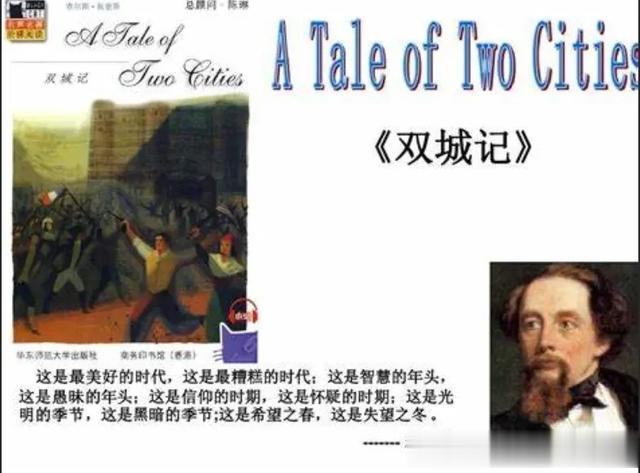
关于双城记的双城,则是英国的伦敦与法国的巴黎。英国于1688年通过光荣革命,建立起了资产阶段的君主立宪制,通过向资产阶段的权力让渡,促进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在英国的发展,伦敦在此后成为世界的中心,享受着工业革命与宪政革命所带来的繁荣与秩序。与此相对应的是,100年后的法国的巴黎,1789年,法王路易十六召开了法国三级国民议会,而这次会议却最终引发了具有深远影响的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在狄更斯的笔下,则成为了与伦敦相对的另一个极端,属于最糟糕的一极,是风暴卷席之地,寒冬光顾之所。

在这样背景下的一个事关二个城市之间生活的一些人的命运,自然就受到这样的环境影响,不论是从大的时代,时期,还是小的某一个季节,都能够体会出世事难料的命运感,会深刻地印在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心中。虽然这些人与我们相隔时代,不过当我们也同样经历着某些相同的时代情景时,就能够理解当时人们的感受,是美好还是糟糕。就如同杜甫在咏怀古迹其二中所言: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当安史之乱后,杜甫飘摇不定,他在此诗中写出了他与宋玉虽相隔千年,时代不同,但萧条相似,自然也就理解了宋玉当时之悲,也就有了杜甫此时千秋之泪。

作者在最后,表达了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美好愿景,并通过“是个女人”表达了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如同中国诗歌中的用典。那是一句著名的句子:“自由啊,多少罪恶是假你的名义干出来的。”
感谢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