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秀才看《千佛名经》,问曰:“百千诸佛,但见其名,未审居何国土?还化物也无?”师曰:“黄鹤楼崔颢题后,秀才还曾题也未?”曰:“未曾。”师曰:“得闲题取一篇好。”
——《五灯会元》第四卷 长沙景岑禅师
 白话直译:
白话直译:张拙秀才看完了《千佛名经》,心中有些疑惑,就来请教长沙景岑:“经中记录了百千诸 佛的名字,却不知道诸佛住在哪里,又都在做些什么呢?”
长沙景岑就问:“崔颢在黄鹤楼题诗之后,你有没有也去题一首呢?”
张拙说:“还没有。”
长沙景岑说:“那有空的时候,你不妨也去题一首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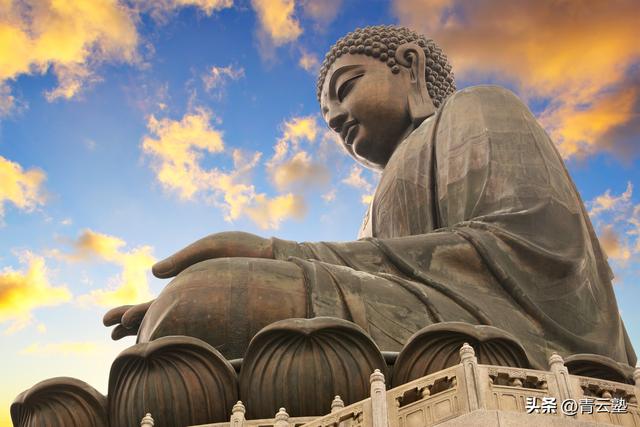 鉴赏评说:
鉴赏评说:张拙是宋初的禅宗居士,曾举秀才,非常爱好佛学,对参禅情有独钟。
他问百千诸 佛在哪里,长沙景岑却只字不提,而是和他聊起了文人雅士最擅长的事情,赏景作诗。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崔颢的那首《黄鹤楼》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就连李白看了也只得留下“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的感叹,搁笔无作而去。
那长沙景岑叫张拙秀才有空也去黄鹤楼题一首诗试试,是在挤兑他还是在故意刁难他呢?

不要错怪长沙景岑的好意了。
黄鹤楼之美景,你去见了就知道;《黄鹤楼》之意境,你去题了就明了。
当浸润在美景之中,提笔抒怀之时,你自然就能体悟百千诸 佛在哪里,又在干什么了!
百千诸佛无处不在,无用不在。一切当下妙用就是佛在化 物,佛 国不在虚无缥缈之处,不在遥不可及之地,就在此时此处,你就是千 佛之国。
佛陀悟道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奇哉!一切众生具有如来智慧德相,但以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人人心里都有一尊佛,佛不在外,就在自己这里!他当然在化物,赏景、题诗不正是吗?
佛 道不在思维里、意识中,而就在当下之用中呈现。

禅 宗不神秘,见 佛不 玄不 圣,其实就是觉知正在生起“身口意”的自己,见自己就是见 佛。
但见 佛不是在故纸堆中,不是在祖师的言句中,而就是当下的行住坐卧之中,当下实践是唯一见佛之路。而脱离当下的知解,都是妄想执着。
因此,对于张拙的问题,长沙景岑只字不提,只是叫他闲暇之余也去黄鹤楼看看,也去题一首诗试试,在“行”中体悟“用”的奇妙,或许就明白了。
百千诸 佛还能在哪里呢?你在,国土在。百千诸 佛还能干些什么呢?在赏景、在题诗,随你闯荡天地之间,无一不是。
见得自己,反观自心后,一切问题就冰消瓦解了。无所得,但却有个歇息之处。

“百千诸 佛但闻名,国土何曾不现成。自是不归 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争。”
在长沙景岑的逼拶之下,张拙秀才有没有去黄鹤楼题诗则不得而知了。只不过,后来在禅月大师贯休的指引下,张拙得缘参谒石霜庆诸禅师。
当石霜问其姓名时,张拙答名拙,石霜反问:“觅巧尚不可得,拙自何来?”张拙由此顿悟,并作偈一首:
“光明寂照遍河沙,凡圣含灵共我家。一念不生全体现,六根才动被云遮。断除烦恼重增病,趋向真如亦是邪。随顺世缘无挂碍,涅槃生死是空华。”
张拙深得石霜庆绪的印可,后成为其法嗣。或许,张拙能在石霜处顿悟,与长沙景岑禅师的这一次机缘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