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人告诉我,买了一套中华书局的简体横排版二十四史,发现错误颇多。
比如《明史·列传第十六》里面的“胡深子伯机”中的“子”在此书就写作了“于”,竖排版的就是“子”。这套简体横排的除了方便易读,价格便宜,其他几乎一无是处啊。

《明史·列传第十六》局部照▲
说起来,啥时候自己又开始喜欢上繁体字了?又是啥时候开始就钟情竖排版了?我也说不清楚啦。
读惯了简体字横排版的友人说:“繁体字加竖排版,读起来太费劲儿,再好看的书都影响阅读兴趣。”“未见得!”我反驳。
“试想想,‘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类似的美篇美句,如果用繁体字和竖排版,是不是更有意境呢?从右到左,心领神会地读;从上到下,点着头地领会。头和目光的移动方向是上下,上下是什么?是点头,是认可。读者与作者的思维像是共通的,那是一种怎样的境界啊!”我继续道。
“倒也是。”友人承认。

诗经《关雎》竖排版▲
笔者认为,繁体字和竖排版的书,并非不好读,不过是一种习惯罢了。
多读几部就习惯了,习惯了就读得轻松、投入、享受。如果有人向你推荐一本你喜欢的作者的新书,内容有特色,写作手法新颖。而你,只因笔画繁复、排版生疏就放弃阅读,那是不是太亏了?
关于简体横版和繁体竖版,无论是学术界还是坊间,总有不少人有话可说。官方统计,二0二三年有将近十五亿人使用汉语汉字,而在海外和港澳台,用繁体和竖版的比例非常大。

竖排版图书▲
汉字距今已有近5000年历史,相传,是由“黄帝时期”的史官仓颉创造而成。
他风餐露宿,来到野外一边观察飞禽走兽的足迹和自然形态,一边拿木棍在地上写写画画,最终发明出原始象形文字。最初,象形字被刻写在兽骨、龟甲等材质上,俗称“甲骨文”。到青铜时代,文字被刻在各种各样的青铜器具上,起到记录历史和装饰的作用,俗称“钟鼎文”。同时期,竹简和木简相继出现,比起青铜,在竹简和木简上刻写文字要容易很多,于是,从商周以后,竹简和木简成为最重要的书写材料。

西周大盂鼎金文书法▲
由于竹简和木简是把竹木制作成宽约1厘米,高约一尺的竹片和木片,中间钻孔用皮绳穿起来,然后在上边刻写文字,一根竹简大约能刻写30字左右,一册竹简大约有80片,能刻写2000字左右,古人通常把竹简卷起来保存,被称作“一卷书”。
古人在竹简或者木简上刻写文字时,通常按照从上到下,从右至左的顺序来写,所以,即使毛笔在战国时期被发明出来,写字工具从刻刀变成毛笔,古人依然延续这个书写习惯。此后,不论经历多少改朝换代,社会如何演变,这个书写习惯未曾变过,一直延续到建国后,才退出历史舞台。

木简版《木兰辞》
顺理成章,延续而下。古人把字写在石头上、树皮上、竹子上、羊皮上,竹简上,从上到下,从右到左,平平仄仄,抑扬顿挫。
直至到五四运动之前,古典小说、文言文、国学经典、坊间信件,几乎全是繁体竖版;离我们不远的民国,如许地山、张爱玲、钱钟书等的作品,以至现代金庸的武侠小说,也多是繁体竖版。用传统的版本读早期的人和事,无论人生哲理还是生活情感,繁体字总觉得生鲜俏皮,内容总觉得更富滋味。

国学经典丛书▲
由于汉字单音节方块字的特殊性,使得形式上“直排”或“横排”都无不可。
“直排”、“横排”的争论主要始于西学东渐,孰优孰劣亦莫衷一是。回到民国那个特定历史时期,赞成“横排”一方如朱我农先生认为,“横排”一“可免墨水污袖”,二“可以安放句读符号”,钱玄同则提出“直排”对于中西文混排的不便。反对“横排”者如胡适则认为如无必要,“直排”亦无不可,且改革起来煞费周章。即在今日,也存在着古籍阅读“直排”优于“横排”的看法。

古代书籍▲
这个书写习惯深刻地影响了排版、印刷等行业,以至于从先秦时期到新中国成立前这2000多年里,人们见到的所有手写体和印刷体,都是竖版排列。
如今,国内一些有情怀的出版社,出版古籍善本时,依然采用竖版形式。实际上,在清朝末年到民国时期,国内出现过一些零星的横排书籍。
中国第一本横版书籍,出自清末学者卢戆章(1854年——1928年)编著的拼音著作《一目了然初阶》。卢戆章是福建厦门同安人,一生潜心研究汉字拼音,用毕生所学,创制中国切音新字,被誉为“中国文字改革的先驱”。他的《一目了然初阶》一书于1892年由厦门“五崎顶倍文斋”刊印后,直接拉开了“汉字拼音化改革”的序幕。

横排版《一目了然初阶》▲
中国第一本横版期刊《科学》杂志,是一群留学生在1915年创办,发起人共有9人,分别是任鸿隽、胡达、赵元任、周仁、秉志、章元善、过探先、金邦正、杨铨。
这些人留学欧美,思想新潮,没有传统束缚,并且,期刊的内容介绍的全是自然科学,所以,就理所当然喜采用了当时全球流行的横版排列和新式标点。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锋,在1919 年1 月创刊《北京大学日刊》时,也采用了横版排列。此时,横版排列的书刊虽然形成一定气候,但对于习惯了竖版排列的中国人来说,阅读起来有一定障碍。

《北京大学日刊》▲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在《北京大学日刊》创刊号上刊登了一则《蔡元培启示》,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月刊形式已由研究所主任会议公决,全用横行,并加句读、问、命登记号。但诸先生中,亦有以吾国旧体文字形式一改兴趣全失为言者,鄙人亦以为然。唯一册之中,半用横行,自左而右,半用直行,自右而左,则大不便于读者。今与诸先生约,凡科学性质之文,皆用横行,送各研究所编入普通月刊;其文学性质之文,有不能不用直行式者,请送至校长室,由鄙人编辑为临时增刊。
可以看出,在这个新旧思想文化相互碰撞的时代,横版排列要想得到大部分人的认同,还需要走很长的路。

《注释校正华英四书》▲
直到建国后,书籍报刊究竟改用横版排列,还是坚持竖版排列?学术界对此一直争论不休,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
1955 年元旦,《光明日报》破天荒发行了全国第一份左起横排的报纸。收到《光明日报》的老订户们突然发现,熟悉的报纸怎么一下子变成了这个样子,昨天的文字还是竖立,今天怎么就变成了横行?
这样一来,看报纸的状态和兴趣也不得不改变。过去,报纸是竖版排列,人们读报纸时,自上而下地换行读报纸的过程,如同一边读一边点头,现在可倒好,横排的报纸让人从左到右换行看报时,如同一边读报一边摇头。
用苦良心的《光明日报》为了消除读者的顾虑,还刊登了一篇题为《为本报改为横排告读者》的文章,说道: 我们认为现代中国报刊书籍的排版方式,应该跟着现代文化的发展和它的需要而改变,应该跟着人们生活习惯的改变而改变。中国文字的横排横写,是发展趋势。

《为本报改为横排告读者》▲
看到《光明日报》成为国内第一个吃螃蟹的报刊,郭沫若、胡愈之等学者即刻撰文造势,并指出文字横排的科学性。
他们指出:人的双眼横着长,视线横看比竖看要宽,阅读时眼和头部转动较小,自然要省力,不易疲劳。横版对各种数理化公式和外国的人名、地名排写起来也较方便,同时还能提高纸张的利用率。
《光明日报》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地位跟前苏联的《消息报》类似,当时,《消息报》的排版采用国际通用的横列,苏联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很大,我们又跟苏联走得很近,所以,就照搬了《消息报》的排版。1955 年10 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明确”提出: 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和有关部门进一步推广报纸、图书、杂志的横排。建议国家机关、部队、学校、人民团体推广公文的横排、横写。

1955 年元旦,《光明日报》改版▲
简体横版和繁体竖版,在华人世界是通用的,香港出版界也并非都用竖版,但是普遍繁体。
有一个现象,无论习惯什么版本,一到写毛笔字,很多人就直奔传统,那是定型的历史,好玩,有趣,有意境。
有一份繁体字竖排版的《紫禁城》月刊,笔者每年必订,每月必读。当一本实体书刊捧在手上,当纸张一页页在指尖翻过,当纸和墨散发出芬芳,触觉、嗅觉、视觉都有了。像砖块样的象形字和形声字,自上而下,堆砌成一道道的文墙,好像有事件跃然纸上,好像有声音破纸而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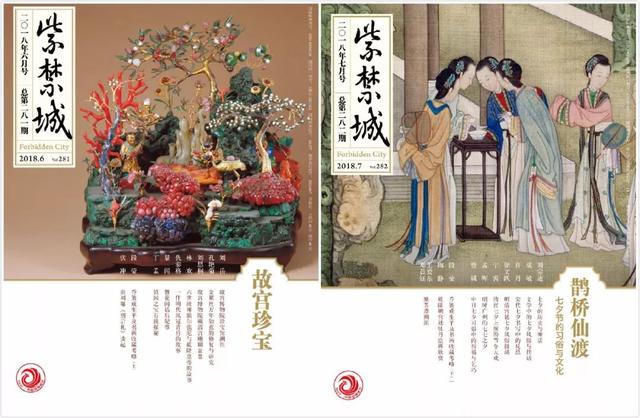
《紫禁城》杂志▲
电脑早已开发出繁转简和简转繁的软件,非常方便,但是转来转去,倒是闹出不少笑话。
转错了是很离谱的。语言学家们正在集思广益地探讨这个问题吧?若干年后,汉语的书写形式会统一吗?怎么统一?
《书海寻珍▪七律》——佚名
静倚轩窗沐晓风,群书博览意无穷。
华章字句藏真智,古典篇章蕴妙聪。
增慧修心知世事,启思养性悟尘空。
墨香常伴心常醉,万卷诗书写大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