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说(667年-730年),字道济,唐代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洛阳(今河南洛阳)人。他历仕武则天、中宗、睿宗、玄宗四朝,官至中书令,封燕国公,是开元盛世的重要缔造者之一,史称其“三次为相,执掌文坛三十年”!
一、家世与早年:从寒门到科举巅峰
张说生于洛阳寒门,祖辈无显宦记载,其父张骘仅为县丞。他自幼聪颖,17岁参加洛阳科举,以《对策天下第一》震动朝野。
武则天亲自召见,赞其“儒者之英”,授太子校书郎。这一时期,他结识张柬之、宋之问等文人,形成早期政治网络。值得注意的是,他虽在武周政权下崛起,却始终保持李唐正统观念,这为其后来参与神龙政变埋下伏笔。

二、政治沉浮录:四朝老臣的权力博弈
1. 武周时期的刚直(690-705)
任凤阁舍人期间,因拒绝配合张昌宗构陷魏元忠,被流放钦州(今广西)。流放途中写下《岭南送使》,诗中“瘴江西去火为山,炎徼南穷鬼作关”展现其不屈气节。这段经历使其在士林中赢得“铁骨御史”之誉。
2. 中宗、睿宗时期的权谋(705-712)
神龙政变后,他秘密联络太平公主,助睿宗复位,官拜中书侍郎。景云二年(711),提出“罢斜封官”政策,一次性裁撤通过贿赂获官的数千人,引发既得利益集团反扑,最终被贬为尚书左丞。
3. 玄宗朝的三起三落(712-730)
①开元元年(713)首次拜相:助玄宗铲除太平公主集团,获封燕国公。主持编纂《大唐开元礼》,确立国家礼制体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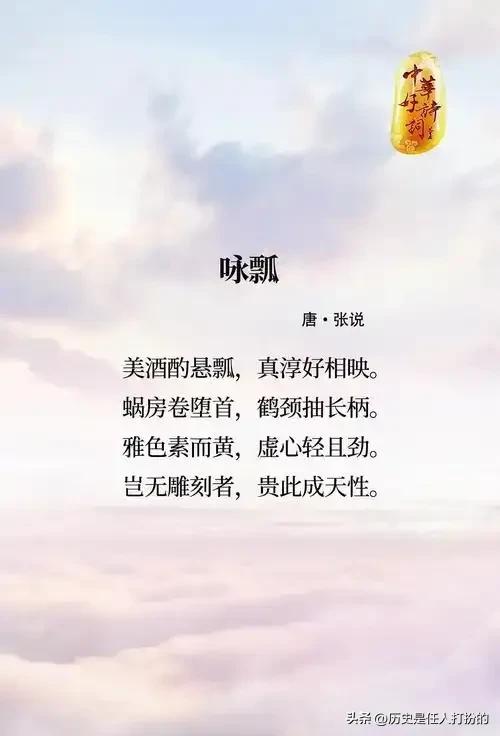
②开元九年(721)二度为相:推行“长征健儿”募兵制,将府兵制下60万兵力缩减至20万职业军,年省军费200万缗。该政策引发边将反弹,安史之乱后被认为削弱了中央对藩镇的控制。
③开元十三年(725)三任中书令:主导泰山封禅大典,创制《封禅坛颂》,确立玄宗“奉天承运”的合法性。但其主张的“广建佛寺”政策,导致寺院经济膨胀,为后期土地兼并埋下隐患。
三、文学改革:从骈俪到雄浑的盛唐先声
作为“燕许大手笔”(与许国公苏颋并称),张说扭转初唐浮华文风,其碑志铭颂雄浑质朴,如《起义堂颂》展现家国情怀。
他提携后进,王湾“海日生残夜”之句得其亲题政事堂,推动盛唐诗歌革新。其边塞诗《邺都引》慷慨悲壮,开高适、岑参先声。
1. 文体革新
针对初唐“上官体”的绮靡文风,提出“崇雅黜浮,气格雄浑”主张。其《洛州张司马集序》系统阐述文学观,强调“文章之道,关乎政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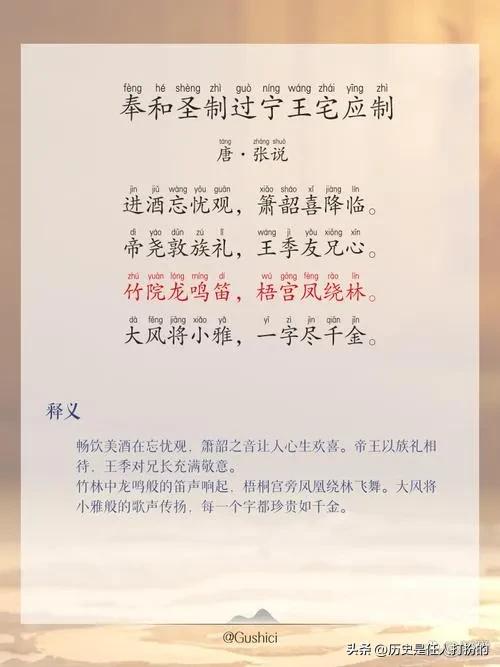
主持编修《三教珠英》时,刻意删减浮华辞藻,收录王勃《滕王阁序》等雄健之作。
2. 诗歌创作
①边塞诗:如《巡边河北作》中“寒沙逐风起,春花犯雪开”,突破宫体诗局限,启高适、岑参之先河。
②贬谪诗:岳州时期的《送梁六自洞庭山作》,以“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开创唐人贬谪诗中的山水寄托传统。
③其《邺都引》被明代胡应麟评为“声调气势,与王勃《滕王阁》并驱”。
3. 文化工程
主持编修《大唐开元礼》《唐六典》,其中《唐六典》首创以职官为纲的典章体例,日本《养老令》、朝鲜《经国大典》皆受其影响。

四、军事战略:职业化军队的奠基者
任朔方节度使期间,张说亲率轻骑巡视边塞,首创“长征健儿”职业化边军。他巧妙分化突厥、契丹势力,以“和亲不过暂安”的务实外交确保边疆稳定。安史之乱前夜,其军事改革为唐王朝积蓄了最后的力量。
1. 边防体系重构
将原有的“行军总管-都督府”体系改为节度使制度,在朔方节度使任上设立“军-城-守捉”三级防御体系。天宝年间十大节度使的雏形即源于此。
2. 胡将任用争议
主张“以夷制夷”,提拔安禄山为捉生将,史载其曾预言安“貌有反相”,但认为“陛下待以厚恩,必无异志”。这一矛盾态度成为后世争论焦点。
3. 军事理论著述
所著《论幽州边事书》提出“三策论”:上策离间、中策威慑、下策征伐,被李靖收入《卫公兵法》注本。

五、历史争议:毁誉参半的改革者
司马光评其“尚通”,既指其政治智慧,亦暗喻其圆融性格。《新唐书》称“朝廷大述作多出其手”,其撰写的《唐六典》开创古代行政法典先河。
作为从初唐向盛唐转型的关键人物,张说以文治武功铺就了开元盛世的基石,其人生命运恰似大唐国运的缩影——在理想与现实间跌宕,终成一代名相风范。
1. 正面评价
①宋代司马光赞其“文武兼资,开元名相之首”。

②明代王世贞称“燕公之文,如金钟大镛,盛世之音”。
2. 负面批评
①《旧唐书》指其“喜排异己,时论颇讥其躁”。
②清人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批判募兵制“启藩镇割据之端”。
3. 现代重估
当代学者傅璇琮指出,张说的“文学官僚集团”实际架空了传统门阀,为寒门士子开辟上升通道,这一社会结构变革比其具体政策影响更为深远。
六、家族传承与历史遗存
①子嗣:次子张均为玄宗驸马,安史之乱中投降伪燕政权,导致张说家族声望受损。

②墓葬:洛阳出土的《张说墓志》由玄宗亲撰,提及“卿有三绝:曰德、曰忠、曰文”。
③文化符号:敦煌莫高窟第217窟壁画中的“宰相礼佛图”,据考绘有张说形象。
总结:张说的一生恰似盛唐的微缩史诗——既有“裁减冗兵”的果决,也有“提拔胡将”的失误;既是文学革新的旗手,又是权力游戏的玩家。
他的复杂性,正是开元盛世在制度转型期多重张力的真实投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