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人物年龄的复杂甚至错迕,既与创作和流传过程有关,也与作者写作技巧特别是叙时策略有关。前一方面,学界研究较多,后一方面似乎还未引起足够重视。笔者尝试进行探索。[1]

剪纸林黛玉
拙文试以林黛玉的年龄提升为例说明之,以就正于方家。

作为小说人物的林黛玉,其年龄自然决定于作者的叙事设计。也就是以第1回石头化身通灵宝玉随同贾宝玉降生为一岁起始的年龄记事叙时系统,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专编《红楼纪历》一章,按贾宝玉年岁排比书中所记人物年龄事件。但他只强调书中年龄记事“井然不紊”“若合符契”的一面。
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在此基础上列《新编红楼纪历》一节,补充了周氏《纪历》中掩盖的小说中人物年龄记事中矛盾错乱内容,使得这一年龄记事系统的面貌能够比较完整地呈现出来。[2]
由于这一年龄系统初见于脂批《石头记》,并以石头记事的方式叙述故事。故可称为石头记事系统,或《石头记》年龄系统。
在此系统中,林黛玉比贾宝玉小一岁。林黛玉的出场年龄是第2回交代的。五岁延师启蒙,六岁丧母。她与贾宝玉的年龄差,在第3回由黛玉口中说出:“这位哥哥比我大一岁。”
依据第2回冷子兴对贾宝玉当时年龄(七八岁)的叙述,可知丧母后因外祖母疼爱由贾雨村护送进京时的黛玉年龄约六七岁。
自第17至18回元妃省亲,直到第53回贾府除夕祭祖,是石头记事第十三年,即贾宝玉十三岁之年。
第25回描写癞头和尚为贾宝玉治病,手擎通灵宝玉,“长叹一声道:‘青埂峰一别,展眼已过十三载矣。人世光阴,如此迅速,尘缘满日,若似弹指。可羡你当时的那段好处:天不拘兮地不羁,心头无喜亦无悲。却因锻炼通灵后,便向人间惹是非。……”

改琦绘通灵宝玉、绛珠仙草
这是贾宝玉年龄记事的最权威最明确的信息,也是石头记事的年龄系统的基本依据。梦稿本、俄藏本作“十五载”。但因为“十三载”与第23回叙贾宝玉“四时诗”,人们“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一句(诸本同)相合,所以多被肯定。
依据这个年龄系统,可以推知十五岁的薛宝钗(第22回)比宝玉大二岁,比黛玉大三岁。以此,比宝玉小一岁的林黛玉年龄自然是十二岁。
林黛玉的年龄提升出现在《红楼梦》第45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黛玉向宝钗倾吐肺腑之时:
你素日待人,固然是极好的,然我最是个多心的人,只当你心里藏奸。从前日你说看杂书不好,又劝我那些好话,竟大感激你。往日竟是我错了,实在误到如今。细细算来,我母亲去世的早,又无姊妹兄弟,我长了今年十五岁,竟没一个人像你前日的话教导我……[3]
由黛玉自己口中说出的年龄信息“我长了今年十五岁”,是很清晰的。这句话,现存脂本程本全都相同,庚辰本还有双行批:“黛玉才十五岁,记清。”[4]

戴敦邦绘《金兰契互剖金兰语》
但学界似乎并不认同这个年龄,大多仍依《石头记》年龄系统认定为十二岁。
清苕溪渔隐《痴人说梦》(镌石订疑)说:(我今年长了十五岁)“应改十二”。姚燮《读红楼梦纲领》:“四十五回黛玉云我今年十五岁,当作十四岁为是。”不知何据。[5]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红楼纪历》推论:“黛玉云‘我长了今年十五岁’,按黛玉小宝玉一岁,实当十二岁。所叙明明不合,疑字有讹误,或后人嫌小,妄改为五。”[6]
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此处批曰:“黛玉此处所报年龄似误,诸本皆然。脂砚斋亦未察觉,庚辰夹批云;‘黛玉才十五岁,记清。’或因作者多次修改,此处疏漏。……此类文本矛盾,可作文本成书研究之重要线索。”[7]
在小说贾宝玉十三岁的年龄叙时系统中,出现了比宝玉小一岁的黛玉自称“我今年长了十五岁”。这当然不是小说人物黛玉的自述错误,而是文本叙时的错误。
但“诸本皆然”的文本信息,特别是庚辰脂批又明确告知读者,这又绝不是流传过程的传抄错误,它来自作者自己的修改。也就是说,到第45回,曹雪芹有意识地把林黛玉的年龄提升了三岁。
这种修改,使林黛玉的年龄脱离了石头记事的年龄系统。其结果,是使黛玉的年龄反大于宝玉二岁,而与原来比她大三岁的薛宝钗同龄。
于是,文本中的叙时系统的混乱就发生了。并且不止于此。

《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4月版。
第49回叙薛宝琴、邢岫烟、李纹、李绮来到贾府进入大观园后,
此时大观园比先更热闹了多少,李纨为首,余者迎春、探春、惜春、宝钗、黛玉、湘云、李纹、李绮、宝琴、邢岫烟,再添上凤姐儿和宝玉,一共十三个。叙起年庚,除李纨年纪最长,他十二个人皆不过十五六七岁。或有这三个同年,或有那五个共岁,或有这两个同月同日,那两个同刻同时,所差者大半是时刻月份而已。连他们自己也不能细细分晰,不过是“弟”“兄”“姊”“妹”四个字随便乱叫。
这里凤姐年龄明显失误,程高本改为“叙起年庚,李纨年纪最长,凤姐次之,余者皆不过十五六七岁。”但它仍与石头记事的年龄系统明显不合。
周汝昌《红楼纪历》指出:“按本年宝玉十三岁,凡小于宝玉者不能超过十三岁。……此为信笔泛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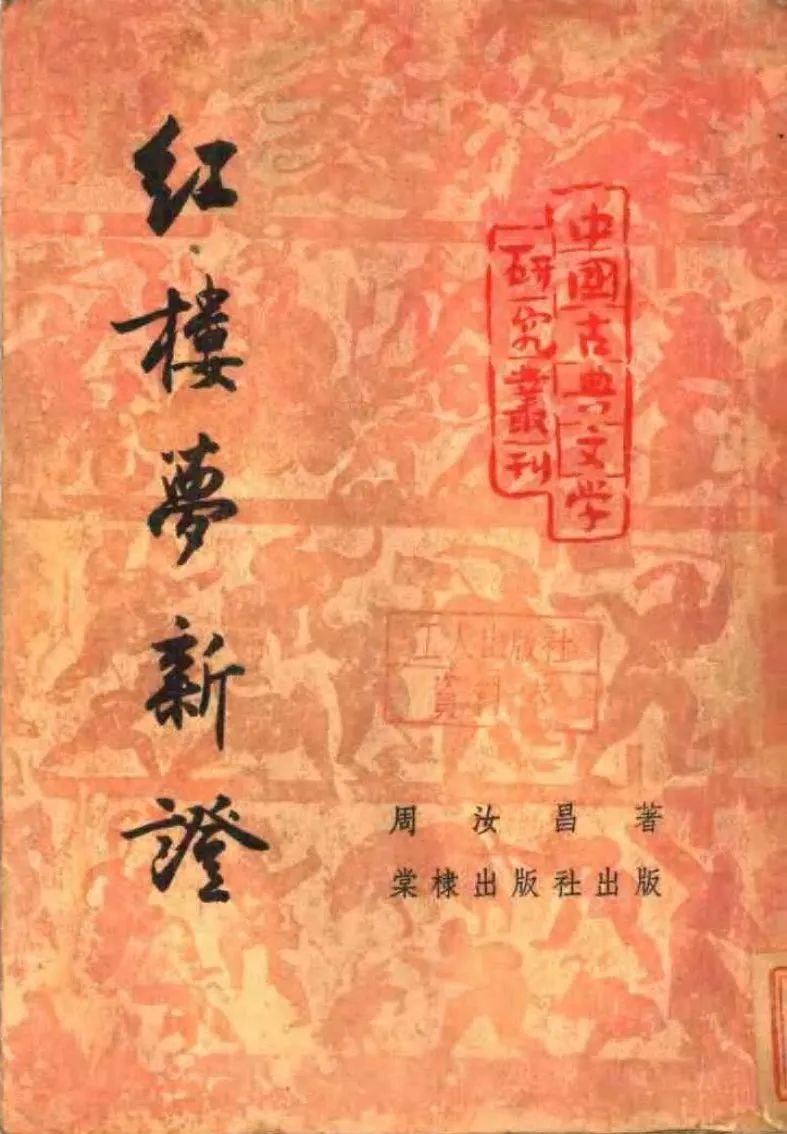
《红楼梦新证》
按这段叙事文字,贾宝玉的年龄也至少要提升三岁,才能把比他小的湘云探春惜春等纳入“十五六七岁”的年龄系统。
不过它又未必是“信笔泛叙”。此回有庚辰总批:“此回系大观园十二正钗之文。”这里说的“十二正钗”,虽然并不全同于十二钗“正册”,但确实是当时能够享受大观园青春美好生活的贵族及其亲属女子,正是他们的集合把大观园的欢乐推向了高潮。
所以这一段关于年龄的概述文字不可认定为“信笔泛叙”,应该是作者为这个短暂的青春乐园设定的年龄边界。“十五六七岁”,越过这条边界,就要进入浊臭的成人世界了。
沈治钧就此指出:“此处又能合于四十五回黛玉‘十五岁’之说”,并且认为“这显然是以大观园故事为核心的新稿《金陵十二钗》的年龄系统,它与今本(按:指《红楼梦》)的时间体系纠缠在一起,自然会现出种种破绽。”[8]
笔者很认同沈先生关于第45回、49回掺入“以大观园故事为核心的年龄系统”的看法。只是觉得这个年龄系统应该更早出现于明义所见《红楼梦》文本,即《红楼梦》初稿,而不是《金陵十二钗》增删稿。
笔者曾著文论述指出,据明义《题红楼梦》绝句二十首所反映的内容,他所见到的“曹子雪芹出所撰《红楼梦》一书”,“是不同于脂本《石头记》的文本,它是曹雪芹早期作为创作基础所写的一个稿本,我们可以称之为《红楼梦》初稿。《红楼梦》初稿的主体故事,是以大观园为主要环境的宝黛钗爱情婚姻故事,以及相关的正副“金钗’的故事。”
虽然现在我们无法找到文本依据,但明义题诗及学者研究成果大体可以证实这一判断。其七云:“红楼春梦好模糊,不记金钗正幅(副?)图。往事风流真一瞬,题诗赢得静功夫。”说明《红楼梦》初稿已有今小说第5回“正幅(副)金钗图”册之梦。也许庚辰批所云“十二正钗”就是今本第49回除宝玉外的十二人。

《明义题红诗研究》
又其十七云:“锦衣公子茁兰芽,红粉佳人未破瓜。少小不妨同室榻,梦魂多个帐儿纱。”笔者认为是写宝黛的。也有认为是写宝钗或晴雯的。不管是谁,年龄信息是很清晰的。
古代称女子十六岁为“破瓜”之年,又隐喻女子初次性事。晋孙绰《情人碧玉歌》:“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 “未破瓜”即不到十六岁,也未有男女性事。这是明确点明其所见《红楼梦》初稿中的大观园群体包括黛玉的年龄界线。也许就是第45回黛玉“我今年长了十五岁”之所本。[9]
故本文仍采取黛玉年龄提升可能系《红楼梦》初稿年龄系统掺入的推断。但同意沈先生认可大观园“金钗”年龄系统的观点。
所以,不论来源如何,有一点是很清楚而确定的:林黛玉年龄提升不是孤立事件,而是大观园“金钗”年龄系统掺入石头记事年龄系统的重要标志。

问题来了:曹雪芹为什么要掺入另一个年龄系统导致年龄叙时的错乱?又为什么选定在第45回给林黛玉添岁作为这种掺入的起点和标志呢?

《曹寅与曹雪芹》(增订本),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在此之前,石头记事的年龄叙时系统不是没有被打乱过。由于《风月宝鉴》旧稿的掺入所致,出现了大小宝玉的问题,出现了秦氏姐弟的问题,以及薛宝钗进府时间及年龄问题等。这些都已经有学者专文探讨。
大观园“金钗”年龄系统的掺入,也有沈治钧等人研究。但为何以提升黛玉年龄为掺入节点,其意义何在,似乎还需要有进一步的思考。
熟读《红楼梦》的人们发现,在石头记事的贾宝玉年龄系统中,有一个最大的年龄叙事板块。这就是贾宝玉十三岁的一年。
它以元春省亲的第17至18回为起点,至第53回贾府除夕祭祖。共计约三十六回(实为三十五回半)。其篇幅,约占全书三分之一,占曹雪芹亲自定稿的前八十回近一半。依《红楼纪历》,前八十回共计写了贾宝玉降生至十五岁,共十五年,十三岁就写了近一半。
这显然是一种特殊的匠心经营。而提升林黛玉年龄的第45回,以及随之掺入大观园“金钗”年龄系统的第49回,恰恰就在这个巨大板块中。
这可能为我们寻找答案提供线索。
曹雪芹为什么用前八十回近一半篇幅写贾宝玉十三岁一年?显然是因为小说主人公的这个年岁具有某种特殊意义。
我们否定“自传说”,但却无法否定小说的某种自叙传性质。“甄真假贾”的符号设计就是为了传达作者的自叙意图。

《从曹学到红学》,刘上生著,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4月版。
小说第56回写甄宝玉十三岁,比时已十四岁的贾宝玉小一岁,第74回探春说江南甄家已被抄家,这年甄宝玉十四岁。如果江南甄家即隐江宁曹家,“贾(假)”又是“甄(真)”的影子,而雍正六年(1728)曹家被抄正值出生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的曹霑(雪芹)十四岁之年。那么,曾经经历过“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第1回)的曹雪芹对贾宝玉十三岁这一年的“末世之盛”大写特写也就完全不奇怪了。
这是《红楼梦》家族盛衰史主题的特笔,也是作者重要创作情结——怀旧情结的集中表现。如果我们可以用“家事”和“情事”来概括小说的基本内容,那么,贾宝玉十三岁这一年的36回板块的基本构思,就是以家事为主体,以家事包含情事。
就家事即盛衰史一面而言,它着力铺叙贾府末世“烈火烹油鲜花着锦”之盛,描写了元宵省亲、端节打醮、游大观园、除夕祭祖等大场面,至第54回下一个元宵,王熙凤说笑话,多次用“散了”隐喻“盛筵必散”,作为转折点。
在时间链条上,作者充分展开春夏秋冬四季的富贵繁华生活的描叙,他的怀旧情结甚至在追忆中有所忏悔的心态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

《红楼梦研究资料分类索引》(1630—2009)
这种叙时手法,与第70至80回用十分之九的篇幅写肃杀之秋,以快进键展示贾府之衰形成鲜明对比。而在贾宝玉十三岁的36回的篇幅里,为了渲染末世之盛,作者却按下了年岁的暂停键。
然而,作者按下了年岁的暂停键,却无法按下故事的暂停键。相反,不但家族盛衰故事在宏大叙事中进行,而且以贾宝玉为中心宝黛钗情感故事,以及十二正副金钗的女儿群故事,依赖家族的“末世之盛”,以大观园为基点,也得到快进键的展开。由此,家事与情事,家族史叙事与青春梦叙事两大叙事系统在时间处理上的矛盾显露出来。
石头记事年龄系统由于需要借助石头叙事和宝玉人生遭际展示贾府衰败历程,因而叙事起点年龄偏小,而且渐进较缓,而大观园生活和爱情自由理想也需要较小的年龄作为保护,以躲避礼教的干预和迫害,这是家事与情事年龄叙时一致性的方面,也是贾宝玉十三岁按下年岁暂停键有效之处。
然而,无论年岁过小,还是年岁暂停,又不符合青春理想的正常规律。情感追求和青春理想都需要一定长度的年龄展开过程,绝非贾宝玉十三岁这一年的时间跨度可以容纳。
由于几乎所有贾宝玉的亲近姊妹都在贾宝玉的年龄线上下活动,而且黛玉湘云等才高情密者比宝玉年小,于是就出现了或者过于拥挤,或者难合情理之处。矛盾凸显出来了。
就宝黛爱情而言,虽然有青梅竹马和前世情缘的铺垫,但真正的试探表白到相互接受,还是在这一年春夏数月内紧锣密鼓地完成(第23至36回),最为动人的砸玉风波、诉肺腑和传帕题诗,写尽了贵族男女爱情的痛苦热烈缠绵悱恻。

刘旦宅绘宝黛
但这却发生在相当于今天小高初一年级的十三岁的宝玉和十二岁的黛玉之间,虽然孩提年龄往往成为保护,但其寻求“知己之爱”的实质内容和婚姻渴求(第32回,34回)却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渴望和成熟。
在这其中,穿插了十三岁的宝玉被提亲、十一岁的史湘云订婚的事件。而十三岁的宝玉还与已成年的二十来岁的薛蟠、蒋玉菡、柳湘莲密切交往,并参加有薛蟠挟妓的酒宴,遥慕二十三岁的傅秋芳,获得十八岁的女尼妙玉的特别青睐等等。这些都颇不合十三岁年龄线的“事体情理”。
大观园诸钗的快乐生活和才华显露,以贾宝玉与女儿们的诗社为中心,出现两个高潮,前一高潮是第37回38回初结海棠社,咏海棠、菊花、螃蟹等;参加者除李纨、宝钗外,迎探惜三春及黛玉湘云都小于宝玉,诗作黛钗争雄。
后一高潮在钗黛和解后,从香菱学诗及宝琴等四艳加入,有咏红梅花、灯谜、联句等诸多活动,时间集中于第47回至51回。
倘若四艳入园后,仍不突破十三岁的贾宝玉年龄线,而让一群人数更多的十二三四岁的小姑娘拥挤在大观园,那么,此后的一系列情节都将无法开展,探春将因年龄太小根本不具备理家的资格(第56回),薛宝琴不会议婚,邢岫烟也不可能会要准备出嫁而引起宝玉叹息(第58回)。

刘凌沧绘《宝琴立雪图》
显然,贾宝玉十三岁年龄线的狭窄时空遇到了挑战,需要突破。这个突破点,曹雪芹选择在第45回,其标志就是林黛玉年龄的提升。
古代女子及笄之年(十五岁)是成年的标志,从此可以谈婚论嫁,也就可以共同面对青春和人生话题。曹雪芹把黛玉年龄提升至十五岁,具有重要意义。
第45回回目《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风雨夕闷制风雨词》标明此回有两个重要事件,一是通过相互交心完成了从第42回《蘅芜君兰言解疑癖》开始的钗黛和解,二是林黛玉写作《秋窗风雨夕》。林黛玉的年龄提升正是为此所做的必要铺垫。
就前一点言,钗黛和解实际上是二人第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在此之前,黛视钗为情敌,钗对黛怀戒心。此次钗以友善态度和诚恳话语(“兰言”)感动了黛,才有前引那段“我今年长了十五岁”的自省肺腑之言。
不论今天人们对钗黛和解作何解读,作者曹雪芹的肯定态度是很鲜明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西厢记》《牡丹亭》是关键要件。
从年龄说,崔莺莺十九岁与张生相恋,杜丽娘十六岁思春入梦,都符合正常的青春规律。对钗黛而言,这是一个敏感而私密的两性话题。虽然宝钗以“杂书”称之(没有贬称“淫词艳曲”),以“移性情”相规劝,其传统内涵是很清晰的。这也反映了作者既同情恋爱又反对“偷香窃玉”的私情以至“淫滥”的态度。

德藏明刻套色《西厢记》 崔莺莺像
如果按照石头记事的小说年龄系统,已经及笄(十五岁)的宝钗与尚未成年的十二岁黛玉对谈,宝钗以居高临下的年龄优势教训黛玉,心高气傲的黛玉必不能接受。而把黛玉年龄提升至十五岁即及笄之年,钗黛同龄而稍长,即可共同面对隐私话题,宝钗又便于现身说法,既可避免矛盾,又易拉近情感距离。
就后一方面说,黛玉写作《秋窗风雨夕》,乃是看了《乐府杂稿》中“有《秋闺怨》《别离怨》等词,黛玉不禁心有所感,亦不禁发于章句,遂成《代别离》一首,拟《春江花月夜》之格,乃名其词曰《秋窗风雨夕》”。
无论从其写作过程,还是诗篇内容,所谓“离别”“别离”暗含的两性情感内容都是很清晰的。以十五岁的年龄写作这种诗歌,当然更加合乎情理。
由此看来,在小说主体的这一部分,为了弥补贾宝玉十三岁这条基本年龄线的叙事缺陷,作者不得不掺入了两条旧稿的年龄线。
一是贾宝玉的成人交往和参加园外成人活动,这应该是来自《风月宝鉴》旧稿:一是从钗黛和解开始的大观园诸钗活动,这应该是来自明义所见《红楼梦》初稿。
这种掺入,解决了家族史叙事与青春梦叙事矛盾带来的年龄困境,也解决了单一的贾宝玉年龄线所无法承载的情节负荷。不过同时也就带来了年龄叙时的错乱。

《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

在曹雪芹创作及修改过程中,不同年龄系统的掺入,以及造成某些人物年龄错迕,时序混乱,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它不但给作家带来写作困扰,也给细心读者带来接受障碍。
但从林黛玉年龄提升等例可以看到,有些“错迕”乃是曹雪芹有意为之,脂批也认可。这表明,所谓年龄“错迕”,也许不仅是作者的疏忽和无奈,同时也可能是作家独特写作观念的一种叙时策略。
这种换一个角度的推想思考,也许可以把过去对小说人物年龄错迕问题的消极讨论,变化成一种积极的“同情的理解”,甚至得到品味红楼的新收获。
笔者的探索观点是,曹雪芹在面对年龄错误和时序混乱等小说叙事困境时产生了某种认识飞跃。这种认识飞跃的最重要表现,是形成了突破史传叙时传统的“不拘拘于朝代年纪”的大时间观,和“新奇别致”的特征叙时策略。
中国古代小说源于史传传统,长篇说部被称为“稗官野史”。时间叙事的精确性是“信史”的基本特征。特别是以《春秋》《左传》到《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
史传体的本纪也是严格编年的。列传才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的写作。从《金瓶梅》写李瓶儿之死“五七”仪式时辰的精确细密,可以看到写实小说对时间叙事传统的继承。[10]
如果《红楼梦》是一部纯粹的写实小说,那么,包括时间(年龄)叙事的生活逻辑便是唯一的考察维度。

《红楼梦资料汇编》
但《红楼梦》创作方法并非如此简单。在曹雪芹的笔下,写实、神幻、隐喻种种融为一体。曹雪芹明白宣称他的作品是“将真事隐去”写作的“假语村言”。特别指出:
历来野史,皆蹈一辙。莫如我这不借此套者,反倒新奇别致,不过只取其事体情理罢了,又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哉!
连同此句,在第1回的这一段短短文字里,“朝代年纪……失落无考”、“无朝代年纪可考”的话说了三遍。
可见作者有意强调,并把“不拘拘于朝代年纪”作为自己创作“新奇别致”的“假语村言”的重要标志。这是对史传乃至野史叙时传统的突破。小说是虚构的叙事性文学作品,时间包括人物年龄只是叙事的线索,而因果(因缘)即“事体情理”才是故事的本质。“不拘拘于朝代年纪”,正是为了突出“事体情理”的本质艺术追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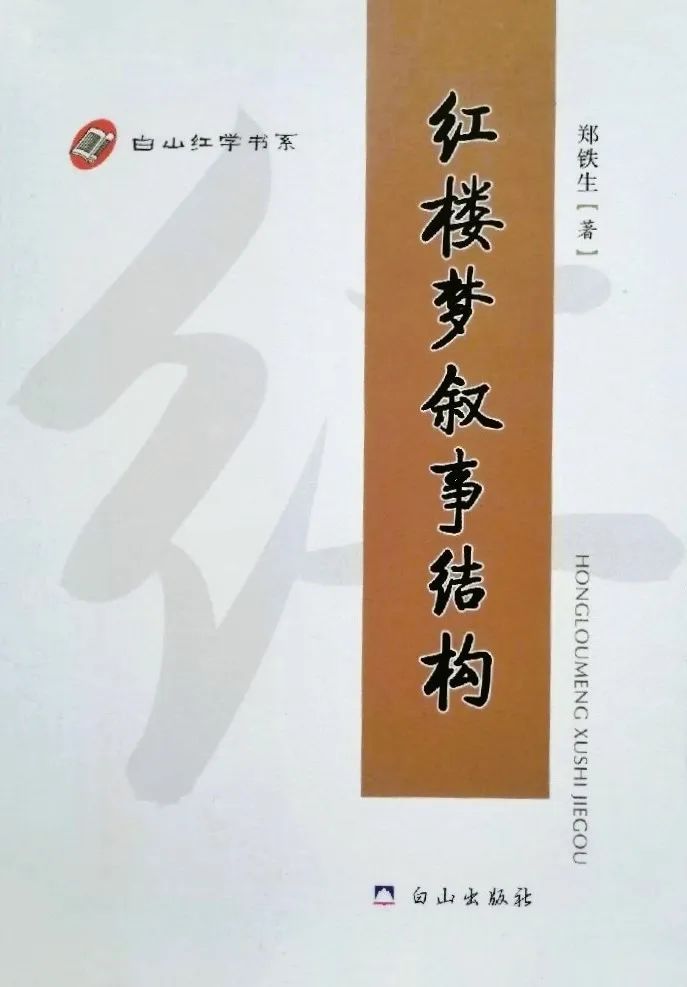
《红楼梦叙事结构》
过去,人们只从作家的“自我保护“策略理解这些话,实际上,它乃是作家创作的“大时间观”宣言。即从宏观上把握历史人生,而不执著于微观叙时的精确。
“朝代年纪”何意?有人认为,“朝代年纪”就是指王朝纪年。笔者认为,“年纪”固然有(历史)“纪年”之意,但自古以来,更多地运用于指人物年龄。以刻画人物为主的小说更是如此。
语言大师曹雪芹是非常熟悉汉语词多义兼容的特点的。“年纪”一词正是如此。空空道人评论石头故事说:
第一件,无朝代年纪可考;第二件,并无大贤大忠理朝廷治风俗的善政,其中只不过几个异样女子……(第一回)
可见他是把“朝代年纪”词语作为分别对应于政治社会历史和个体人物年龄二者的时间概念。
“年纪”一词在《红楼梦》中多次表示人物年龄,如前引第49回“叙起年庚,除李纨年纪最长”,又同回贾母说:“这是我们有年纪的人的菜”等等。
所谓“无朝代年纪可考”,乃是曹雪芹“大时间观”下的叙时策略,大而言之,王朝世代:小而言之,人物年龄,都是具体物质的时间存在。“大时间观”超越这些具体视点,小说石头下凡历劫回归记事的构思,和借助于佛家观念语词的“空-色-情”哲理思悟,使作家能够站在超越性的认识顶点俯视过往时间。
所谓“何必拘拘于朝代年纪”,就包含对具体而微的时间的有意模糊和忽视,而凸显描写对象的概括性与典型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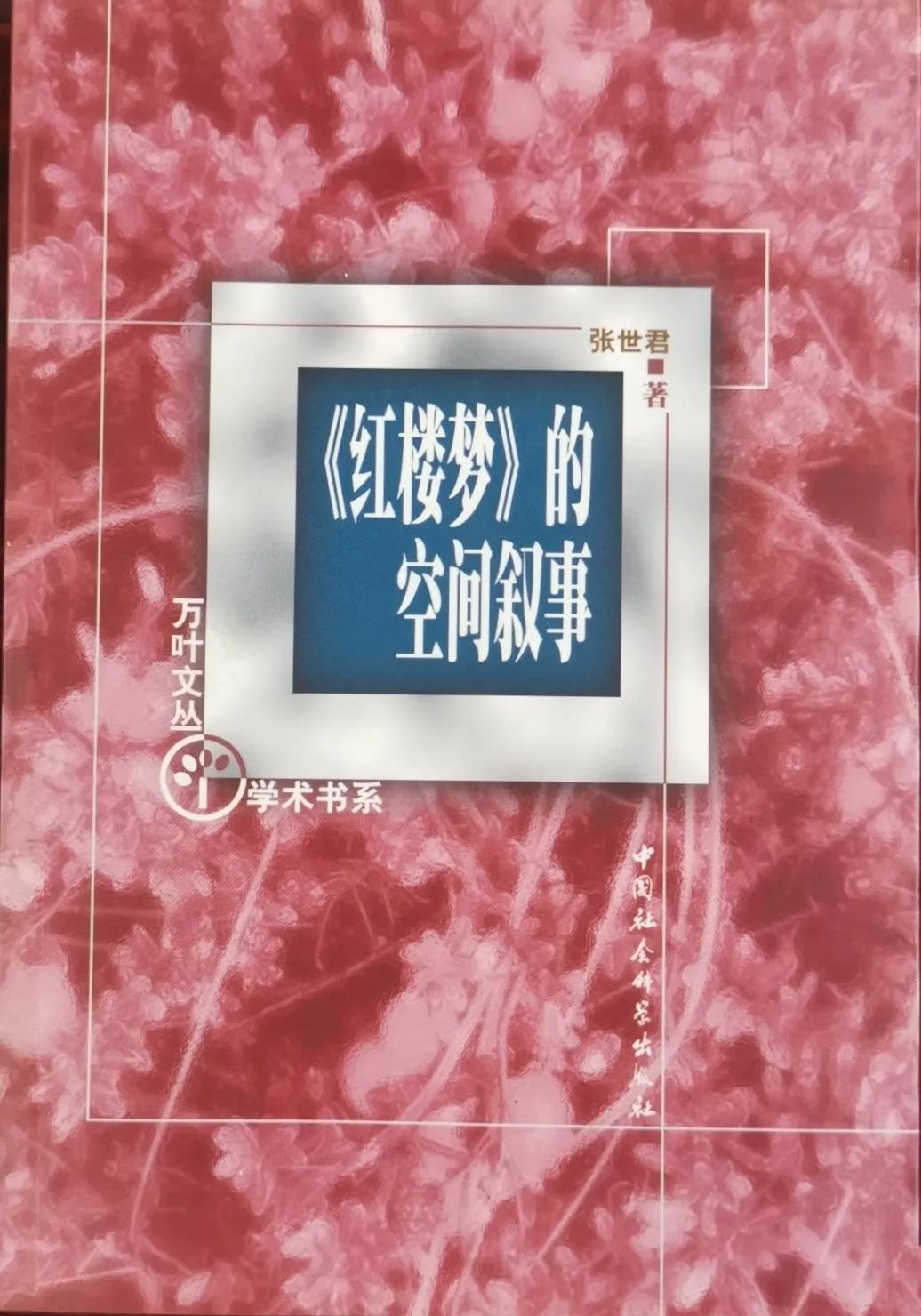
《红楼梦的空间叙事》
从写历史看,《红楼梦》着眼于盛衰记忆和变易规律,这就是它并不执着于一己家世和当朝政治,所叙贾府和四大家族“无朝代”可考的原因。
那种认为《红楼梦》是曹家自传,或者把它看作影射清朝康雍乾政治或寄托“反清复明”的观点,是作者明确否定的。所谓“无朝代”可考,不能只看做“真事隐去”的掩护,更应该理解为“假语村言”的高度历史概括功能。
从写人生看,所谓“无年纪”可考,则应理解为作者着眼于年少青春记忆和情感理想。这种记忆和理想的本质不是年龄的大小,而是纯净的真情、自由和美。这就是它并不注重宝黛钗及十二钗诸册女子年龄精确性甚至不惜保留种种矛盾的原因。
“大时间观”的计量单位也发生了变化。曹雪芹借助包含历史运动变化的佛教时间观念,设置宏大计时单位。

《石头记叙事时间线与成书时间》
第1回从“造劫历世”到“劫”“世”并联,叙僧道携石头幻化的通灵宝玉下凡,说“后来,又不知过了几世几劫”,空空道人在青埂峰下看到石头记。其实就是寓示作者写下了“历尽离合悲欢炎凉世态的一段故事”,时间距离不过几十年。
这里却把古代的纪年单位“世”与佛家的“劫”连在一起。作为时间单位的“劫”,佛教视之为不可计算之长大年月(或谓一劫为四十三亿二千万年)。古代以三十年为一世,但同包含尘世成住坏空的“劫”并联,就变得无比漫长。
又,同回甄士隐梦中道人对和尚说:“三劫后,我在北邙山等你。”甲戌眉批云:“佛以世谓劫。凡三十年为一世。三劫者,想以九十春光寓言也。”
这是径直以“劫”代“世”。内涵丰富外延漫长的“劫世”概念取代“年岁”进入家事历史叙事,就是具体时间含糊而内涵清晰的“末世”观念:“凡鸟皆从末世来”,“生于末世运偏消”。(第5回)用冷子兴的话,这种末世特征就是:
如今生齿日繁,事务日盛,主仆上下,安富尊荣者尽多,运筹谋划者无一。其日用排场费用,又不能将就省俭。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未甚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这还是小事,更有一件大事,谁知这样的钟鸣鼎食之家,翰墨诗书之族,如今的儿孙,竟一代不如一代了!(第2回)
这实际上是作者对自古以来“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富贵衰败规律的剖析概括,表明作者站在宇宙高位审视历史和人生。这段话里又出现了一个时间词语“代”。
父子相继为代。“代”与“劫”、“世”(“末世”)一起,构成“大时间观”的叙时单位。在这种大时间观观照之下,精确的具体人物年岁变得相对并不那么重要了。

《情节与历史叙事》时间与叙事
曹雪芹从来就是用充满着哲学睿智的眼光审视创作诸要素的本末大小轻重缓急。第47回香菱学诗与黛玉对话:
(香菱)“……如此听你一说,原来这些格调规矩竟是末事,只要词句新奇为上。”黛玉道:“正是这个道理。词句究竟还是末事,第一立意要紧。若意趣真了,连词句不用修饰,自是好的。这就做‘不以词害意’。”
实际上这也是曹雪芹的小说写作要素观。“第一立意要紧”。时间当然是叙事要素,年龄只是一种叙时手段。
曹雪芹当然意识到他的小说中某些人物年龄错迕可能造成阅读障碍。但这种“末事”不会造成“系统性失误”。他的“无朝代年纪可考”事实上就包含着一种导引性回应。“考”,包含考察、考核、考求等义。
无可考,即既不可从现实中得到实在性印证,也不可从逻辑上得到合理性解释。就“无年纪可考”而言,就是既不可验证于现实,也不必考核于前后,只能以文本所叙为是,凡文本未叙即不作考索。

《文学时间研究》
年岁叙事的精确、连贯和前后一致本来是写实叙事的基本要求,细心的阅读会发现和指摘小说人物年龄的错迕,作者无权拒绝读者的质疑和批评。
但是,作者显然认为,比较起精确叙时纪岁,完成他的主题表现、规律探寻、人物刻画等等是更加重要的。在几经修改而二者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他只能有所取舍。
在石头叙事的贾宝玉十三岁年龄线上,第45回的黛玉只能是十二岁,提升至十五岁毫无文本依据,也违背逻辑常理,但黛玉十五岁的年龄设置乃是影响后文的关键。
因为贾宝玉的年龄线已经不能满足大观园青春梦的叙事要求,必须有所调整突破。学者们可以考究出“十五岁”可能来自另一年龄系统。但读者们只是从文本上看到毫无来由的“十五岁”。
这当然是“无年纪可考”。既然诸本皆然,可见出自曹雪芹手笔,那就认了吧,不要再胶柱鼓瑟,探究前文的贾宝玉十三岁年龄线了。
由此可知,所谓“无年纪可考”,并非要掩盖小说明显的或隐性的人物年龄错迕,而是告知读者不要因小失大、舍本逐末,不必在年纪问题上纠缠,影响对作品宏大叙事和精细艺术描写的欣赏把握,避免由于过于关注人物年龄或因人物年龄错迕问题产生阅读失误,并且进一步提示读者,他在有意创造“新奇别致”的叙事策略。
应该说,这也是作者的一种导读技巧。前引第49回叙群钗年龄“不能细细分晰”,“随便乱叫”,恐怕也正含此深意。

《中国近现代小说中的时间问题研究》

如果说,以“无年纪可考”导引读者放弃对于年龄问题的过分关注与纠结,只是一种消极的回应,那么,更具有积极意义的是,曹雪芹进行了“新奇别致”的叙时写作策略创造。这种创造,以浪漫、隐喻与写实结合的特征叙时改造单纯的写实精确叙时,显示了《红楼梦》的文本特色和作家的创新精神。具体而言,有如下做法:
其一,创设浪漫、隐喻与写实融合的总体叙时构思。
一开始就申明小说系“假语村言”并且是“荒唐言”的叙事性质和特点。设置“情根石”化身“通灵宝玉”随贾宝玉降生的神性故事作为年龄记事的起点,使人物年龄叙时具有浪漫、隐喻与写实融合的特点,从而区别于精确叙时的纯写实小说。这是《红楼梦》“不拘拘于年纪”的非精确叙时的构思支柱。

《中国叙事学》第2版
贾宝玉的衔玉而生,就使他成为“古今未有之人”,“通灵宝玉”前身“情根石”,寓意“行为偏僻性乖张”的叛逆本质,“木石前盟”的前世情缘,就使宝黛爱情笼罩命定的悲剧色彩。所有这些,都启示读者必须转换单一的写实视角和评价标准。
冷子兴说:“说来又奇,如今长了七八岁,虽然淘气异常,但其聪明乖觉处,百个不及他一个。”逆反“男尊女卑”的“泥水骨肉说”,当然不是七八岁孩子的思维水平和能力。至于第五六回的梦遗和初试云雨,作者的意图只在于写出性发育成熟,作为以后写“情“的生理性基础,是否合乎男子精通年龄,并不需要合理性证明。
笔者试图用“梦中长大”的神幻叙事解释曹雪芹模糊宝玉年龄的用笔,也是着眼于其非写实特点。[11]因为导致这一事件的“游幻境指迷十二钗,饮仙醪曲演红楼梦”(第五回回目)本身就没有任何“现实合理性”值得探究。
其二,创造年岁模糊而特征鲜明的非对称信息流。
笔者也把这种创造称为“童性年龄与少年青春特征的二重性用笔”。所谓“非对称信息流”,实际上是在写实内容中融入浪漫想象,创造诗性情境,弱化年龄意义,突出事体情理。第三回宝黛初见就是一个范例。
依石头记事系统,黛玉进府不过六七岁,宝玉七八岁,但二人见面时相互眼中的印象却是:
(黛玉)心中想着,已进来了一位年轻公子……面若中秋之月,色如春晓之花,鬓若刀裁,眉如墨画…….越显得面如敷粉,唇若涂脂,转盼多情,语言常笑。天然一段风骚,全在眉梢;平生万种情思,悉堆眼角。
(宝玉)厮见毕归来,细看形容,与众各别:两弯似蹙非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如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弱三分。

孙温绘贾宝玉初会林黛玉
这种初见的互感印象,绝非童真甚至也非懵懂少年,而是情窦初开的美丽青春形象。它所呼应的,正是绛珠仙子与神瑛侍者的前世情缘,因此才会有似曾相识一见如故的神秘感应:“黛玉一见,便吃一大惊,心下想道:‘好生奇怪!倒像在那里见过的一般,何等眼熟到如此!’”“宝玉看罢,因笑道:‘这个妹妹我曾见过的。’”它把日久生情和一见钟情这两种情感模式巧妙地融合在一起。是曹雪芹的神来之笔。
笔者曾经就此提出了“童性年龄与少年青春特征二重性”的命题进行探索:
曹雪芹创造了一种带有童性年龄和少年青春特征信息双重性的艺术笔墨。这种叙事年龄与实际年龄特征不一致的状况,主要是创作修改过程复杂性所致,也是艺术表现的需要。青梅竹马,最好童蒙待启;相知相悦,需要情窦初开。……
文本显示,这是一对小儿女的初见,而其少年青春气息,则是特殊意义的附加。这种特殊意义,就是作者为宝黛爱情设置的前世情缘。我们可以把这种附加称为叙事的“溢出性”信息。“溢出性”信息负荷着写实笔墨的表意功能。[12]

连环画《宝黛初会》
把宝黛相见的年龄提升几岁,或许能够使黛玉的言行举止更符合初进贾府“时时在意,处处留心”的描写,但并不能弥合“童性年龄与少年青春气息二重性”的矛盾。
相反,还可能影响作者描写的这对小伴侣“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两小无猜礼教不防的真实合理性。
作者的策略则是有意模糊二人年岁,凸显一见如故的心灵感应。人们注意到,第二回有宝黛年龄的明确交代,第四回有宝钗年龄的明确交代,但第三回除了雪雁之外,所有人物都没有明确的年龄信息。
王熙凤问黛玉几岁了,也没有写黛玉的回答。以至于不联系第二回的年龄信息,单独阅读第三回,在作者着意渲染的艺术氛围里,人们都感受不到宝黛年龄幼小与互感的不和谐。非精确特征叙时的艺术笔墨,在第三回已见端倪。
年龄与性格心理的非对称信息流一直贯穿到大观园生活前期。以45回林黛玉年龄提升点为分界线。
在此之前,青春梦主题的许多情节都具有某种超年龄超现实的浪漫意味。集中于第23回至34回的宝黛爱情,“彩笔辉光若转环,心情魔态几千般。写成浓淡兼深浅,活现痴人恋恋间。”[13]。
但这发生十三岁的宝玉和十二岁的黛玉之间,却显出与年龄不相称的纠结缠绵。少年宝玉与成年男子蒋玉菡等一见倾心的密切交往也令人费解。

邮票《黛玉葬花》
在贾宝玉的年龄线上,大观园的诗魂林黛玉的青春绝唱《葬花吟》以及爱情绝唱《题帕三首》都写作于十二岁。
这位尚未受到现实风刀霜剑压迫,在大观园的明媚春光里生活的豆蔻少女,竟写出充满死亡意识毁灭悲情的“一朝春尽红颜老,花落人亡两不知”的长篇歌行,几为古代著名才女所不及。[14]
而海棠诗社诸女子的写作年龄,有的比黛玉还小,年方十一的史湘云居然写出很有魏晋名士风度的“萧疏篱畔科头坐,清冷香中抱膝吟。数去更无君傲世,看来唯有我知音“(《对菊》)和预示未来孤苦命运的“自是霜娥偏爱冷,非关倩女亦离魂”(《咏白海棠》)等,按照现实合理性的标准,岂非都不可思议?
在作者弱化年龄信息的笔墨下,这些与年龄不对称的信息仍然独富魅力。可见“二重性”乃是一种特殊写作技巧。至第45回黛玉年龄提升,其所作《秋窗风雨夕》与年龄的不对称才消失。

戴敦邦绘风雨夕闷制风雨词
其三,创设叙时特征支点和标杆年岁。
《红楼梦》多年岁模糊或错乱,但并不等于作者不重视年岁时间的标识性意义。就家族末世史而言,清二知道人早就提出小说的四季特征问题,后来诸多学者对《红楼梦》的四时叙事进行研究。[15]
《红楼梦》重视关键性的时间节点。从全书布局看,元宵、中秋都是极为重要的对映性节日。“用中秋诗起,用中秋诗收,又用起诗社于秋日。所叹者三春也,却用三秋作关键。”(甲戌第一回眉批)[16]。
前文所引宝玉十三岁板块,两个元宵之间的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描写和隐喻意义十分分明,又与十五岁(70至80回)略春夏详秋,形成贾府盛衰映照。
《红楼梦》人物年岁大多模糊,甚至成为描写热点的人物生日(贾敬、凤姐等)也不显年岁,但作者仍为几位主要人物的年龄设置了清晰的标杆年岁。
这几个标杆年岁,是作者意图的明确表现。除了作为石头记事标杆的贾宝玉入园之年十三岁外,最重要的标杆是宝钗和黛玉及笄之年十五岁,此外,就是晴雯夭亡之年十六岁。标杆年岁的意义,是对本人或相关人员及情节布局有重要影响。宝玉前文已论,晴雯另当别论,这里再补充黛钗及笄之年特别是黛玉十五岁的标杆意义。
前文已论,钗黛十五岁分别设置在两个不同的年龄系统——石头记事年龄系统和大观园“金钗”年龄系统里,前者是叙时主体,后者是叙时掺入,但这种掺入改变了原来主体的年龄标尺。原来以十三岁的贾宝玉为标尺的众姊妹年龄,提升成了以十五岁的林黛玉为标尺的年龄系统。

陆小曼绘大观园
大观园的青春梦描写也因此划分为前后两段。简而言之,贾宝玉十三岁(黛玉十二岁)入园是“青春梦”的初始,而提升的黛玉十五岁已经到了“青春梦”的边际。这二者是具有某种对映意义的。
在前一时段,第22回宝钗的及笄之年,贾母亲自为她庆贺,还请了戏班子,这当然引起黛玉不快。
不过,宝钗给宝玉说戏,居然点赞了《虎囊弹》的《山门》的《寄生草》曲:“谢慈悲剃度在莲台下,没缘法转眼分离乍,赤条条来去无牵挂……”,使宝玉在难解的女儿纠葛中感悟“赤条条来去无牵挂”的禅意。同一回宝钗做的“更香”灯谜:“朝罢谁携两袖烟,枕边衾里总无缘”,都寓示其未来婚姻的孤苦命运。
而在后一时段,第45回黛玉及笄之年作伤感离情的《秋窗风雨夕》“泪烛摇摇爇短檠,牵愁照恨动离情”,“不知风雨几时休,已教泪洒窗纱湿”,也明显流露对未来的悲剧预感。钗黛的婚姻爱情悲剧都暗示其中。

《林黛玉的悲剧》
但比较起来,黛玉的十五岁,与后文情节具有更强的连贯性。一方面因为钗黛和解,黛玉多少改变了过去的孤高自许,更多地融入大观园短暂的欢乐之中;另一方面,则因年华渐长,更深地陷入爱情追求与传统观念的矛盾。
特别是57回宝黛二人的生死至情暴露后,紫鹃和薛姨妈以不同心态提出了婚姻问题而后文并无着落,其爱情前途的悬念一直贯通到八十回末《芙蓉诔》“诔晴雯即以诔黛玉”的隐射中。
进一步看,林黛玉标杆年岁作为大观园“金钗”年龄系统的代表,成为了大观园理想的边际线。
一方面,少女成长,崭露头角,如探春在理家、拒检等事件中大放光彩;另一方面,少女长大,谈婚论嫁,礼教防范压迫加强,大观园理想的终结即将到来。
从一定意义上说,第45回“金兰契互剖金兰语”,钗黛谈心,“读杂书,移性情”的警告,实际上已经隐含外在礼教势力对宝黛爱情的干预。
虽然此后群芳毕集还在延续,但第63回怡红夜宴,麝月的“开到荼蘼花事了”花签已经暗示欢乐即将终结。作者用两回篇幅铺叙宝玉生辰却有意模糊宝玉年岁,更显示了黛玉标杆年岁的边际意义。
到同样年岁提升的贾母八十大寿(第71回)[17],“末世之盛”的绝唱掩盖的各种矛盾一一爆发,随着寓示黛玉命运的晴雯之死等一系列悲剧,大观园的末日也就即将到来。家族史叙事与青春梦叙事在黛玉标杆年岁中扭结成了一个整体。

电视剧《红楼梦》中贾母剧照

《红楼梦》第45回林黛玉的年龄提升至及笄之岁,既是曹雪芹用掺入不同年龄系统的方法解决家族史叙事与青春梦叙事矛盾的一个标杆,又是关系全书人物描写和情节走向的一处关键,具有多重意蕴和功能。
由此人们看到曹雪芹面对创作和修改过程难以解决的叙时矛盾产生的认识飞跃,一方面,以“不拘拘于朝代年纪”的大时间观导引读者不舍本逐末,不纠结年龄错迕;另一方面,积极创造浪漫、隐喻与写实融合,年龄与特征非对称信息流和标杆年岁等特征叙时策略,成为小说“新奇别致”艺术效果的重要亮色。所有这些,都值得深入探讨。
2024年11月15日定稿于深圳
注释:
[1] 参见刘上生《换一个角度思考——<红楼梦>人物年龄错迕问题新探》,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2024,9,15..
[2] 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180至201页。
[3] 本文所引《红楼梦》原文,除特别说明外,均据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本《红楼梦》,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4] 【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592页。
[5] 一粟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红楼梦卷》,中华书局1963年版,104页,174页。
[6]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201页。
[7] 张俊沈治钧《新批校注红楼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678页。
[8] 沈治钧《红楼梦成书研究》,中国书店2004年版,194页,223页。
[9] 刘上生《论明义所见<红楼梦>抄本的文学史意义》,载《红楼梦学刊》2019年第3辑,刘上生《从曹学到红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380至393页。
[10] 参见刘上生《质实与空灵——“瓶儿之死”与“秦氏之丧”的比较研究》,载《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3辑,《从曹学到红学》,浙江古籍出版社2024年版,329至344页。
[11] 参见刘上生《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浙江古籍出版社2019年版,036至044页。
[12] 刘上生《探骊——从写情回目解味<红楼梦>》,029至035页。
[13] 【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335页。
[14] 【明】沈宜修《季女琼章传》记才女叶小鸾十二岁能诗,“今检遗箧中,无复一存。想以小时语未工,儿自弃去耶?”
[15] 裘新江《春风秋月总关情》,《红楼梦学刊》2003年4辑。
[16]【法】陈庆浩编著《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27页。
[17] 第39回,贾母对七十五岁的刘姥姥说:“比我大好几岁呢。”按石头记事年龄系统,71回八十大寿,年龄至少提升了五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