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浪漫时期的音乐(1820—1910)
第三节 中期浪漫乐派
向阳光
二、理查德·瓦格纳
(二)艺术成就
6.音乐风格
瓦格纳自《漂泊的荷兰人》之后的乐剧作品都是艺术杰作,创作质量之高为音乐史中罕见。他在音乐语言的各个方面均有重大突破和创新,形成了浓郁、恢宏、炽烈、复杂而具有强烈感染力的音乐风格。因此,瓦格纳对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对其身后德国乃至整个欧洲的音乐创作和文艺思想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他的乐剧中,“主导动机”作为具有丰富象征内涵和无限发展潜能的材料细胞,不仅指代具体的人物、感情、意念或物体,而且根据不同的戏剧情境进行交响性的裂变、组合、变奏和转型,因而和传统歌剧中的“回忆性主题”具有本质上的差异。在以《尼贝龙根的指环》为代表的长篇乐剧中,一些处于中心地位的主导动机贯穿剧情发展的始终,既推动了剧情的发展,又起到了整合结构的作用,成为瓦格纳乐剧风格中的核心因素。

尼贝龙根的指环
与主导动机的运用紧密关联的是,在瓦格纳的乐剧中,乐队的作用得到空前提高,成为戏剧叙述和内涵表达的中心要素,其地位不仅不在人声之下,有时甚至超越人声成为戏剧的主角。如果说人声的旋律和歌词表达了戏剧外在的具体情景和内容,那么乐队的无言音乐则往往刻画戏剧内在的隐秘内涵和意味。在瓦格纳的手中,乐队的丰富表现力得到极大的扩展,虽使用庞大的四管制乐队编制,启用如瓦格纳大号等诸多崭新乐器,但配器手法根据剧情需要变化多端,从震耳欲聋到细致入微,其效果之瑰丽和手法之新颖,使瓦格纳得到“魔法师”的赞誉。
在乐剧的结构处理上,瓦格纳认为传统歌剧中的咏叹调、二重唱、重唱、合唱以及芭蕾舞场景往往打断剧情发展,人为地破坏戏剧的连贯。因此,为了歌剧的整体性和情节发展的不间断性,他创造了不断跟随戏剧运动、时刻与戏剧表达联系在一起的“无终旋律”。瓦格纳的连续性乐剧结构摒弃了传统歌剧中的“分曲”音乐惯例,取消了“分曲唱段”的独立性,融合宣叙调的叙述性特征和咏叹调的抒情性特点。声乐部分在瓦格纳的乐剧中,不具备独立的意义,它成为乐队中的一个声部,与乐队构成织体上的对位层,旋律写作追求表达词意的深刻意味,摒弃外表的华丽动听,形成具有特色的瓦格纳式咏叙旋律风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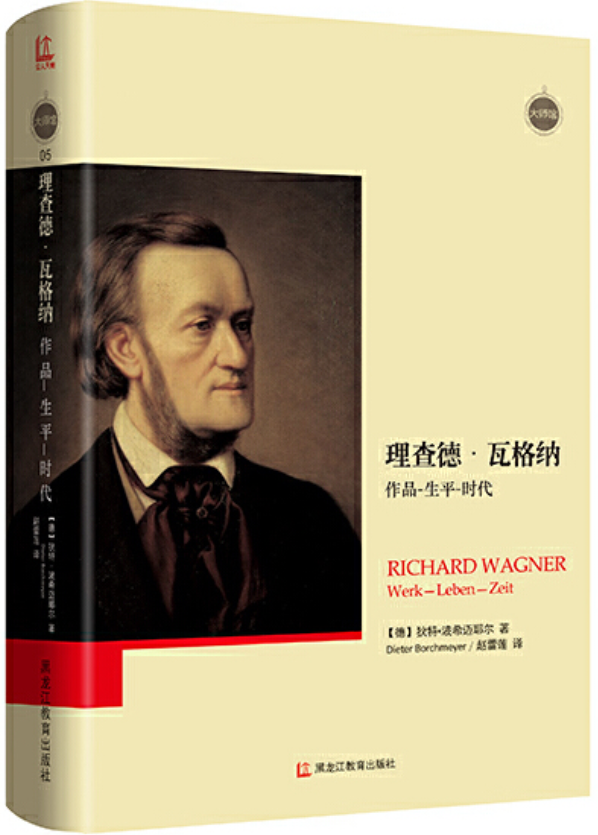
由于瓦格纳在传统和声功能体系的范围内大量使用半音化的和声进行,他开创了和声史上的新纪元。在瓦格纳的乐剧中,由于时间尺度的扩大和变音和弦的大量使用,和声关系开始模糊,调性中心的游移普遍存在;但另一方面,他在扩展半音和声使用范围的同时,并没有完全抛弃调性和声的基础。调性的向心力和半音化和声的离心力之间构成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使瓦格纳的和声写作具有高度的情感表现力。著名的《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前奏曲中,具有强烈导向的变音属七和弦不断“解决”到另一个同样不协和的变音属七和弦,主和弦从未真实出现,但一直潜伏在音乐背景中,从而妥帖表达出该剧情欲渴望,但却无法满足的中心戏剧意念。
瓦格纳的乐剧,是德国歌剧发展的顶峰。在他逝世之后,其他德国歌剧作曲家长期处于他的阴影之下,因而他对后世的影响既是建设性的,又是消极性的。瓦格纳刚愎自用的做人风格,其思想意识中的反犹主义和德意志中心论,以及二战期间希特勒对瓦格纳的推崇以及与他家族的密切交往,都遭到后人强烈非议。然而直至今日,瓦格纳的剧作继续稳居世界各大歌剧院保留剧目的中心地带,拜罗伊特艺术节依然香火不断,对瓦格纳作品和思想的研究,仍在继续深入。可以预见,作为一个具有复杂人格的音乐文化巨人,尽管瓦格纳的直接影响力已经今非昔比,但他对后人依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7.主要作品
(1)音乐戏剧

《仙女》(1834);《禁恋》(1836);《黎恩济》(1840);《漂泊的荷兰人》(1841);《汤豪瑟》(1845);《罗恩格林》(1848) ;《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1859);《纽伦堡的名歌手》(1867);《尼贝龙根的指环》——包括《莱茵的黄金》(1854)、《女武神》(1856)、《齐格弗里德》(1871)、《诸神的黄昏》(1874);《帕西发尔》(1882)。
(2)管弦乐
《C大调交响曲》(1832);序曲《克里斯托弗·哥伦布》(1835);《D小调浮士德序曲》(1840,修订于1855);《效忠进行曲》(1864);《齐格弗里德牧歌》(1870);《皇帝进行曲》(1871);《百年纪念进行曲》(1876)。
(3)声乐曲
合唱《信徒之宴》(1843);合唱《臣民对敬爱的腓得烈奥古斯特之赞礼》(1843);人声与钢琴《韦森东克之歌5首》(5,1858)。
(4)著述

《德国歌剧》(1834);《哈列维和法国歌剧》(1842);《德国和他的侯爵们》(1848);《艺术与革命》(1849);《音乐中的犹太性》(1850);《歌剧与戏剧》(1851);《未来的艺术作品》(1860);《什么是德国的?》(1865);《我的一生》(1865—1880);《德国艺术与德国政治》(1867);《论指挥》;《贝多芬》(1870);《关于“乐剧”的命名》(1872);《宗教与艺术》(1880);《英雄精神与基督教精神》(1881);《关于人类中的女性》(18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