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梦的黄金时代(1945年-1970年)
二战结束后,美国制造业迎来前所未有的繁荣。美国国内制造业产值(不包括海外美国企业)1953年达到全球的28.3%,占本国GDP的28%。就业人数一度高达1,900万,形成底特律汽车城、匹兹堡钢铁带等多个产业集群。依托强大的产业优势与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美国工人的收入与福利水平在美国是中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更是首屈一指:一个美国工人,可以很轻松养活一个四口之家,两辆车、一条狗。

1953年制造业平均周薪为75美元,是服务业工资的1.5倍。
通用汽车生产线工人时薪1.8美元,加上加班费年收入可达5,000美元,足以进入全美收入前30%。
一辆雪佛兰轿车售价1,500美元(相当于工人5个月工资),而2023年同等车型需工人10个月工资。
2,单收入养家与住房模式。
1955年,82%的已婚男性制造业工人仅凭一份收入即可负担全家吃住与子女教育开支。底特律一线工人家庭年收入约4,800美元,而郊区独栋新房均价约8,000美元,不到两年工资即可全款购买。抵押贷款利率仅2—3%,远低于后世水平。
3,建立了完备的福利制度。
1950年,汽车工人工会(UAW)谈判斩获了全额医疗保险(0自付)、固定收益养老金(退休后领取原工资60%)、每年2—4周带薪假期等福利。1953年,通用汽车在福利支出上占劳动力成本的比重高达17%,而到2023年,仅剩8%左右。

4,消费型社会逐渐成型,生活流动性强劲。
1955年,75%的制造业家庭至少拥有一辆私家车;60%家庭拥有洗衣机和冰箱(1940年不到10%)。匹兹堡钢铁工人家庭典型配置:克莱斯勒New Yorker轿车(分期月付50美元)、郊区四卧室独栋住宅(月供60美元)、子女享受免费公立大学教育(当年州立大学学费约200美元/年)。1948—1973年,美国制造业生产率增长96%,工人工资与生产率几乎同步增长(实际工资增长约91%),社会流动性强劲。5,工会力量强大,分配模式合理。1954年峰值时期,34%的私营部门工人加入工会(2023年仅6%),通过集体谈判确保了3%以上加通胀的年均工资增长。流水线工人与管理层的收入差距维持在4∶1左右,而到2023年已拉大至约300∶1。
住房负担:1955年工人3.5年收入可买房,2023年需8.2年。
教育成本:密歇根大学1955年学费150美元(工人2周工资),2023年为16,000美元(工人5个月工资)。
这一时期的生活水平建立在美国占全球制造业50%份额(1950年)、企业税最高达91%(1950年税率)以及强工会集体谈判的基础上。
但随着1970年代产业转移、自动化加剧和工会衰落,这一模式逐渐瓦解——到2023年,美国制造业就业人数已降至1300万,占GDP比重不足11%。
三,美国工人生活好的四大原因。
1.战后全球格局赋予的领先优势美国本土未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而欧洲和亚洲工业体系急需重建:美国既是“世界工厂”,也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受益国,形成全球50%以上的制造业份额。
2.技术创新与产业集群效应底特律三巨头(通用、福特、克莱斯勒)引领汽车工业标准化与流水线作业;匹兹堡及五大湖区钢铁、化工产业凭借里程碑式创新(电炉炼钢、高分子化学)牢固占据全球市场。
3.政府政策与税收体系1950年代,美国企业最高边际税率一度高达91%,政府借此征收的高额税收部分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州际公路网)、教育和社会保障,促进了中产阶级的扩大与消费能力的提升。
4.劳资关系与法律保障1935年《瓦格纳法案》确立工人集体谈判权,1946年《塔夫脱-哈特利法案》在维护雇员组织自由的同时,也为工会与企业划定了更为稳定的博弈规则,共同推动了劳资合作与共享经济成果的实践。
5,工会力量巅峰:35%私营部门工人加入工会(1954年),推动工资与福利集体谈判。


2.技术替代与自动化浪潮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自动化设备和机器人广泛应用于流水线,制造业劳动需求减少。据统计,2000—2020年间,美国制造业岗位减少约40%。
3.金融化趋势与股东至上导致的资本转移。上世纪80年代以来,以股东回报最大化为导向的公司治理逐渐取代利润与工资“双赢”模式。
资本转移:标普500企业海外利润占比从1970年的5%升至2020年的45%
导致分配差距扩大,劳资共享的传统被边缘化。
4.工会影响力衰退工会会员比重从1954年的34%下降到2023年的6%,集体谈判能力严重削弱,使得工人与企业之间的收入增长分配权力失衡。
里根时代政策转向更是加速了体系崩溃:
1981年解雇罢工航空调度员事件削弱工会力量,1986年税改将企业税从46%降至34%,资本利得税从28%降至20%。
这些变革使劳动报酬占国民收入比重从1970年的58%降至2020年的53%。

5.当下的政策响应为重振制造业,美国先后推出《芯片与科学法案》(2022年颁布,520亿美元补贴半导体产业回流)、《通胀削减法案》(IRA,2022年生效,大规模扶持新能源与绿色产业)。然而,全球劳动生产率红利分配机制已根本改变,能否重塑中产繁荣尚待观察。
五、结论1950—1970年美国制造业黄金时代,得益于“无损战后市场”“技术领先”“强势工会”“高税收分享”“完善社会保障”等多重因素叠加,创造出工人阶层普遍体面的生活。
今日回望,其核心在于劳资共赢与财富再分配机制的平衡。
一旦这一平衡被打破,便难以复刻当年奇迹。面对未来,既需产业政策和技术创新的支持,更需关注社会分配正义和劳资关系的健康格局,才能为新一轮中产阶级繁荣提供可持续的制度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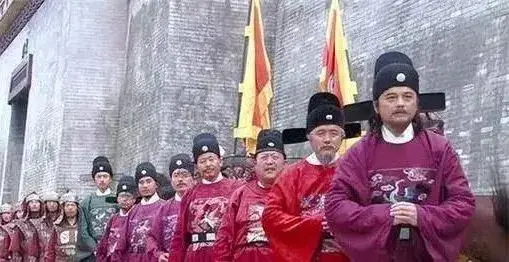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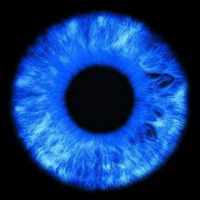
美国制造业巅峰时,同时也是苏联实力巅峰时。面对着华约集团的强大军力,资本家只能善待工人。
因为有苏联
外面还有一个参照物!
[赞][赞][赞]
工会勇于争,工人有保障!
这个本质是二战红利够吃二十年,美国吃了二十年,苏联何尝不是,只是二战美国获得的红利最大,世界财富和知识人才皆归于美国,苏联捞得些机械设备和德国技术人才。七十年后你还想吃红利就是异想天开了。
苏联的存在,美国以及西方国家不得不提高普通民众的生活以体现民主,自由的制度优越性!西方资本财团也因为苏联的存在,不得不交给更多税以对抗苏联……冷战时期西方国家老百姓过的比现在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