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编辑:nirvana
这是1939年,四川泸州城中。
一声突如其来的防空警报,划破清晨的天际。
城中瞬时戒备森严,军警荷枪实弹,如临大敌;而街巷里的百姓,则慌作一团,纷纷躲进地窖、屋后、茶馆角落,只因以为日机将至。

就在这乱中夹着惶恐的气氛中,一辆不起眼的军车,悄然从大北街监狱驶出,直奔长江与沱江交汇的管驿嘴。
等到傍晚,街头巷尾才传出风声——原来那警报并非为敌机所设,而是为一人而响。
那人,便是南溪金厂劫案的主谋、川南巨匪之首、传说中“百步穿杨、飞檐走壁”的杨黑兽头——杨海清。
泸州当局密令行刑,防空警报是为避开其兄弟伙劫法场。于是,这位搅动川南数年的匪王,终于倒在了自己最擅长利用的混乱与暗影之中。
至此,一桩震动川南的黄金劫案,才算落下帷幕。
第一章:金潮与匪患
万里长江第一县的宜宾南溪县(宜宾市南溪区),江水千年流淌,沙中夹金这件事早就不是新闻了。
靠河吃河的人都知道,南溪沿江一带,到处都有沙金。
只是,这金子虽多,却不是哪里都能淘。
像东门的金鸭儿滩,沙金虽密,却是“游金”——一淘就漂,贴不上盆子,白忙一场。
又比如石城墙附近、中坝、学堂码头这一带,金子成色好,但石头多、沙不好洗。
真正的宝地,是瀛州阁水口一线,这个地方的金沉得稳,贴得牢,是淘金人眼里的“金窝”。
但直到1936年农历十月,这块“金窝”才第一次被动了真格的。
此事的发起人是宜宾人冯永年。

他托着省上批的采矿证,带着三十多条船、五十多号人,硬生生在瀛州阁下水开工,说是按规章来淘金,合法经营。
但南溪地方人对此很不买账。
最反对的是本地前清解元曾继光。这位老先生一口咬定:瀛州阁是南溪的风水口,沙金一淘,河道就会变,早晚这地儿要喂鳌鱼。
一席话,搅得街头巷尾议论纷纷。
百姓气不过,几次找县府请愿。
县长偏偏两头不沾,说“不反对,也不支持”,一句话等于没说。
结果当天县衙门口就闹开了,几十号人挤进大堂,当场跟县长拍桌子吵架。
冯永年见风头不对,就转去龙川庙一带另起炉灶。
谁知那地儿早有农业试验场,也不愿意掺合淘金的事,结果又被赶了出来。
最后百姓一怒之下,干脆把金船砸了、家什打了,这第一次“淘金热”也就这么没了下文。
但这事,终究像石子投进水里,起了波纹,也算是南溪金潮的第一声响雷。

三年后,1939年,国民政府直接出面,在南溪设立“采金处”,挂着“经济部采金局南溪区”的牌子,从上到下搞得热火朝天。
工程师、会计、矿警一应俱全,最旺的时候,河面上密密麻麻排了三百多条淘金船子,从大南门一直铺到瀛州阁。
民工自带船,每船四五人,每天三元二角工钱,伙食另算。
金子统一交收,不准私藏。有人说这是“救灾工程”,也有人说是“刮地皮”,还有人偷偷背沙回家自己淘,说不出几两金子,倒真能换碗热饭。
这场淘金热持续了大半年,淘出来的沙金不少,每天能收个两斤上下。
但金子多了,问题也就来了。
淘金人眼里是金,在某些人眼里就成了肥肉。
什么人会惦记上这块肥肉呢?自然是土匪。
四川自辛亥之后,战乱不断,兵散为匪,匪假为兵。

尤其川南一带,像泸州、南溪、江安、富顺、宜宾这些地方,土匪多得像田里的草,割了一茬又一茬。
这些人有退伍兵、破落士绅、袍哥兄弟,也有流寇赌棍、逃兵混子,有枪就能称头,有胆就能拉棚。
他们有自己的制度:大的叫“总棚”,小的叫“边棚”;头目叫“老摇”,管窝点的叫“坐地老摇”;还有跑滩、刀匠、棒老二,层层分工,比衙门还讲规矩。
他们也有自己的黑话:“吃饭”叫“造粉子”,“走路”叫“勾”,“抢人”叫“捞票子”,“杀人灭口”叫“撕票”,官兵来了,就说“涨水了”。

有人说他们是匪,其实他们早就是另一种“地下政权”。
匪患太多,官府抓不过来。
有的干脆私底下和匪讲好:你别抢我们乡,我也不抓你。更有甚者,有钱乡绅主动请本地匪来当“护寨”,外人不得入,肥水不流外人田。
这种局面下,南溪黄金厂在官面上热火朝天,在暗地里却早被匪人盯得清清楚楚。
而在这一张张望金之眼、磨刀之手中,有一个人已经动身了。
他就是后来搅乱整个川南、令无数县城夜不安枕的杨黑兽头。
第二章:杨黑兽头杨海清,泸县况场乡人,江湖人送外号“杨黑兽头”。
为啥叫杨黑兽头呢?
“兽头”者,四川土话里面就是“猫”,因为他面皮黑、眼神利、五短身材,天生一副猫样面孔,加上走路轻巧、身手灵活,乡里人私下都叫他“黑猫”。

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变成了“杨黑兽头”,名号愈传愈响。
不过杨海清起初不过是个苦命娃儿,小时家里穷,靠给盐商背盐过活。
那年头,背盐是条活路,也是条命路。
一次赶脚途中,他背的盐巴被土匪洗劫,东西没了赔不起,只得逃亡他乡,从此流落江湖。
后来经人介绍,进了区里团练队当兵,端起了枪。

杨海清是个能吃苦的人,别人训练一遍,他练三遍,不但枪打得准,还学了些拳脚功夫。
常有人说他百步穿杨、夜行如猫,能一跃上房,飞檐走壁,虽然有几分夸张,但也真有两下子。
再后来,他嗨了袍哥,投了况场乡有势力的“义”字舵爷陈福舟为“恩兄”,在袍哥里混成“三排”。
江湖上开始叫他“杨三哥”。

那几年,川南枪匪横行,杨海清当兵,也常与江湖上那些浑水袍哥(土匪、棒客)打交道。
打是打,交情还是有,有些匪人怕他枪快,也敬他仗义,暗地送些钱物交好。
一来二去,杨的心就动了。
他看得明白,当团丁拿三吊钱,不如干一票大的。
于是不到一年,他带着五六个弟兄,带枪出走,正式干起了土匪勾当。
投了山的杨海清,很快在绿林中间站稳了脚。

靠着一杆钢枪、那身轻功、还有不薄的江湖道义,他四处结交,打东家、掠西家,专拣有钱的下手。
他有个规矩:四邻不动。
“不吃窝边草”是他嘴上常挂的口头禅。他也不是光说,有时手下弟兄在本地作案,被他知道了,当场训斥,甚至赶出棚口。
乡里百姓见他如此,有的反倒感恩,谁家有病有难,他还真送点米送点银,一面做匪,一面做善人。
可一旦出了自己那几条村,他下手就狠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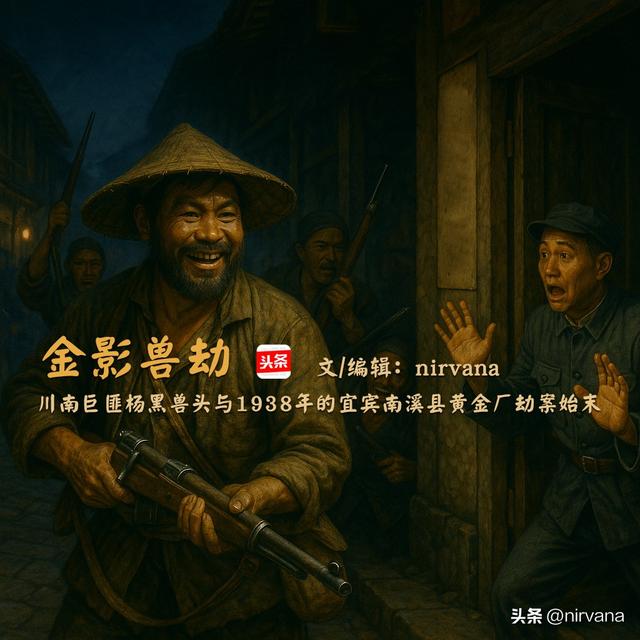
1936年四月,杨黑兽头带人突袭富顺县城,先把街口要道堵住,再对空鸣枪三声。随后一声喊“抓卖客”,三十多匪徒蜂拥进城。
县团练局首当其冲,被他夺了二十余杆长短枪和千发子弹,团丁被堵在屋里,动都不敢动,等他人走了,才敢追几步装样子。
同年秋天,又是一票。

这次,他率匪突入江安县城,强行攻入团防局,击毙一人、伤一人,夺枪七支,子弹十多带,还抢了三千多块公款,走得干干净净。
县里虽急电上报,但追兵没追到人,反倒让杨的威风传得更广了。
一时间,川南一带,只要一提“黑兽头”,老百姓就不敢吭声,妇女小孩一听名字就吓得往屋里钻。
而江湖上更多的是另一种传言——说他枪打百步百中,说他夜里能窜三墙不沾地,说他劫县如探囊取物,是“棒客里的阎王爷”。
杨手下的匪众越来越多,边棚也一个个归顺,投他旗号。
不到两年,已经是拥有十多棚口,人枪数百余的川南大土匪头子。
第三章:南溪县黄金劫案与洗劫纳溪县城杨黑兽头这一辈子,干的恶事不少,但真正让地方当局铁了心要“除掉此人”的,有两件大案。
第一件,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南溪县黄金厂被劫案。

此时正是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了筹措军费,在四川境内广设采金机构,南溪因地处金沙富饶的长江支流——瀛州坝一带,自然又成了重点采金区域。
那时候金子是国家命脉,一边在前线打仗,一边在后方挖金,金越多,枪炮粮饷就越有着落,于是国民政府“经济部采金局南溪区”牌子一挂,采金破坏风水的论调也停了下来。
南溪这处沙金厂,由当时余会堂师负责主办。
最热闹时,金厂日夜轮班、灯火通明,几十条船子淘金,工人上百人,一天能出几两赤金。
按说防守也不算松,县里专门拨了赵志刚中队的一分队驻守。
可这队伍,说起来是保卫金厂,其实不过是个“空壳子”。

带队的叫熊荣生,好吃懒做,嗜赌成性,三天两头泡城里,队伍没人管,久而久之,兵也跟着学样:有的跟民工玩钱局,有的干脆和土匪暗通消息。
杨黑兽头的手下,看得清清楚楚。
当时他的“大管事”张海清(绰号“跳烟灰”)已经潜入金厂附近多日,专打听“哪天存金多、哪晚守兵少”。
到了1938年8月的一晚,杨黑兽头亲自带人,趁着夜深露重,直奔金厂。
门岗被一枪撂倒,另一个也跟着中弹倒地。

整个厂区还没反应过来,匪徒已经蜂拥冲入库房,一口气卷走黄金上百两,连沙盆、半成品金砂也一起带走。
这事一出,南溪县震动,全川南炸锅。
这可不是普通抢案,这是打到了政府金库的脸上。
国民政府保安部立即下令,第七区保安司令限期捉拿凶匪,川南各县张贴通缉榜文,悬赏捉拿杨黑兽头。
但问题来了,杨匪不是普通匪。他耳目众多,消息灵通,匪徒藏在各行各业:茶铺伙计、渡船艄公、收粮的、打铁的,全是眼线。
他本人更是神出鬼没,夜出昼伏,深居简出,平日连部下都见不到人影。
这一仗下来,熊荣生先是被停职,后来干脆被以“擅离职守”罪名关押判刑,坐了几年牢;

两名士兵——余洪文和郑三元——因案发前逃跑,案后又回来找“饭碗”,也被认为与匪勾结,被一并关押;就连自卫总队副总队长李维树,也因“领导不力”,被宜宾专署撤了职。
而在金厂抢案之后,杨匪并未偃旗息鼓,反倒接连活动。
1938年9月,纳溪县团防局在清乡过程中,抓到两名杨匪的亲信,关进监狱。
杨得知后,不但不避风头,反而派人刺探到一个更大的“肥头”:合江县的一笔筑路款,正存放在纳溪县衙门里。
于是他一不做二不休,带着各边棚匪众上百人,干脆直接洗劫县城。

9月29日深夜,杨匪人马包围县署,打死门岗四名,炸开监门放出囚犯,直冲税务所、财政局、商号店铺,大肆洗劫,一夜之间抢走税款6008元。
连街上百姓都没逃过,衣裳首饰被扯得七零八落,家家门窗紧闭,县城整夜灯火不灭,全城百姓如同惊弓之鸟。
纳溪县长为此被记大过一次,县团防局更是被省上“下死命令”:一个月之内,必须把杨黑兽头抓回案下,活的死的都要结果。
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围捕杨黑兽头的“天罗地网”才正式张开。
第四章:一件大衣锁定内鬼,顺藤摸瓜但是在洗劫纳溪县城的时候,杨黑兽头在混乱当中,犯了个大错。
他们不慎遗落了一份内部名单。
这份纸条落入纳溪县团防局手中,上头写着几位参与匪首的代号,其中两个最引人注意:一个叫“万五”,一个叫“喻昆”。
这两个名字不是本名,官府一时查不出具体是谁。
不过,经过多方走访,地方情报人员打听到了一些头绪,说这两个代号可能与泸县况场方山一带的人有关。

为了查清这人是谁,团防局局长龙达远亲自带队,点了几名干员,还带上县保安连的连长——杨万五,一行人直奔方山搜捕“喻昆”。
搜了两天一无所获。
临回县途中,杨万五主动邀请龙局长到他家歇息,说是顺路,也好招待一顿热饭。谁知这一脚,反把自己送了进去。
龙达远一进门,眼光就落在床头的一件皮大衣上。那件大衣颜色、款式太眼熟,走近一瞧,居然是自己在纳溪县署遭匪洗劫时遗失的那件。
局长脸色一沉,当即变脸下令:“拿下!”
杨万五被押往五县联防指挥部戴碑寺,由主任张乃根亲自审讯。
起初杨万五嘴硬,死活不认,反问:“你说这是你龙局长的大衣,有凭证不?”
龙达远冷冷一句:“你拆开领口自己看。”
原来龙达远的大衣领口里面是写着他自己的名字的,众人一拆,三字露出。
于是人赃俱获,已是铁证。

在事实面前,杨万五只能认罪。他交代:这件大衣,是洗劫之后分脏得来的。他本是杨黑兽头的部属,平日里坐地分银,也分得大件物品。
更关键的是,杨万五供出:“真正知道杨匪藏身处的,是喻洪顺。”
这才揭开“喻昆”真名——喻洪顺,乃是杨海清的老表兼弟兄。
不日,喻洪顺被捕归案。经连夜审讯,终于招出:杨黑兽头正藏在富顺县琶琶场太阳山凤子坡一户农家,化名‘周一顺’。
保安大队当即派出便衣队员前往富顺侦查,并最终摸清了杨匪潜藏的具体位置和出入的道路情况以及人员动态。
几人回来后,汇报了情况,保安大队经过缜密的部署计划,最终决定选择在除夕之夜动手。
第五章:除夕夜,周大哥的真面目除夕之夜,万家灯火。
是夜,三更时分,山风刮得紧,天地一片寂静。

保安大队悄无声息地包围了杨匪的住所。两个着便服的保安队员潜至屋前,敲门低唤:“杨三哥在家不?”
屋里传出警觉的回应:“哪个?”
外头答道:“我们是来给三哥拜年的兄弟伙。”
屋内停顿片刻,一人应道:“你等一哈。”
紧接着,“咔嚓”一声,门闩响动。昏暗中,一名男子边提裤边拉开木门。

便衣队员定睛一看,见那人腰间一动,以为他要拔枪,不容分说,拔枪便射。
枪声震破夜色,那人应声倒地。电筒一照,才发现——死者并非杨黑兽头。
屋里顿时一片死寂。
片刻后,里屋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
“恭喜,恭喜你们。”
说话的是杨海清本人。
他知道已无退路,走出屋来,双手抱头,俯首就擒。他这一生狡如狐、狠如狼,终究还是栽在除夕夜这声“拜年”里。
后经查验,被误杀的那人,竟是杨海清的舅子——钟中士,本名已不可考,曾在保安队任职,后投奔杨匪,自愿担任贴身守卫。
杨海清被捕的消息,很快在太阳山传开。

可让官府意外的是,村里不少百姓竟还为他写了联名保状,要求“宽大处理周大哥”。原来这些年里,他在山中低调潜伏,时常送米送油、挑水补屋,假意周济邻里,装得极像一个本分的庄户人。
而当官府揭示他真实身份——正是劫金洗城、枪杀士兵、通缉多年的“杨黑兽头”杨海清时,众人一片哗然。
有人惊叹:“周大哥竟是他?”
那份保状,第二天一早就被群众自动取回,再无人敢提一句“保”。

几日后,杨海清被押解回泸州。因传言其兄弟伙欲劫法场,泸州当局悄然策划处决。
临刑当日,泸州本无空袭,却突然响起了防空警报。
全城百姓听声避入地道、屋檐,误以为日机来袭,街巷一时空空。

就在这混乱中,军警趁机将杨黑兽头从大北街监狱悄然押出,送往长江与沱江交界的管驿嘴,就地枪决。
无宣判,无围观,无惊呼。
一个搅动川南多年的土匪头目,一名打劫黄金的亡命之徒,就此悄无声息地埋骨江边,终结了他的“兽道”。
而那座被他洗劫的金厂,早已人去楼空,沙金耗尽,滩头荒草丛生。
只留下一个名字,至今在南溪、泸州、江安一带的老人口中,还偶尔低声提起:
“黑兽头”——那个能飞檐走壁、百发百中的人,终究还是死在了一件大衣和一句拜年里。
参考文献:
廖宾儒:南溪三次淘金概况
包君甫:南溪采金的部份情况
周荣瑜 廖宾儒:国民党统治时期南溪的地方武装
秦中南:川南惯匪头子杨海清(黑兽头)落网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