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年度艺术人物”是《库艺术》媒体延续了十六年时间的经典专题品牌,已然成为一年一度业界的关注焦点,同时,“年度艺术人物”也见证了中国当代艺术的潮起潮落。2023年,我们选择不再仅仅关注展览、奖项等等外在光环,而是在这一特殊时间节点下去观察艺术家真正的学术推进与创作进展。在AI时代的浪潮下,人工智能的出现无疑给人类带来了便利和发展机遇,但在发展迅速的表象背后也将面临着相应的危机与挑战,艺术领域同样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体现在艺术创作的技术手段上,更在于艺术家们对于艺术本质的思考与理解,如果艺术家不能在个人方法论和观念上有所推进与更新,其艺术将面临失语和无效的危险。 今年共有 16 位艺术家入选《库艺术》“年度艺术人物”,他们对时代有着深刻洞察,以创造性的工作打破界限,不断刷新人们对于事物的固有认知,并在开放性的工作中不断自我更新。可以说,在这个不断变动的时代中,他们是最能够诠释艺术的存在意义与价值的艺术家。
年度艺术人物推荐词
ARTISTS OF THE YEAR
看张恩利的作品,这个人必须足够有耐心。要给观看足够的时间以及想象力,让目光和画布之间产生足够的摩擦力,让意识抵达并流连于画布——感受到线条的速度和转折,体会到意识的凝聚和游走,才能够让所经历的观看和召唤的情感,在观看者的身上渐渐成形。这是张恩利创造的一种新的关于肖像的语言,一份关于意识的万有引力。
“年度艺术人物”个案研究
张恩利
从凝视走向流动
——关于意识的万有引力
FROM GAZE TO FLOW
文 / 沈奇岚博士

“那是一个可以克服重力的世界,一种摆脱图像和逻辑重负的绘画表达。”

"张恩利:肖像"和美术馆展览现场图片
©和美术馆
摄影:刘相利
张恩利是如何一步步走向如今的抽象绘画的,这是个吸引人的命题。毕竟他是那个画了惊人的《两斤牛肉》的艺术家,还有那些烟火气腾腾的群像,那些欲望饱满的脸庞。
张恩利是个富有耐心的人。他为此做了多年的准备。他深入地研究了线条,从皮管到电线,他知道如何用一根线条支撑住巨大的画面,同时无比饱满。张恩利研究过各种曲线和人的心理的对应关系。线条在画面上可以形成的心理空间,他对曲线的曲度跟人的紧张程度了如指掌。他探索了无形之物之间的万有引力:无形的重力、紧绷的薄膜、黄昏时分的咖啡座、视觉上令人迷惑的马赛克水槽。他发现了画面上重要的是存在,而非物件。他想对抗肖像的确定性,他探索了“容器”,他探索了“空间绘画”。
从凝视走向流动,在张恩利历年的创作中,有迹可循。观察他在十年之间创作的五幅关于球的作品,可以摸索出他的探索轨迹,他如何抵抗了对图像的迷恋,如何在画面上创造新的存在。
 球布面油画180 × 160 厘米2007
球布面油画180 × 160 厘米20072007 年,张恩利创作了《球》。那是在一个金属的球框里,十来只球静静地堆叠在了一起,屏息凝神。凝视是对这幅画的观看之道。2012 年,《大球和小球》。三只大小不同的球被放在了一个具有透视效果的平面上。尽管画面上的球并未滚动,但气势逼人。球体依然有着阴影,在视觉上,画面上的线条和物体依然遵循着某种逻辑和绘画规律。

大球和小球
布面油画
250 x 300 厘米
2012
2016 年,他再次画球,是红黄蓝三色球《不明物》。三只球的外延被一根线条相连,互相牵引,处在某种运动平衡之中。这三只球已经被平面化为三个圆形,但它们依然需要一根外在的线条将它们以某种形式联系在一起。那是一根心理上的线,在视觉上承载并托住了三个球之间的关联。

不明物①
布面油画
160 x 180 厘米
2016
再后来他又创作了一幅《铁匠》,仿佛是他把 2007 年的《球》中的球框猛然抽走,里面所有的球向四处滚落而形成的图景。这幅作品上,每一只球有着自我的意志,从画面向观众涌出。这一刻,球战胜了无形的重力,获得了自由,这些色彩和圆形成为张恩利自己的语言和词汇,不再听命于外在规律。已经不再需要外在的线条,球拥有了自由意志在画面上四散,也在观看者的心中四处滚落。张恩利掌握了画面空间和观者的心理空间之间的神秘呼应。

铁匠
布面油画
200 x 180 厘米
2017
2017年,张恩利创作了《建筑工人》,在画面上,是许许多多个球和圆形,是运动中的圆形。这幅画面可以联想为俯看中的许多人的头顶,也可能只是一些简单的圆圈,充满着流动感。此时,他已经掌握了对无形之物的牵引。
把球筐抽走,成为自由的点和色彩,球在张恩利的笔下拥有了自己的浮力和轨迹,摆脱了传统透视和重力的控制,从具象的指涉关系的世界解放出来,拥有了一种自己的节奏。那是一个可以克服重力的世界,一种摆脱图像和逻辑重负的绘画表达。
张恩利说:“我要用一种看不见的规则创造完美。”他要赋予一只球以自由意志,从凝视走向流动。由此,他把绘画带入更深的海域,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觉感知。这是对“面具”符号的拒绝,是对图像占统治地位的艺术创作提出的回应。

“神游时刻是张恩利在画面上一再重访的时刻,在人物状态的内部游走,是他从凝视走向流动的关键。”
 张恩利在工作室版权所有:港口杂志摄影师:徐晓伟编辑:郭爱
张恩利在工作室版权所有:港口杂志摄影师:徐晓伟编辑:郭爱对无形之物的兴趣,在张恩利早期的绘画中就已经埋下了伏笔。在他的三联《少女》(1999)中,三个穿着高跟鞋的女性陷入了沉睡之中。这幅作品在艺术家的创作中,常常被归类于他同期所创作的都市众生相的系列。但这件作品与众不同,作品中的人物处在了一种临界状态。沉睡是一种神秘的状态,一种介于富有自我意识的清醒与毫无意识的死亡之间的状态,沉睡是一种十分轻盈同时紧绷的状态。这种状态是张恩利在创作《少女》时真正的主体。画面上的红色与蓝色的高跟鞋和女性饱满的身体,透露着被描绘者旺盛的生命力,但此刻的她们陷落在了椅子之中,陷落在了沉睡之中,她们的生命力被沉睡包裹,被画布包裹,她们的存在因此拥有了某种流动性,下一刻她们可能醒来,成为拥有鲜明性格的人物,犹如张恩利其他画面上的那些张扬的人物。但此刻《少女》中的人物依然处在混沌的神游时刻,她们拥有无限的可能。这种神游时刻,是张恩利在画面上一再重访的时刻,在人物状态的内部游走,是他从凝视走向流动的关键。

 “张恩利:表情”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图片©龙美术馆摄影:shaunley
“张恩利:表情”龙美术馆(西岸馆)展览现场图片©龙美术馆摄影:shaunley这件《少女》让我想起了西班牙艺术家戈雅对沉睡者的描绘,那幅《The Sleep of Reason Produces Monsters》(1799《理智入睡催生梦魇》)上也是一个沉睡者。戈雅的画面上,人代表着理智,理智的沉睡时刻,空中升腾出各种奇兽。戈雅同样意识到沉睡是某种临界状态,他对临界状态的刻画与捕捉如此惊心动魄。在张恩利的创作过程中,他曾对蒙克和德拉克洛瓦等对绘画有深刻理解的艺术家做过细致的研究,包括创作了一幅《仿德拉克洛瓦作品中一个死者的形象》。他探索着绘画中如何描绘不同状态下的身体,或者如何呈现身体的不同状态:生机勃发的、沉睡的、失去意识的、仅作为物体而存在的肉身。在不同的探索中,张恩利找到了张力最大 的神游时刻。他近期的抽象绘画,是一次又一次神游时刻的降临。观众的意识进入他的画面,无论是《骑白马的男子》,还是《独行者》,观众的想象被张恩利的画笔牵引,进入一次次的神游。作品邀请着观众的意识进入不确定的旅程,在沉睡和清醒之间迷路,在每一次重新寻找中得到新的发现和启示。

骑白马的男子
布面油画
210 x 350 厘米
2023
我想起布罗茨基如此定义诗人:“写诗的人写诗,首先是因为,诗的写作是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的巨大加速器。一个人若有一次体验到这种加速,他就不再会拒绝重复这种体验,他就会落入对这一过程的依赖,就像落进对麻醉剂或烈酒的依赖一样。一个处于对语言的这种依赖状态的人,我认为,就称之为诗人。”布罗茨基对诗人的状态的书写,也可以描述张恩利在画布上追寻存在的创作状态,他综合着意识、思维和对世界的感受,在画面上挥洒画笔是他的加速器,他体验到了这种加速,他踩下意识的油门,让这种加速驰骋于画面。这是艺术家最痛快的创造时刻,他要一次次重返这样的时刻,这是推动他不断创作的源泉。


“张恩利的画面内部,是不可见之物在支撑着视觉和心理的感受。”

"张恩利:肖像"和美术馆展览现场图片
©和美术馆
摄影:刘相利
张恩利的肖像创作,从凝视到流动,是对人类感知能力的召回,他对肖像的探索,扩大了观众感知的潜力。让人好奇的是这份对感知的扩大是如何形成的。这又是一个吸引人的命题。
当我们的观看从询问“画的是什么”解放出来之后,就可以更好地进入绘画的内部空间。哲学家梅洛·庞蒂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一书中,说道:“这些不可见之物构成了可见之物的深处,并支撑着各种可见之物。”张恩利的画面内部,是不可见之物在支撑着视觉和心理的感受。在流动的画面中,张恩利拆解了凝视。随着观看时间的加长,观看者产生了目光的滑动和心理意识的调度与流动。目光和意识在线条上会遭遇速度上的减速和加速,在色彩上会遭遇撞击或共振的戏剧性,由此增加了心理感受的丰富性。赋形是艺术家的特权,艺术家和无形之物的共舞,形成了画面上的独特存在。张恩利的画面是感性驱动的。他感受涌动,感受一个人在时间和空间中留下的印记,当这些涌动在张恩利的心中发生作用时,他果断地拿起画笔,在画布上追逐这些涌现的意象和感受,那是他对所绘对象的生命直观感受。画布上的色彩和线条,构成了一种拥有自身属性和引力规则的“视觉和弦”,和弦的作用不在于具体指涉某物,而在于激起观看者心中的涟漪。没有具体的对应物可以参考,观看者必须激发心灵的想象力——我们在张恩利的画面上,一次又一次地凝聚意识,被他的画面推动着进入新的感知和想象。每一次得到的感受都不同。当画面拥有了流动的意识,就拥有了无限的可能。比如《灰鹦鹉》是一件易于感受的作品。画面上的线条可以理解为灰鹦鹉曾经飞翔的轨迹,可能是它的翅膀扇动的轨迹,或是涌起的气流。“天空没有痕迹,但鸟儿已经飞过”,张恩利将那些流动的痕迹捕捉,成为灰鹦鹉的肖像。

灰鹦鹉(二)
布面油画
250 x 200 厘米
2017
另外值得探讨的张恩利作品的两个维度,是命名与时间。张恩利对作品的命名,寻找的是词语形成的那一刻(命名时刻),是事物在意识成形的那一刻。他寻找的是词语内部和画面之间的能量张力,他完成的是对观众的意识的牵引。命名创造的引力,是作品的构成维度之一。
在张恩利的抽象绘画中,充满了许多的“小时间”与“微叙事”。关于“小时间”(small time)的概念,来自学者阿尔弗雷德·艾克斯(Alfred Acres)的《微型物质史:早期尼德兰绘画中滴水般的往昔》(2002)(参考见巫鸿的《豹迹》中的分析,画家魏登的作品中基督的血和周围人的泪让画中的时间不再是基督生平事迹的“传记时间”,也不是这些事迹的“故事时间”,而是一种更细致的微观纪录,拥有了自身的时空维度。)


"张恩利:肖像"和美术馆展览现场图片
©和美术馆
摄影:刘相利
张恩利近期的抽象绘画中,在不同的局部,线条和色块之间,会形成自己的引力和某种时间结构,这形成了一种“小时间”,同时构成了一个“微叙事”(micro narrative),这一部分与画面的其他部分的时间节奏明显不同,但又被一种更大的引力统摄着,形成紧密的关联。在这些不同的小时间中,整体的画面拥有了一种折叠式的时间结构,不仅在视觉层面,也在心理层面完成了一种拓扑结构。这是观看者意识游走的迷宫,也是画面与感受得以无限延展的秘密。

建筑工人
布面油画
200 x 250 厘米
2017
具象作品总是默认它的图像拥有一种共时性,共识性提供了确定性。这是张恩利一直在默默对抗的确定性。比如他在绘画马赛克水槽时,惊喜地发现马赛克瓷砖在画面上既是线条和形式,又是结构本身。水槽的显现和消逝同步发生,“它既在又不在”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复杂性,在时间的向度上成为不可能的结构,这恰恰是艺术的迷人之处,作品内部的时间结构拥有了新的复杂性。这是张恩利追求的“用一种看不见的规则创造完美”。他可以用线条和色彩,把存在从被禁锢的图像功能中赎出来。这的确是一种突破。
这种特殊的时间结构形成了张恩利内在的图像的节奏感,是他创造的独特的视觉和弦,观看者由此完成了一次次的视觉与心理感受的凝聚。
张恩利在画面中继续创造意识的万有引力——继续把观看者脑中的球筐抽走,他们的想象力可以无数次潜入画中,与万物同游。
 艺术家简介
艺术家简介 (张恩利在工作室 摄影:赵仁)张恩利Zhang Enli
(张恩利在工作室 摄影:赵仁)张恩利Zhang Enli1965 年生于吉林。1989 年毕业于无锡轻工业大学艺术学院,现生活工作在上海。
张恩利在世界各地的多个重要机构举办过个展,包括香港 Hause & Wirth 画廊(2024)、龙美术馆上海西岸馆(2023)、和美术馆(2023)、龙美术馆重庆馆(2021)、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2020)、苏黎世 Hause& Wirth 画廊(2020)、比利时霍夫肯画廊(2019)、意大利博尔盖塞美术馆(2019)、上海 K11 艺术基金会(2019)、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2018)、纽约 Hause & Wirth 画廊(2018)、英国 Firstsite 美术馆(2017)、台北 MOCA(2015)、香格纳画廊(2015)、伦 敦 Hause & Wirth 画 廊(2014)、 香 港KAF(2014)、意大利 VILLA CROCE 当代艺术博物馆(2013)、伦敦 ICA(2013)、上海美术馆(2011)、上海民生现代美术馆(2010)、Ikon 美术馆(2009)以及瑞士伯尔尼美术馆(2009)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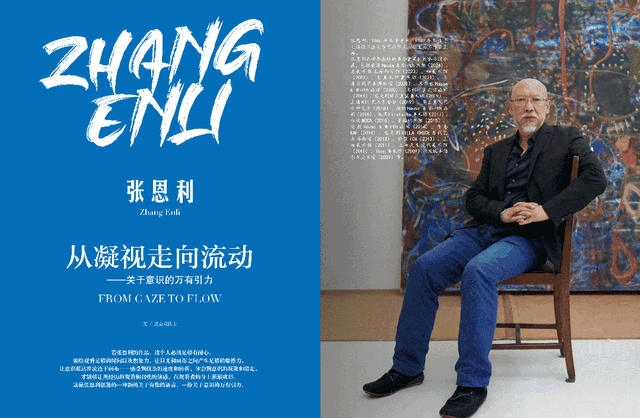 ◎《2023年度艺术人物·存在与超越》张恩利个案研究文献图书出版*Copyright © KUART.All Rights Reserved.“2023年度艺术人物”专题策划内容由《库艺术》KUART原创,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转载,否则权利人将根据知识产权法追究法律责任。
◎《2023年度艺术人物·存在与超越》张恩利个案研究文献图书出版*Copyright © KUART.All Rights Reserved.“2023年度艺术人物”专题策划内容由《库艺术》KUART原创,任何单位及个人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转载,否则权利人将根据知识产权法追究法律责任。绘画创作者为什么需要补这一课?
Why do painting creators need to make up this lesson?
德国现代绘画课程 “格式塔命题创作:绘画性研究” 专项课题研究线上工作坊 特邀导师:乌尔里希·克里博(德)、张一非线上课程启动时间:2024年3月16日课程时长:6周(每次课程时长3小时)授课形式:1,周六、日晚腾讯会议面对面实时交流与创作点评2,周一到周五群内就有关问题交流及课题作品指导3,当日课程回放(一年内无限次观看) 长按或扫码立刻报名 报名微信:kuyishu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