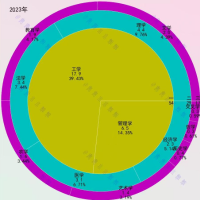本篇以河北省廊坊市大厂回族自治县的景泰蓝工艺为背景虚构创作。
明景泰七年,京畿大厂,御窑瓷器烧制的重任落在了匠作头领林守义肩上。
彼时,景泰蓝风行宫廷,器质厚重,釉色深幽如夜。
这年,皇家下旨要烧制一对罕见的蓝釉瓷瓶,"宝瓶盈光润如玉,蓝釉点霞映丹青",质地需柔中带韧,釉色更需如海水幽蓝。
林守义为此日夜操劳,却因连月天青窑火不旺而愁眉不展。
这日深夜,林守义端坐窑前,忽然听到一阵若有若无的低语声,仿佛有人在他的耳边呢喃:"火候若差一分,釉水添五毫......"
他猛一抬头,却只见到密不透风的窑房内空无一人。那声音飘渺而清晰,仿佛穿透了岁月。
他急步走到窑炉前,却发现窑火中隐约有道若有若无的影子,宛如初唐水墨画中的青蓝轮廓——那身影似在拨弄炭火,动作却与他完全不同。
翌日清晨,他在作坊里无意间翻到了一本布满釉痕与霉斑的古册,上书:
"大厂青釉技自唐,天青转青幽为魂......宝光蓝焰自幽生,釉影留形传古意。"
册页最后绘着一尊模糊的孩童影像,头戴青釉莲花冠,双手捧宝瓶,眉目间笼着幽蓝的釉彩。
林守义忽然忆起祖父曾神秘提过,这窑场曾有一个"青蓝釉童子"的传说,守护釉料配比与火候的秘方,代代只传头领。
传说中,这个孩童并非凡人之躯,而是窑火百年的凝精。
林守义半信半疑,却隐隐感到,那夜窑前的人影与这本古籍存在某种联系。
为了试一试,他将制好的蓝釉瓷瓶置于案上,用柴火余烬点燃,用青釉矿粉轻轻涂抹在瓶身,随后在漆黑中默声祈祷:"若有灵,可许我烧成大器,不负家国?"
随即转身退下,却在耳畔清楚听见一声仿若细雨般的细语:"火柔釉凝,心静瓷生......"
他猛然回头,只见釉彩渐次流淌,光影中似有青釉莲纹在瓶身浮影闪现。
当晚,林守义于恍惚中再入梦境。他见古籍中的孩童站在青色釉波的涟漪中招手,那孩童竟朝他露出了如儿童般天真的笑容,随即用小指点了点那瓶身,轻声说道:
"你可知,这幽青蓝釉需渗入风,你父曾烧不出,因他拘泥于瓷土,而忘了风中釉的魂。"

言罢,青釉童子将瓶举起,轻撒釉彩于蓝光中,刹那间,梦中天光大亮,整个天地仿佛被釉彩填满,他醒后就觉灵感如泉涌。
他重新调整配方,以古法制蓝,将釉料炼制后晾干三天,又加入些许"风釉土"——大厂独有的矿土,据说含风之灵气。
第三天清晨,他亲眼见矿土中散出幽幽蓝光,如满天星辉映射到釉水中,蓝得如梦如幻。
随后,他将瓷瓶放入窑中,严密封门,这次并没有心急如焚守在窑边,而是走到窑房外,对着青空长吟:"愿釉如青天,不愧大厂魂土也!"
三日后开窑,林守义刚掀开窑门,忽觉鼻尖掠过一阵凉润之意,抬眼时,他竟看见一抹淡青色的光晕萦绕在出窑的蓝釉瓷瓶上,瓶身上的青蓝釉流光溢彩,宛如有青蓝雾气在瓷胎上徐徐流动,连釉光都似乎带有灵性。
他轻轻拨动瓷瓶底部,忽然听到一声细微如叹息的声音:"釉心归位矣......"
当夜,青蓝釉童子的幻影再现作坊,孩童笑着指向瓶身:"我守的,是大厂瓷魂。唐代的青釉融于景泰蓝中,宝光凝魂,方能成器。你若有心护这血脉,这釉可世代相传;若有心贪功,连风釉之灵都将散去。"
林守义伏地叩首,郑重说道:"守义愿世代护宝,不私藏一丝天机!"话音未落,青光忽散,古法烧成的宝瓶在幽蓝光线下恍若神物,似还在轻轻颤动,与天地呼应。
自那以后,大厂的景泰蓝独步天下,无论形制抑或釉色,皆堪称极品,而窑火每逢夜晚,总有淡淡的青蓝色釉光飘动,仿佛有人仍在守护着这传世秘艺。
后人传言,那青蓝釉童子虽无形体,却将瓷魂凝聚在每一尊"大厂之蓝"中。林氏匠作世家的后人只要抚摸瓷瓶,还能在耳边听见低语:"火候深一分,青釉即裂;心急一分,宝光尽失......"
岁月流转,朝代更替,但大厂景泰蓝依旧流传千古,甚至官窑瓷瓶上的幽蓝釉纹偶尔也会显现那捧宝瓶的孩童浮影。
工匠们都说,那是青釉童子的化身,为守护这片窑火而凝。至于匠人家族,始终守着这个约定,从未有人妄图私占"风釉之术",只为延续这来自唐代的蓝色遗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