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这个人工智能、信息爆炸的时代,艺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前所未有地得以展现。然而,这也使得众多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淹没在浩瀚的艺术海洋中,难以被专业机构以及大众所认知。为此,我们特意策划了“星丛”这个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关注到这些新锐艺术家,为他们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本专栏中,我们将通过深入访谈、作品解读、创作过程揭秘等多种形式,带领读者走进这些新锐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创作激情与艺术追求。他们的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当代艺术的多元面貌。这些艺术家们不仅拥有扎实的艺术功底,更在创作上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创新,为当代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我们相信艺术的力量能够跨越时空,连接心灵。让我们一同期待这些艺术家们在未来的精彩表现吧。
在这个人工智能、信息爆炸的时代,艺术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前所未有地得以展现。然而,这也使得众多优秀的青年艺术家淹没在浩瀚的艺术海洋中,难以被专业机构以及大众所认知。为此,我们特意策划了“星丛”这个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关注到这些新锐艺术家,为他们的成长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在本专栏中,我们将通过深入访谈、作品解读、创作过程揭秘等多种形式,带领读者走进这些新锐艺术家的内心世界,感受他们的创作激情与艺术追求。他们的作品涵盖了绘画、雕塑、装置、影像等多种艺术形式,充分展示了当代艺术的多元面貌。这些艺术家们不仅拥有扎实的艺术功底,更在创作上敢于突破传统,勇于创新,为当代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挑战与机遇的时代,我们相信艺术的力量能够跨越时空,连接心灵。让我们一同期待这些艺术家们在未来的精彩表现吧。 潘禹成Pan Yucheng
潘禹成Pan Yucheng1989 年生于贵州遵义
毕业于云南艺术学院文华学院美术系
现生活工作于上海。

散-8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235 × 131 × 14cm
2024
“星丛”系列专访潘禹成:“水性”是我创作时的遵行之法,也是我的处世之道库艺术=库:能向我们介绍一下你的成长经历吗?潘禹成=潘:我是在西南地区的一座重工业基地长大的厂矿子弟,长辈都是在这里工作,这个工业基地像一个大镇,有数万人围绕着这座工业基地工作生活,身边的朋友和同学都是一模一样的出身,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都是在厂子弟学校,吃饭在厂菜市场买菜,看病在厂医院,我们的生活不需要和外界有太多接触,我就是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游-1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158 × 107 × 18cm
2023
 游-1(作品局部)库:你认为这些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潘:我在那种环境下首先是可能性的缺乏,就像我在刚才那个问题里面说到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轨迹几乎完全相同,不止是我自己,是整体性的认知雷同。伴随着由此带来的绝望,对将来要陷入的未知局面感到焦虑,长辈需要你循规蹈矩的生活学习,所以我的思想和生活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实不控制我们自己也很难想象出更多的可能性。我小时候都觉得长大大概率就是接替长辈继续去操作那些大型生产机械。
游-1(作品局部)库:你认为这些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潘:我在那种环境下首先是可能性的缺乏,就像我在刚才那个问题里面说到的,我们所有人的生活轨迹几乎完全相同,不止是我自己,是整体性的认知雷同。伴随着由此带来的绝望,对将来要陷入的未知局面感到焦虑,长辈需要你循规蹈矩的生活学习,所以我的思想和生活都受到严格的控制,其实不控制我们自己也很难想象出更多的可能性。我小时候都觉得长大大概率就是接替长辈继续去操作那些大型生产机械。
散-7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133 × 84 × 14cm
2024
小时候画画并没有想过以后会从事艺术,只是这是个不受重视的单元,在我那个环境里没有人会在乎和关心一个小孩画画的事情,这是一个被严格控制下被漏掉的一个环节。所以我在绘画这件事情上拥有无限可能性。当时我自己都没有觉察这里面的一些东西,其实到现在我才逐渐发觉这种不受控的生长反而是开放的出口。所以到后来我对于偶然性的东西比较感兴趣,偶然性的发生前提就是失控。任何事物只要和人连接都会作用到人,环境会塑造人,只是很多时候它不是显性的表现甚至是反向推动。
散-6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97×94×10cm
2024
 散-6(作品局部)库:你何时开始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家人支持你吗?潘:我也说不清怎么走到这上面来的。可能是在其他事上都没有什么感觉。几乎全靠家人支持,他们很难明白我在做的事,但是还是支撑了我很久,做艺术需要强大的内心,做艺术家的家人可能需要更强大的内心。
散-6(作品局部)库:你何时开始想成为一个艺术家的?家人支持你吗?潘:我也说不清怎么走到这上面来的。可能是在其他事上都没有什么感觉。几乎全靠家人支持,他们很难明白我在做的事,但是还是支撑了我很久,做艺术需要强大的内心,做艺术家的家人可能需要更强大的内心。
散-1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96 × 81 × 19cm
2023
库:请谈谈你现在的创作情况以及在实践中主要涉及的主题?潘:我做的创作我自己称为“水性”,我不知道这算不算主题,“水性”是我创作时的遵行之法,也是我的处世之道,有点像一种修行方式,是一种类似于魔道修行的方式,这个“魔道”不是在玄幻小说中所讲的那种魔道,这个“魔道”的内核是逍遥法,讲自在由我,是以庄子思想为基础的修行方式。想了解可以去百度“魔道”。而这个“水性”我解释一下,我们通常讲“水无常形”,水的变化是无限的,我们把一盆水泼出去,它会呈现出各种形态,你可以分裂它或者再融合都不会改变它,水的状态本身就是反结构的,它拥有无限可能性还永远都成立。
散-2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257 × 110 × 18cm
2023

散-2(作品局部)
库:你认为你的作品是雕塑还是绘画?这些作品最终将如何呈现?悬挂起来吗?潘:我不太去想做这个定义,定性就会有约束,这不符合我前面所说的“水性”。我只能说我是做绘画出身,所以作品总会有绘画的痕迹在里面。目前做的大部分都是可以悬挂的,而且大的作品因为是拼接的,在每次呈现都会出现变化,这也是我偶然发现的,也具有“流动性”的属性,我会故意在每次拼接的时候都随意改动每个部分的位置,每次重新悬挂都像一件新的作品,这很有意思。而且我现在在尝试做出更立体的不上墙的作品以及可以像藤蔓一样在墙上和地上蔓延的组合作品。
散-5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115 × 72 × 11cm
2023
库:你通过控制陶瓷石膏液的凝固程度来创作,这增加了很多不可控成分,你如何平衡偶发性与主观控制?什么时候这个作品才会最终停止(完成)?潘:虽说要让其处于失控的状态,但是只要人参与进去就不可能做到百分百的不控制,因为这个过程本身就是我选择的,选择本身也算是控制。 创作过程这又和创作者的敏感度相关,我的做法是尽量的不去做主观的控制,取舍交给敏感度,现在不都在讲创作的过程性讨论吗?我们这种类型的创作者的表达核心就在过程性讨论上,过程性就是我们抛开目的,不是去制作一件预设好的作品,而是按的敏感度在每一步做判断,一步一步的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那个环节被我的敏感度判断为终止它就终止了。我让其随机发展,但是发展的每一个小环节和最终结果的取舍由我来判断,我的主观性发挥就在这里。
创作过程这又和创作者的敏感度相关,我的做法是尽量的不去做主观的控制,取舍交给敏感度,现在不都在讲创作的过程性讨论吗?我们这种类型的创作者的表达核心就在过程性讨论上,过程性就是我们抛开目的,不是去制作一件预设好的作品,而是按的敏感度在每一步做判断,一步一步的做到某一个环节,然后那个环节被我的敏感度判断为终止它就终止了。我让其随机发展,但是发展的每一个小环节和最终结果的取舍由我来判断,我的主观性发挥就在这里。 创作过程我们的认知会通过生活中的各个部分被塑造,我们认识的人、读过的书、经历的事等等方方面面都是在塑造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敏感度判断自然就会建立。库:是什么事情启发或者决定让你采用这种创作方式?潘:这个也是慢慢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最开始是朋友买了几袋陶瓷石膏粉,本来是做其他东西的,但是失败了就闲置下来了,摆在我工作室很久,我没事就尝试把这些石膏粉兑水之后倒到各种现成容器中得到了各种陶瓷石膏块,我发现很有意思,就开始尝试用泥土随意捏各种形状的容器灌入石膏液,甚至直接在野外的地坑里倒入石膏液,又得到很多奇形怪状的石膏块,慢慢的画也不画了,天天就弄这个,然后就变成只做这个。
创作过程我们的认知会通过生活中的各个部分被塑造,我们认识的人、读过的书、经历的事等等方方面面都是在塑造我们的认知,我们的敏感度判断自然就会建立。库:是什么事情启发或者决定让你采用这种创作方式?潘:这个也是慢慢的发展到现在这个样子,最开始是朋友买了几袋陶瓷石膏粉,本来是做其他东西的,但是失败了就闲置下来了,摆在我工作室很久,我没事就尝试把这些石膏粉兑水之后倒到各种现成容器中得到了各种陶瓷石膏块,我发现很有意思,就开始尝试用泥土随意捏各种形状的容器灌入石膏液,甚至直接在野外的地坑里倒入石膏液,又得到很多奇形怪状的石膏块,慢慢的画也不画了,天天就弄这个,然后就变成只做这个。
散-4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110×106×13cm
2023
库:你如何理解“材料”在当代创作中的运用?潘:材料本身是一个中性的东西,为什么它又具有意义,这就要回归到“物”的层面,物的本质是中性的,物有物的自然属性和物理属性,但是人类通过观察和感受“物”的某些特质和现象,感悟到某些道理再进行思考,东方哲学往往就是采用这种方式。就比如我们在探讨东方思想时经常会说到的水,水就是“物”,水是实实在在的,西方思维大部分情况下会对水进行成分分析来认知水,水就是H2O,这是西方认识“物”的通常方式。他们认识是基于世俗化之后理性思维崛起的科学认知方式。但是在东方思想对于“物”的认知并不在“物”本身,而是感受“物”对外作用的现象。水的形态是抽象的,水无常形,水可以和许多其他的“物”进行连接,东方人通过对水的形态和水对其他事物的作用进行了许多的哲学思考,并把这些思考与人本身进行连接,这个时候“物”就开始作用于人。
雨-1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130 × 62 × 9cm
2023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说到材料的时候,材料本身就有它的特质了,因为它对“人”产生了作用,它变得不再中性。然后再说回创作上来,我认为作品和创作是两个概念。创作是一个动词,作品是名词。创作是我们被“物”影响再对“物”进行作用,作品是艺术家创作的产物。艺术家应该是思想的实践者,我们被传导的哲学思想也好自己的感悟也好应该是塑造我们的,当然,我们不是围绕这些概念进行创作,我们不能把思想工具化。既然思想是塑造艺术家的,并不是艺术家创作的目的,所以“物”本身也不应该是目的,所以材料就不是创作的目的,材料应该是和人相互作用完成创作的条件。所以材料应该和艺术家敏感度是同一种性质并融合的东西,就像画一张画,此处应该是一条曲线,那里应该是一片蓝色一样,它完全是由艺术家的敏感度在决定,它充满了生长性和不确定性,材料的选择也是艺术家敏感度的一部分,而作品是这些一些列敏感度的作用之后的产物。库:你目前在哪里工作,日常的工作室实践是怎样的?有什么惯例或信条吗?潘:目前在上海朱家角,日常就是普通的日常,创作者是思想的实践者。惯例或信条可能就是跟我的创作一样,要让它失控。“水性”不刻意的随意流动。前面不说了嘛,这不仅是做创作的方式,这是一种修行方式,先自己做到“水性”,然后自然会作用到创作实践中。库:近年你的创作方式有没有过转变,在工作方法上有哪些变化?潘:创作方式最大转变还是从绘画转变到现在综合材料。工作方法的变化要怎么说呢?无非也就是从架上绘画变成倒各种金属条和石膏液。更多的转变还是在观念上越来越成型了。
蔓延-3
陶瓷石膏/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120 × 125 × 14cm
2023

蔓延-3(作品局部)
库:你一直在坚持创作,当前艺术领域最让你兴奋的是什么?潘:我不太理解你说的当前艺术领域是指什么。对于创作者来说,做创作本身就让人兴奋。但是你又说艺术领域,艺术发展到现在已经到了一个瓶颈,很难有什么让人真正觉得兴奋的点,或者说现在我们要解决的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一直在说后现代,但是没有人能真正脱离现代性,不仅是艺术,许多领域都是这样,科学、政治制度、艺术等等,我们建立的最新的理论体系其实在几十年前甚至上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我们只是在把这些基础扩宽应用而已。我们现在的后现代艺术就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名字是新能源,其实内核都是很旧的。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流动”起来,跳出以往经验,如果非要说兴奋点,那就是现在我国年轻一代的艺术从业者有一部分确实是有批判性的,批判就是要打破以往结构。库:近期诞生的ChatGPT、Gemini等AI机器人更是可以在一个简单的指令下创作出无限复杂而准确的图像,您认为AI绘制的图像属于艺术创作吗?面对AI带来的“威胁”,人类艺术家应当作出怎样的回应?潘:Ai是工具,不是目的,如果我们把Ai当做工具使用,怎么不能算作是艺术创作?我们不要去管我们发出的指令多简单,它给出的结果又有多复杂。工具就是用来把麻烦的事情简单化的,就像远古时候人类只能用石头来刻木头,有了铁器之后可以用刀来刻,现在有各种电动工具可以使用,刻木头这个事情变得方便了。我们要的结果是刻木头,而不是去管具体用什么工具来刻木头。 游-2
游-2陶瓷石膏 /丙烯色/透明树脂/金属
99×86×19cm
2024
换到Ai来说,首先指令是需要由人发出的,这是关键,然后它所生成出来的信息还是由人运用敏感度来判断取舍,所以使用Ai完全能算做是创作。说到威胁,我不觉得有什么威胁,目前的AI还没有自主意识,它只能在人类以往的经验中做一些事情,虽然这些经验丰富度非常大,但终归是有限的,因为人类在训练它的时候喂给它的数据都是现有的数据,它只是有整合这些数据的能力。我们可以让Ai用梵高的绘画语言去画天安门,但是让它用一种世界上还没出现过的绘画语言来画一张画,它就做不到。也就是说它如果不经过人,它不具备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创造能力。至少是在目前这个阶段是如此。还有就是我刚才说的对于最终结果的判断取舍,Ai无法做这个判断,即便它能给出一个所谓的判断对人来说也是无效的。库:新的一年里你有什么展览或创作计划吗?潘:展览计划目前没有,这个也需要碰机会。创作计划就是做就是了,反正你不管怎么做,最后总会有一些作品。就像站在画布前面,不管怎么画,最后总会有一张画,先把这张画设计好再画还有什么过程性的讨论,你要让这张画带给你惊喜,你就得给它一些自由度,让它失控。 库艺术线上课程推荐 以一本书的价格 获取书中没有的现代艺术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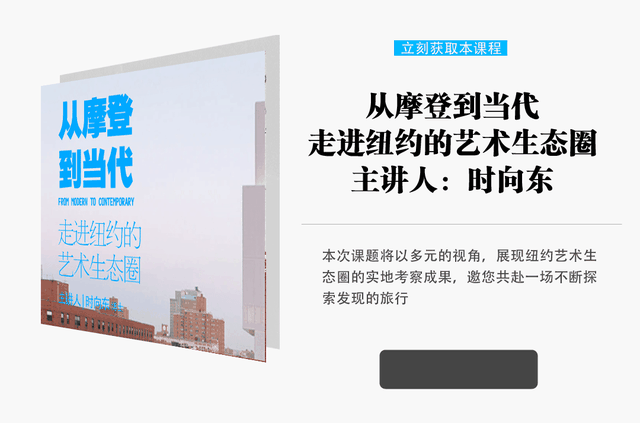
 《库艺术》新书推荐
《库艺术》新书推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