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隆中对》中诸葛亮对荆、益二州的天时地利、战略地位就十分看重。荆州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控制了这一战略要地,就可以四通八达,进退自如,统一中国、复兴汉室的战略目标,就有了实现的基本条件,失去了这一战略要地,就会陷于被动;对益州,诸葛亮着重是从战略后方、后勤、辎重以及历史的角度来考虑的。益州地势险要坚固,土地肥沃辽阔,物产富饶,人民富裕,地方富足,汉高祖就是凭借益州这些优越条件建立了汉朝的帝业。控制了益州,就有了巩固的战略大后方和充足的物资来源。进攻得有基地,立国得有国土,否则,就没有基本的立足点和生存条件,统一中国,复兴汉室,就成为空中楼阁。


在“天下有变”之时从荆、益二州出军争霸中原;“成霸业、兴汉室”。
选择两路伐魏的战略方向,历史上有成功的先例。汉高祖刘邦即以汉中、巴蜀为根据地,底定三秦,东向与项羽争夺天下;汉光武刘秀则奋起于南阳,昆阳一战大破王莽的主力,两帝最后俱能削平群雄统一全国。如果就现实情况而言,公元207年隆中决策之时,在一般人民心目中以“汉为正统”的观念还相当强烈,因而诸葛亮对刘备说:届时大军北伐,“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
《隆中对》规划的战略目标从关羽大意失荆州时注定无法实现。荆州丢失导致《隆中对》战略中途夭折,原先诸葛亮两路伐魏的战略计划变成了北出秦川一条路线。二是荆州丢失后,刘备意气用事,不顾一切地发动复仇之战,最后兵败夷陵,蜀汉不仅元气大伤,而且破坏了“外结好孙权”的外交战略,将弱小的蜀国置于同时面对两个强大敌人的境地。

1.荆州地区的当时的归属权问题
荆州本来是汉朝的,为汉宗室刘表统治,由于其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加上其主刘表为“外宽内忌,好谋无决” 的无为之辈,一时的野心家们没有不觊觎的,如东有孙权之垂涎,北有曹操之虎视,刘备寓居荆州也是蠢蠢欲动。
208 年,曹、孙、刘三家终于为争夺荆州展开了赤壁大战,战后荆州也为三家所分,赤壁战后,为巩固已得的荆州地盘,刘备与孙权进行了的明争暗斗,甚至不惜兵戎相见。
建安十三年(208 年)十二月,刘琦为荆州刺史,引兵南徇武陵、长沙、桂阳、零陵,四郡皆降。备以诸葛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以赵云领桂阳太守;建安十四年(209 年)十二月,周瑜攻占江陵,领南郡太守,屯江陵;程普领江夏太守,屯沙羡。刘琦病卒,刘备领荆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给刘备,备立营于油口,改名公安。权以妹妻备;建安十五年(210 年)十二月,刘备至京口见孙权,周瑜劝权留之。权以曹操在北,方当广揽英雄,不从。会周瑜卒,鲁肃代之,劝权以荆州(指南郡)借刘备,共拒曹操,权从之。;建安十七年(212 年),曹操攻孙权,权呼备自救。刘备却乘机进攻刘璋;建安十九年(214 年),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等入蜀,仅留关羽守荆州。是年刘备取益州;建安二十年(215 年),孙权遣诸葛瑾从刘备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权遂置长沙、零陵、桂阳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遣吕蒙取三郡,刘备引兵五万下公安。正当双方大战一触即发之际,曹操乘机攻汉中,刘备惧失益州,遣使求和于权,权亦遣诸葛瑾报命,更寻盟好,遂分荆州,以湘水为界: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

汉末十三州
2.蜀汉关于荆州指导层面的失误
但是自诸葛亮入蜀,刘备占有益州之后,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经营西蜀和汉中前线的防御上,无暇顾及荆州,而将荆州放手让关羽去镇守,加上益州与荆州之间由于地理阻隔的原因,无形之中刘备将关羽与荆州孤悬于益州之外。在荆州丢失的最后几年中,作为最高统治者刘备没有对荆州防守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更没有和孙权那样始终如一地在谋划夺取荆州。这是刘备在荆州问题上所犯的战略性错误。
关羽指挥下的荆州军团主要人员也没有进行充实。关羽统领下的荆州军团指挥人员的构成:武将方面,有关平、廖化、刘封、糜芳、傅士仁、赵累等;谋士方面,有马良、糜竺、潘睿、伊籍等。无论是武将,还是谋士都是跟随刘备多年,出生入死,转战南北的忠勇之士;但在政治观察力和处理错综复杂多边关系的能力上普遍较差,尤其是缺乏一位有战略眼光并能制约和协助关羽的谋士。如果说,刘备和诸葛亮先后率部入蜀是因形势紧迫,来不及考虑荆州军团指挥人员的人事安排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刘备夺得汉中并称汉中王后,尤其是获悉孙权集团中识大局的联刘派将领鲁肃去世,其职务由攻刘派将领吕蒙替代后,仍未对荆州军团指挥人员的配备进行适当调整,则不能不说是刘备的一个重大错误。
刘备据有汉中以后,势力如日中天。他认为形势对他有利,于是命令常年驻扎于荆州的关羽向曹操的荆襄军队发起进攻,以形成两路夹击中原之势,一鼓足气打败曹操,以实现《隆中对》全据“刘表荆州”的战略目标。此种构想过于理想化,他们没有意识到客观形势的变化,最后,关羽不仅没有占领整个荆州,反而身首异处,丢失原有的荆州。

3.关羽真的是大意吗?还是一错再错,错了又错?
错误一,关羽擅自发动攻樊之战打破了三方在荆州的均势,引起了孙吴及曹操的恐慌。
据《三国志·关羽传》称:“(建安)二十四年,……羽率众攻曹仁于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汉水泛溢,禁所督七军皆没。禁降羽,羽又斩将军庞德。……羽威震华夏,曹公议徙许都以避其锐。司马宣王、蒋济以为关羽得志,孙权必不愿也,可遣人劝权蹑其后,许割江南以封权,则樊围自解。曹公从之。”
由于关羽打破了三方在荆州的均势,打痛了曹操,才迫使曹操主动向孙权求援,从而使孙权在三方中处于最为有利的地位。因为这样一来被夹击的正好是关羽,而曹操则唯恐孙权不能成功,故孙权不仅可以放心大胆地干,而且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效。

错误二,后方空虚,给敌以可乘之机。
关羽在发兵樊城之战前,是做有认真准备的,“多留备兵”于公安、南郡,防备吕蒙袭击其后方,从这一点来看,他对孙吴可能袭其后方还是有所警惕的。一举攻下樊城,哪知关羽很快被胜利冲昏头脑,水淹曹操于禁七军之后并不主动撤军,而是得寸进尺,分兵攻襄阳,企图一举占领襄阳,结果久攻不下,被迫将防吴备兵全部调至前线,从而造成后方空虚。更严重的是他在得知孙权即将进攻公安、江陵的确切消息后,还“自恃二城守固”,仍不退保后方,终于失去了自救的最后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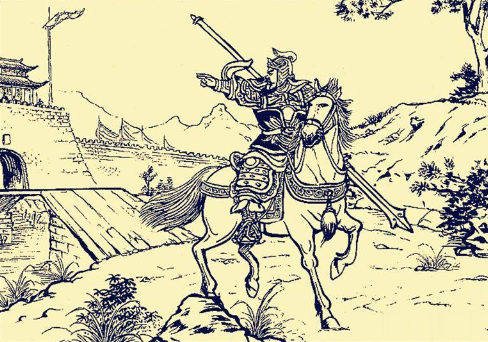
错误三,与盟友关系急剧恶化。
关羽个性有一重大弱点,即“刚而自矜”。
关羽这种个性在与孙吴打交的过程中,对联吴的策略毫无认识,以致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如孙权遣使为子求其女时,关羽不仅不同意,而且大骂其使者,引孙权震怒。关羽围樊城,擒曹操的于禁所部三万余人后粮草不济,擅自打开孙权设在湘关的米仓取粮,从而进一步激怒了孙权,使孙权终下决心与关羽开战。而在北攻襄樊之后,关羽曾一度向孙权求援。因吴兵“淹迟”不进,关羽乃骂曰:“貉子敢尔!如使樊城拔,吾不能灭汝耶!”孙权闻讯,“知其轻己,伪手书以谢羽,许以自往”。关羽这种自大狂的心态,其实又是最容易被利用的,丧失了对东吴的起码警惕,终被孙权以武力给灭杀。

错误四,内部不稳。
关羽这种性格上的缺陷,在处理内部关系时,则表现为对同僚和下级的简单粗暴。
《三国志·关羽传》称:“又南郡太守縻芳在江陵,将军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轻己。〔自〕羽出军,芳,仁供给军资,不悉相救(按《通鉴》作“相及”),羽言‘还,当治之。’芳、仁咸怀惧不安。于是权阴诱芳、仁,芳、仁使人迎权”。
粗暴凌下早已引起芳、仁的不满而不自和,反而委以镇守后方(亦即防吴前线)的重任。既委以重任,又不仅未能安抚其心,反而威胁要严惩其人,这不是自断后路吗?这样,孙权不费吹灰之力就夺取了荆州。
驻扎在上庸的刘封、孟达也因与关羽有宿怨,当关羽进攻樊城遇到困难向其求救时,刘封、孟达“辞以山郡初附,未可动摇,不承羽命。”以致关羽兵败麦城,被孙权的部将所杀。可见,内部离心,同僚的不和为孙吴几乎兵不血刃大获全胜提供了极佳的契机。从以上四错可以看出,刘备荆州的丢失,固然是孙曹夹击的结果;但孙曹夹击的形势,则完全由关羽攻樊所促成。再加上关羽的一错再错,屡次失去挽救危运的时机,才造成荆州丢失的。

荆州丢失,对蜀汉是一关键转折,从此,横跨荆益,分兵北上的战略宏图化为泡影此后,刘氏政权只能偏居一隅,苟延自保,再难与曹氏争夺天下,复兴汉室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