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他在中南海睡觉,周恩来来了,没叫他,走了,他醒来发火,把随行吓得不敢吭声。
“我许世友的觉有那么值钱?”他怒吼。
这不是矫情,这是真事,1967年,中南海,一次午睡,一场误会,一段情谊的真实暴露。
 不是所有人,能进中南海
不是所有人,能进中南海许世友是被接进去的,不是请进去的。
那年他状态不好,整个人都“走形”了,长期失眠,心悸、暴躁,酒喝得多,血压高,他扛得住枪林弹雨,却扛不住当时的政治风向。
他先是在大别山静养,消息一出来,不少人以为他是“靠边站”,其实不是。

是毛泽东要他进北京,是周恩来亲自安排落点。
不是医院,是中南海。
当时正值“文革”爆发初期,军队高层人人自危,中央决定将许世友“调”进中南海,原因有两个:
一是养病;二是保护。
谁的决定?毛泽东点的头,周恩来拍的板,许世友被安排在陈毅原来的办公室住,离毛泽东“游泳池”住处几分钟脚程。
这里不是招待所,是权力中枢,谁能住进来,意义不用多说。

他不是一个人来的,他带了警卫、医务人员,还有他最亲近的秘书,这些人破例能在中南海自由走动,还能和李先念、周恩来“串门”。
这种待遇,放眼全国,没人敢多嘴,许世友也不是没有感觉,他一进来就看懂了。
中南海,不是来休息的地方,这是信任,是掩护,是信号。
许世友的第一反应,不是安心,而是紧张,他开始“自查”,不是为了别人,是怕自己哪天也突然失踪。
但周恩来不这样看。
他几次过来看他,不说大道理,不谈时局,拿着养生汤、药方、饭盒,说是“夫人亲手做的”。
许世友不信,说:“总理没这闲心。”
周恩来笑:“你就当她是护士,给你送饭。”
 周恩来走了,许世友火了
周恩来走了,许世友火了矛盾出在第三次探望。
前两次,周恩来都进来了,第三次,带着邓颖超一起,他到门口,秘书说:许司令午睡了。
工作人员要进去叫,周恩来伸手拦住,说了七个字:“我们是邻居,改天再来。”
没叫醒,走了。
谁也没当回事,直到一个小时后,许世友醒来。

他起床第一件事,不是洗漱,是找人,问:“今天有没有人来?”
秘书犹豫了一下,说:“总理来过,您在睡觉,他说不要打扰……”
下一秒,屋里炸了。
“你们脑子进水了是不是?”他吼,“我许世友的觉就那么重要?周总理来了你们都敢不叫醒我?”
屋子安静,没人敢出声,他指着门:“出去,全出去!”
没人动,秘书硬着头皮说:“是总理不让叫的,他说不打扰您……”
“他是总理,你们是干什么吃的?”
“叫我!”他声音抖着,“就是睡死了,也得叫我!”

外人可能不理解,为什么他反应那么大。
不是装,不是气头上说的,他是真的在乎,他认为自己被“剥夺”了一次重要会面,不是政治,是情分。
“我许世友这一辈子,欠总理一条命。”他说,“来了我都没见着,我还活着干什么?”
这不是夸张,他是真的受过周恩来的救。
 铁汉的软肋,不是伤,是情
铁汉的软肋,不是伤,是情外界都以为许世友刚硬,没人敢惹,他当面骂干部、军委、连毛泽东也顶过嘴。
但他一提起周恩来,整个人就变了。
他说:“总理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我是铁头,这辈子服的就他。”

这不是客套。
早在50年代,许世友曾因喝酒闹事,被人“收集材料”,准备处理。
那次,周恩来挡在前面,亲自跟中央军委说:“许世友酒是喝多了,但他脑子清楚,不该上纲上线。”
后来文革初起,南京军区局势极其复杂,许世友被中央隔离审查的传言一度泛滥,是周恩来一句话:“你们敢动许司令,就是跟我作对。”
这些话没公开过,但许世友知道,他知道自己能从“风口”下来,不是因为多清白,而是因为周恩来亲自站过队。
 不喝了,是赌输了
不喝了,是赌输了1970年那次“酒局”,成了转折点。
许世友是出了名的酒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喝完三斤茅台再骂人,他有句口头禅:“酒是烈的,人才是真。”
周恩来说:“你这样会喝出命来。”
许世友说:“我喝得明白。”

说完他又笑:“总理您也别劝了,我这酒啊,戒不掉。”
周恩来点了点头,没说话,第二天,带了两瓶酒,说:“咱们打个赌。”
许世友说:“怎么赌?”
“今天喝,你赢了,我不劝了,你输了,以后你每天不超过六杯。”
许世友点头:“来。”
整整三个小时,两人你一杯我一杯,谁也不认输,桌子上摆着一排空瓶。

最后是许世友先倒下。
不是醉,是站不起来了,他说:“我认栽。”
从那天开始,他真没多喝过一杯。
 最隐秘的改造,是卫生间
最隐秘的改造,是卫生间许世友住进中南海的第三天,周恩来来看他。
他没说太多话,只在屋里转了一圈,然后停在一处角落。
“这屋里没卫生间。”

许世友说:“没事,我下楼去。”周恩来没接话,只转头看了秘书一眼,说:“改。”
第四天开始装修,第五天完工。
中南海的老楼,不是谁说改就能改的,卫生间牵涉管线、水压、安全。
但没人问原因,也没人敢拖时间。
许世友开始不理解,觉得自己没那么金贵。
但事情接着发生了第二件,饮食被换了。
他平时吃辣,喝酒,不忌口,可搬进来后,菜单变了。
“你不能吃辣,血压高;米饭少点,晚上粥换汤。”
是谁安排的?不是医生,是邓颖超。
她亲自去厨房下的单子,还专门配了护士。
许世友嘴上不说,心里明白,他告诉贴身秘书:“你记着,不是怕我出事,是他们怕我不好。”
“我一出事,周总理都不好交代。”
 周恩来最后一次躺下,许世友跪了
周恩来最后一次躺下,许世友跪了1975年,许世友最后一次见周恩来。
不是在中南海,是在医院。
那个时候,周恩来已经进医院半年,体重从60多公斤掉到40出头,讲话都靠纸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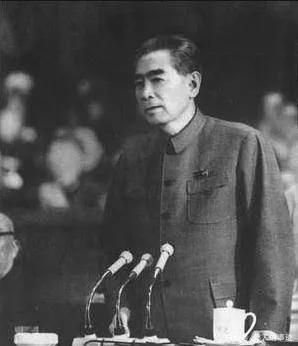
许世友去了,不是通知,是他自己要求的,他一进病房,门一关,五分钟没人能进。
外头的工作人员只听见一声低吼:“总理!”
然后是沉默。
后来护士进去的时候,发现许世友跪着,没人喊他跪,他也没做戏,是他自己跪下的。
“总理,我来了。”他说。
他一边跪,一边用毛巾给周恩来擦汗。擦一次,换一次。
他手在抖,不是害怕,是撑不住。
他从没见过周恩来这个样子,这个当年能连续通宵处理文件、能从容面对红卫兵围堵的男人,现在躺在那里,嘴唇泛白,说不出话。

周恩来看着他,点了点头,眼角湿了。
许世友走之前,握着他的手,说:“你是我见过最讲义气的。”
第二天,他没再来。
他不敢来。
他说:“我再见一眼,我怕受不了。”
 许世友哭了,但只为一个人
许世友哭了,但只为一个人1976年1月8日,消息传来。周恩来逝世。
中南海的气压陡降,没人说话,走廊里都是沉默的脚步声。
许世友听完后,关门,关窗,一个人坐在屋里不动。

没人敢敲门,过了两个小时,门开了,他出来,衣服没换,眼圈是红的。
秘书说他第一次看到许司令哭。
“他不是哭,是在低声呜咽,像压着火一样。”
他没参加追悼会,不是不想去,是怕控制不住。
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走了,没人管我了。”不是矫情,是实话。
从那天起,许世友变了,他开始沉默,喝酒少了,不再对人吼,他常坐在中南海的楼台上看天,一坐就是半天。
“总理不在了。”他说,“没人劝我了。”
 不是每段情谊,都写在简历上
不是每段情谊,都写在简历上很多年后,有人写回忆录,提到许世友在“文革”时受重用,调入中央,有中南海特别待遇。
但没人知道,他住的那间屋子,是陈毅的旧办公室;他吃的那顿饭,是邓颖超换的单子;他喝的那碗药,是周恩来让人送的。
没人知道,他在一次午睡里错过的见面,是他最后悔的事。
他宁愿醒着面对责骂,也不愿沉睡错过那句“你好”。

也没人写,他在周恩来病重的病房跪了整整五分钟,这不是史料,这是人。
历史不会写这种事,因为它太小,太私人,太“不重要”。
但许世友自己说得明白:
“不是他护我,我今天还在不在都两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