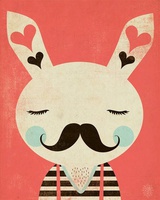《周礼·秋官·朝士》记载:“左嘉石,平罢民焉;右肺石,达穷民焉。”说的是嘉石和肺石的作用,似乎有着民本主义思想。只是后代并没有延续下去,而是剔除了民本主义思想。只是用建筑来凸显皇权的威严,凸显礼教文化,也就等而下之了。

立嘉石的目的是教育惩罚那些邪恶的人、触犯刑罚而罪不当诛的人,还有乡里为非作歹的人,根据犯罪情节的轻重规定了不同的惩罚办法。如情节严重者,戴上手铐脚镣,罚跪嘉石十三天示众,并要服劳役一年,期满后,还需地方长官作担保人,才能放回原籍。立肺石的目的是为那些孤苦无告者提供一个诉冤的地方,有冤屈而地方长官不予转达,只要站在肺石上三天,朝士就会受理他们的告词,向六卿汇报,并处罚那些不肯转达的地方官。到了西晋,建立了直诉制度,在朝堂外悬设登闻鼓,允许有重大枉屈者击鼓鸣冤,直诉中央甚至皇帝。唐宫城承天门朝堂外东置肺石,西设登闻鼓,就是这一制度的反映。到了宋代,就演变成钟楼和鼓楼了,而嘉石和肺石却不会提起。本来嘉石是为了惩戒作奸犯科者,肺石是为了让那些孤苦无告者直接“动达天听”,要把冤屈直接申诉给皇帝,可以越过很多官员的阻挠。本来制度设计是好的,但并不是所有作奸犯科者都能到嘉石那里去罚跪,也不是所有受冤屈的人都能到肺石那里去站立,直接把冤屈申诉给皇帝。权力系统并非不知道这样的事实,而只是设立嘉石和肺石,以儆效尤,同时摆出了亲民的姿态,似乎可以把人间的冤屈全都处理清楚。
唐朝的肺石仍然有着伸冤的功能,登闻鼓有着击鼓“动达天听”的意思。只不过很多民间的作奸犯科者并不能被惩戒,而是占尽了便宜。一些贪官污吏可以层层加税,甚至为了收税,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却不会到嘉石跟前罚跪。民间的偷盗者总是占了便宜,被逮住的在家族内部处理或者官员处理,而不会放到京城的嘉石旁边罚跪,不然就会暴露了地方官员的问题,起码说明地方官员治理不佳,导致小偷产生。民间真正有冤屈者只能自己忍耐,却不能到京城的肺石那里去站立,不能直接告诉皇帝。如果谁想要去伸冤,就会被地方官员提前知道,被人看管,不能顺利到达京城,以免暴露地方治理的问题。地方官员宁可看管这些去伸冤的人,不让他们告状,也不会帮助他们处理问题,并不会替他们伸冤。问题没有解决,要解决提出问题的人,最终让那些伸冤者只能在一定的范围内活动,却不能到京城的肺石那里去站立。地方官员有自己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套路,也有上级替自己“捂盖子”,当然可以控制一些伸冤的人。也就是说,嘉石和肺石设立的象征意义永远大于实际意义,只是起一个象征作用,让老百姓理解怎么回事就可以了,而实际操作起来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作奸犯科者占尽了便宜,有贪官污吏做榜样。民间会有很多地痞无赖,攒钱做衙门里的临时工,专门购买收税官的职务,替官员收税,最终逼得老百姓家破人亡,而他们却可以肆意加税,自己赚得盆满钵满。这些作奸犯科者并不会被皇帝发现,也不会到嘉石那里去罚跪,当然就可以混得风生水起了。而那些被逼得家破人亡的老百姓大多不读书,不识字,世世代代做农民,忍受别人的欺负,只能忍耐,不能反抗。越是这样,他们就越是没有出头之日,除非生存遇到危机,吃不上喝不上了,才会跑到外地逃荒要饭。倘若有人组织他们造反,他们会义无反顾地去造反,因为造反还有可能活下去,不造反就很可能饿死。皇帝不知道民间具体情况,只是设立嘉石和肺石,要人们引以为戒,同时给底层老百姓伸冤的机会,却往往没有那么理想。
宋代设立了钟楼和鼓楼,老百姓可以敲钟击鼓,直接伸冤,但钟楼和鼓楼的意义并非如此,只是一个皇家建筑的意义,有了礼教方面的说法,却并没有惩罚作奸犯科者,也没有让有冤屈的老百姓敲钟击鼓。京城不是什么人都能去的,而钟楼和鼓楼也不是什么人都能上去的。倘若真的为老百姓做事,就应该把钟楼和鼓楼的钟鼓放到地面上,让老百姓伸手就能触摸到,而且人人可以去,派官兵看管,防止有人破坏。但事实上却并非如此,钟楼和鼓楼建得高高的,钟和鼓放在楼里面,人们要拾级而上才能进去,甚至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去。即便钟楼和鼓楼前有嘉石和肺石,也只是作为象征意义的东西存在,却并没有起到原初的作用。本来朝廷设置嘉石和肺石的出发点是好的,目的也是好的,但实行看来之后,嘉石和肺石就成了一种象征意义的存在,而没有实际的意义。以至于后代把嘉石和沸石的象征意义延伸了,改变了嘉石和肺石的形态,也改变了其象征意义,最终成为礼教文化的一部分。就好像社会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被有些人修正了,变成了修正的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但走这样道路的统治阶级并不承认,人们就还是认为走了社会主义道路。

嘉石和肺石的象征意义是美好的,但现实却很残酷,并没有实现这样的意义,只不过用来愚弄老百姓罢了。后代朝廷弄的很多亲民的建筑也都有这样的意义,但最终符合了礼教文化,却不贴地气,距离老百姓太遥远,当然也就失去了实际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