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64年七月,在南明皇帝朱由榔被杀两年之后,仍旧在浙江舟山群岛抗清的张煌言被叛徒出卖,惨遭清军抓获。
消息传到北京,51岁的孝庄太后对10岁的康熙皇帝说道:“立刻下令将此人就地正法!”
张煌言与孝庄太后,二人虽然同处一个时代,但是在地理上却一南一北,素不相识,为何孝庄太后获知张煌言被抓后这么大反应,并要求立刻处死张煌言呢?
 孝庄和多尔衮的绯闻
孝庄和多尔衮的绯闻这一切都源于张煌言多年来写下的十首绯闻诗——《建夷宫词》,让整个满清皇室连头都抬不起来。
其中直接和孝庄太后有关的便是下面这首:
“上寿觞为合卺尊,慈宁宫里烂盈门。春宫昨进新仪注,大礼恭逢太后婚。”——张煌言《建夷宫词》
这首诗的白话意思,本来为太后过寿准备的酒,突然间变成了太后和摄政王所喝的交杯酒。而慈宁宫张灯结彩本来是为了给太后庆祝寿宴,最后却因太后的下嫁变得稀烂。听说满清的礼部尚书一直在研究礼仪,照说华夏五千年来什么礼仪没有呢,直接拿来用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好研究的呢。没想到,这满清的礼部尚书研究的是太后下嫁摄政王的礼仪,而这“弟娶寡嫂”的皇家礼仪,在华夏五千里的历史典籍中,的确是找不着,这可是得好好研究一下。
此诗一出,立马在江南各地的反清势力中传播,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通过张煌言的诗作引子,民间把满清顺治皇帝的老妈孝庄太后下嫁摄政王多尔衮一事传的有鼻子有眼。此诗不仅在当时给满清顺治皇帝,孝庄太后,和摄政王多尔衮造成了很大的心理负担,更为后人编排孝庄太后和多尔衮提供了谈资。

直到今天,世人还在为孝庄太后有没有下嫁多尔衮争论不休。
然而,孝庄太后到底有没有下嫁多尔衮呢。这个事情,在史书里没有记载。
更有人说,多尔衮为了心心念念的孝庄太后,竟然放弃了唾手可得的皇位。
但是深谙历史的人都知道,一个人能不能当皇帝,不是他个人说了算的,而是他背后的利益集团以及各方势力博弈的结果。
即便多尔衮想为了孝庄太后放弃皇位,将皇帝之位拱手让于孝庄太后的儿子福临,多尔衮背后的利益集团也不会答应。
在皇太极死后,多尔衮登上皇位的最大竞争对手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多尔衮当时掌控的军队,也不过是满清八旗中的正白旗,镶白旗,以及他亲弟弟多铎正蓝旗。而清太宗皇太极的长子豪格,则是继承了皇太极的正黄旗和镶黄旗,实力也不输多尔衮。并且其他三位旗主,虽然不站队多尔衮和豪格,但是他们一致要求立皇太极的后代为帝。
最后多尔衮和豪格相继妥协,让孝庄太后六岁的儿子福临捡了便宜,当上皇帝。作为妥协条件,多尔衮当上了摄政王。而豪格则属于权力争夺的失败者,最后被多尔衮罗织罪名杀死。
在张煌言写这首讽刺孝庄太后和多尔衮的这首诗之前,恰逢多尔衮杀死了自己的政治对手豪格,并且强娶了豪格的妻子。从伦理上说,多尔衮这属于强娶了自己的侄媳,这个在史书上是有记载的。

后来,这件事传到了在江南抗清的张煌言耳中,张煌言便将事情张冠李戴到孝庄太后身上。
从华夏儒家礼仪上来讲,多尔衮强娶自己侄媳这件事,要比多尔衮娶自己寡嫂孝庄太后这件事更荒唐。但是由于豪格妻子的身份并不足够引人重视,爆出来的影响力不会很大。而孝庄太后的身份不一样,他是满清当朝皇帝的母亲。把这件事安排在孝庄太后的头上,则能从伦理和道德方面,对满清的统治产生巨大打击,以达到反清复明的目的。
顺治和董鄂妃的绯闻编排完孝庄太后还不算,张煌言在不久之后,又把目标锁定在长大后的顺治皇帝身上。
其中,和顺治皇帝有关的一首诗是:“掖庭又说册阏氏,妙选孀闺足母仪。椒寝梦回云雨散,错将虾子作龙儿。”——张煌言《建夷宫词》
在这首诗中,张煌言把顺治皇帝册封皇后比作匈奴单于册封阏氏,结果呢,顺治千挑万选,选了一个别人的遗孀当老婆。如果这样也就算了,当时这个女人的肚子里还怀着过世丈夫的孩子。就这样,顺治皇帝也认。在和这个女人在居住的宫殿一番巫山云雨之后,明知女人肚子里怀的是别人的孩子,顺治却也心甘情愿的把他当成自己的。
与上一次编排孝庄太后的绯闻相比,张煌言这次编排顺治帝并非空穴来风。
顺治皇帝有一个妃子叫董鄂妃,董鄂妃在嫁给顺治皇帝之前是有丈夫的。她的丈夫是顺治帝的弟弟博果尔。在没嫁给顺治之前,两人婚姻甜蜜。然而,就因为董鄂氏在又一次进宫给孝庄太后请安之时,被顺治皇帝看见,顺治皇帝从此就对董鄂氏念念不忘。

不久之后,15岁的博果尔因病去世。而顺治在博果尔死了二十七天之后,便急不可耐的将董鄂氏召进宫中。仅仅一个月后,顺治便昭告天下,封董鄂氏为皇贵妃。次年,董鄂妃就生下了一个儿子。
当这件事被张煌言听说之后,一心寻找满清污点的他当即挥毫泼墨,写下了上面这首讽刺顺治皇帝的诗。而和张煌言一样,孝庄太后对儿子顺治皇帝和董鄂妃的感情也持否定态度,一度达到母子决裂的地步,顺治皇帝更是以出家为威胁,逼迫孝庄太后同意他和董鄂妃的事情。但董鄂妃最后在嫁给顺治皇帝五年之后,便因病去世,年仅22岁。而顺治皇帝也在董鄂妃去世的当年,不幸感染天花驾崩,年仅24岁。
顺治皇帝去世之后,他年仅8岁的儿子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而张煌言的讽刺之作很快也接踵而来。
由于顺治去世时只有24岁,刚刚继位的皇帝玄烨只有8岁。故而顺治在去世之前,留下四大顾命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共同辅政。
于是,张煌言作诗一首:“玉几凭来顾命新,负扆闻道有家臣。从今赌却钻刀咒,不信华人信满人。”——张煌言《建夷宫词》
这首诗的意思是康熙刚登基时,辅佐他治理国家的都是爱新觉罗家的家奴,是一群没有经过科举选拔的文盲,这样一群人能治理什么国家。以此暗讽满清政权只是一帮会打仗的粗人在管理,他们是文化上的侏儒。
全面讽刺除了从伦理和文化方面编排满清之外,张煌言更是从服饰,饮食,信仰,文字和生活习性的方方面面来讽刺满清。
“盘龙小袖称身裁,马上雕弓抱月开。太液池边金弹落,疑从紫塞射雕来。”——张煌言《建夷宫词》
这首诗的白话意思是满清的服装是胡服,和华夏衣冠相比根本上不了台面。诗中的太液池指的是皇家园林里面的湖泊,而能在皇家园林里游玩的都是身穿宽衣长袍之人,哪像满清的权贵一样穿的不伦不类。在张煌言看来,穿着满清的服饰在皇家园林游玩,就好比身上挂着雕弓在大雅之堂发射金弹,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刚从承德的射猎围场射雕回来。
张煌言此诗,意在从服饰上打击满清。

紧接着,张煌言的下一首词,又从饮食上,将满清损的体无完肤。
“毳殿春寒乳酪香,近臣偏得赐新尝。老珰不解驼酥味,犹道天厨旧蔗浆。”——张煌言《建夷宫词》
这首诗的意思是,紫禁城里到处都飘着乳酪的香味,原来是满清的皇帝正在将自以为美味的乳酪一一赐给乾清宫的近臣们吃。但是从明朝遗留下来的老太监们,从来都没有吃过奶酪,竟然还以为是甘蔗汁放久发馊了。张煌言以此暗讽满清当政者没见过华夏的美味佳肴,竟然把乳酪当做好东西,真是没吃过猪肉,也没见过猪跑。
喷完了饮食,张煌言开始从信仰上喷满清。
“朝罢瞿昙次第迎,内庭深处说无生。不知鹦鹉能胡语,偷向金龙诵佛名。”——张煌言《建夷宫词》
“瞿昙”是和尚的意思。
上面已经说过,顺治皇帝为了娶董鄂妃,竟然不惜以出家当和尚来威胁孝庄太后。
因为受顺治皇帝的主观意识影响,所以终顺治一朝,满清在政治方面一向崇尚礼佛。而顺治皇帝每次上完早朝之后,前来迎接他的却是一帮和尚,而后和尚们便拉着顺治皇帝诵经礼佛。但此时距离满清入关不到十年,女真人刚从茹毛饮血的时代过渡到封建时代,他们哪里知道什么是佛。在张煌言眼里,顺治皇帝的礼佛之举不过是鹦鹉学舌,不知所云。
在吐槽完满清的信仰之后,张煌言继而又从文字上打击满清。
“六曹章奏委如云,持敕新书翻译闻。笑杀钟王空妙笔,而今鸟迹是同文。”——张煌言《建夷宫词》
“六曹”指的是吏部、户部、礼部、工部、兵部、刑部等维持封建王朝运转的政府职能部门。满清入主中原后,他们要治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国家,六部官员是必不可少的。但随之而来的是,六部的奏折也如雪片般飞往皇宫。但是在这时,就会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满人皇帝看不懂汉文,每一道奏折都必须将汉文翻译成满文才能让皇帝看懂。
而满文用笔书写出来,和鸟爬出来的没什么去区别。这样的字被称为文字,简直是对文字最大的侮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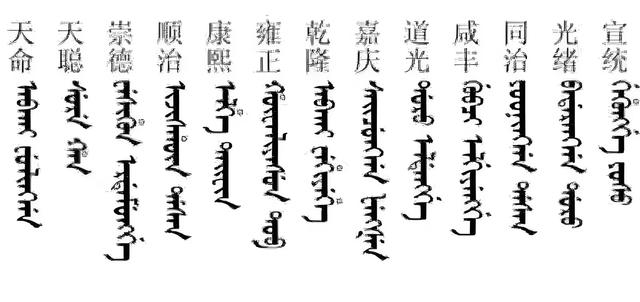
最后,张煌言从生活习性上,再一次打压满清。
“平明供奉入彤闱,亦舞霓裳唱羽衣。千骑骖驔知侍猎,挥鞭驰道拥明妃。”——张煌言《建夷宫词》
意思是满清皇帝凌晨起床时,也让宫女们像汉人王朝一样载歌载舞,但是满清皇帝虽然入主中原,却一点皇帝的生活习性没学到。在看完歌舞之后,就带着女人骑马打猎去了,真的是暴殄天物。
张煌言只活了45岁,但是却在明朝灭亡后,在浙江沿海坚持抗清20年。在这20年期间,虽说屡战屡败,但是却一直利用文学创作,从精神上摧残满清统治者。
而《建夷宫词》中的“建夷”二字,则是张煌言作为一个文化人,对“建奴”二字的文明用语。“建奴”二字,是粗人对建州女真的蔑称,而建州女真就是满清的前身。
在张煌言被满清抓住时,南明永历皇帝朱由榔已经被吴三桂杀死,西南的李定国和台湾的郑成功也病死了,就连张煌言拥立的鲁王朱以海也在福建金门岛病死。但是,张煌言却坚持到了最后。
由于张煌言在近二十年的反清斗争中,不仅编排了孝庄太后和多尔衮的绯闻,更肆无忌惮的讽刺孝庄之子顺治的污点,更是一直在吐槽满清王朝的落后。故而,当孝庄太后获知张煌言被抓获时,一向温文尔雅的孝庄太后火冒三丈,当即从后宫出来,要求立刻将张煌言在杭州斩首。
在孝庄太后的强烈要求下,张煌言和其儿子最终在杭州被斩。临死之前,张煌言抬头仰望吴山,而后叹息道:“大好河山,可惜沦为腥膻。”

“腥膻”一词,意思为身上带有牛羊腥膻味的人,喻指满清。而这,也算是张煌言对满清最后的讽刺。
在被斩首的那一刻,张煌言坚持不跪满清,最后坐而受刑。这是张煌言作为一个文人最后的倔强。
张煌言被斩之后,其头颅被外甥朱湘玉赎回,葬于杭州西湖边的南屏山荔枝峰下。而在张煌言之前,西湖边已经长眠着另外两个忠义之士,一个叫岳飞,一个叫于谦。张煌言则是有幸和岳飞、于谦二人被后世称为西湖三杰。
而孝庄太后虽然下令杀了张煌言,但是由张煌言诗文中传出的有关于他和多尔衮的绯闻,却在历经三百多年后的今天经久不衰,依旧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