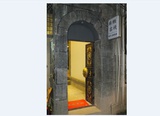当三月把胭脂点在桃枝上,我便知这场花事总要有人成全。你提着满篮烟雨款款而来,说要把春色系在柳梢头,系成解不开的同心结。

我的心跳在惊蛰的雷声里发芽,比燕山新雪消融得更快。你说要带我去看雁字回时的云纹,听二十四桥的箫声,在油菜花海数北斗星子,于碧螺春尖吻落霞余温。

我们踏着青石板数年轮,你突然说疼。原来春寒料峭时,总有人把相思刻得太深。我解开绣着并蒂莲的绢帕,裹住你指尖蜿蜒的掌纹,像裹住前世失落的半阙词。

岸边的芦芽正破译冰封的诺言,你偏要折柳作笔,蘸着涟漪写诗。墨色晕开处,游出两尾红鲤,衔着褪色的桃符。原来有些缘分,早在《诗经》泛黄前就已注定。

你说要借我的眉黛画远山,却把狼毫搁浅在梨涡里。风忽然卷走落英,漫天都是打翻的胭脂盒。我们追着花瓣奔跑,跑过社戏喧嚷的戏台,跑过失而复得的鹊桥,跑成清明上河图里两粒朱砂。

当流萤点亮草叶上的露珠,你对着北斗七星斟酒。我笑这琉璃盏太浅,盛不下整条银河。你却将星子串成璎珞,说要把璀璨别在我的云鬓。醉意朦胧时,听见整个春天在拔节生长。

有人站在二十四番花信外叹息,说绚烂终将零落成泥。我们却在荼蘼架下埋下酒坛,约定来年以落花封泥。你看,连蝴蝶都在碑拓上复活,我们何惧岁月泛黄?

你突然把柳哨吹成凤求凰,惊起满树早莺。我系在你襟口的丁香结,不知何时已抽成缠绕的藤蔓。原来至深的牵绊,从不需要锁链叮当。

暮色漫过石阶时,你问要不要撑伞。我指向天际燃烧的霞光,说我们本就是行走的晴雨。你笑弯的睫毛上,栖息着整个江南的杏花微雨。

当月光把影子绣成连理枝,我们终于读懂春风的隐喻——最炽热的绽放不必追随节气,最绵长的相守无须栓系红绳。你看那并蒂莲立在浊水中,照样开成不染的模样。

此刻柳浪深处传来摇橹声,我们相视而笑。何必追问归舟载得动几多愁,既然选择了共舞,便做彼此不系之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