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个特区:顺天府】
清朝定都北京后,将顺天府划归北直隶管辖,并定其为京师。初始阶段,顺天府仅辖大兴、宛平二县。直至康熙十五年,昌平、良乡等县才改由顺天府统辖。发展至清末,顺天府下辖四厅、五州及十九县。就行政层级中的府级单位而言,顺天府堪称全国规模最大者。
顺天府的定位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从名义层面而言,其隶属于直隶范畴。然而,鉴于顺天府地处京畿这一关键地理位置,致使它处于一种特殊地位。这种特殊性具体呈现于下述多个方面:
与其他府的职官建制相较,顺天府在职官设置方面独具特色,其官员品级亦更为尊崇。顺天府配置府尹一名,官居正三品;另设府丞一名,品秩为正四品。此外,其下属还设有治中、通判、经历、照磨以及司狱等职。
一般而言,府级行政单位的主官为知府,官阶从四品。此外,设有同知(正五品)与通判(正六品)辅助政务,此二职位并无固定员额。其下属官员配置,包含经历、知事、照磨、司狱各一名,分别负责相应具体事务,共同构成府级行政管理体系。
从称谓角度审视,顺天府的最高行政长官并非以“知府”冠名,而是被称作“府尹”,此乃对古代京兆尹称谓传统的沿袭。由于其行政级别相对较高,故而在待遇方面,相较于普通知府更为优厚。在仕途晋升路径上,顺天府府尹通常有望擢升至布政使或巡抚之位。

顺天府,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处于京畿要地,故而肩负着特殊的职责。它所涉事务范畴,绝非局限于一般的地方行政事务,更与朝政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关联。于司法、礼教以及科举等诸多关键领域,顺天府均以京师衙门的角色履行职能。基于此,顺天府尹这一职位,兼具地方官员与京官的双重属性,这种特殊的定位,是由顺天府特殊的职掌所决定的。
【第二个特区:东北】
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将东北地区奉为王朝的肇兴之地,故而实施封禁政策,严禁汉族及其他诸族涉足其间,东北地区由此成为满洲贵族专属的领地。在此区域,清代推行了别具一格的行政管理体制。
东北地区在特定历史时期所施行的官制,呈现为“一府三将军制”的架构。其中,“一府”指的是奉天府,它在东北地区的行政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而“三将军”分别是肩负盛京地区驻防职责的盛京驻防将军、承担吉林区域驻防任务的吉林驻防将军,以及负责黑龙江地域驻防事务的黑龙江驻防将军。此官制架构对东北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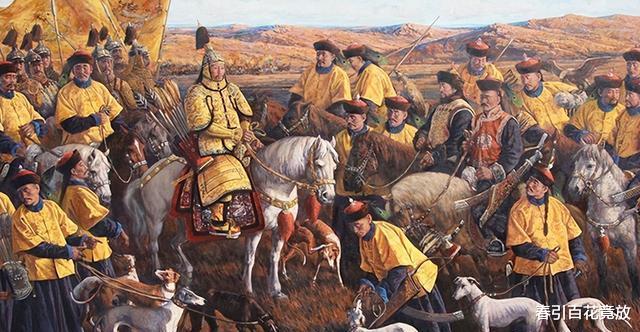
自定都北京后,清廷将盛京确立为留都。于顺治十四年,正式设立奉天府,其行政级别与顺天府等同。奉天府的最高行政长官为府尹。至乾隆三十年,朝廷参照顺天府的建制,在奉天府增设“兼管府事大臣”一职,由盛京五部侍郎兼任。
在东北地区,主要施行的行政管理制度为三将军制。其中,奉天府虽位阶颇高,且设有“管府事大臣”,然而其行政领导关系上,直接隶属于盛京将军。从区域行政管理架构而言,于东北特别行政区这一范畴内,奉天府实则可被视作该特别行政区中的一个具有特殊地位的区域单元。
东北地区在行政管理体制上,与其他各省存在显著差异。于其他省份而言,设有总揽军、民事务的总督与巡抚,在此架构下,军、民政务于督抚之下,分属两个平行的系统运行。
其一为地方行政体系,涵盖司、道、府、州、县等层级。其二是军事体系,由驻防将军、副都统所统领的八旗兵,以及提督、总兵所统帅的绿营兵构成。
在东北地区正式建省之前,施行的是一种集驻防将军、副都统、总管、协领、城守尉、防守尉等职官于一体,融合军事与民政管理的制度体系。具体而言,清代于东北地区的治理模式,本质上可归结为军事管制。

【第三个特区:少数民族地区】
在清代,少数民族聚居区域可划分为五个部分。其一为内蒙古地区,该区域统辖科尔沁等二十四部,共计四十九旗,此外还包括察哈尔游牧八旗、达什达瓦额鲁特一旗以及蒙古土默特二旗。
其二为外蒙古地区,该区域统辖范围涵盖喀尔喀四部计八十三旗,唐努乌梁海部之五旗及三佐领,另有额鲁特二旗、辉特一旗,同时包括扎赉特、杜尔伯特等八部共三十一旗。
其三为新疆地区,清廷在此设置伊犁将军,统辖范围涵盖惠宁、惠远、乌鲁木齐、库尔喀喇乌苏、吐鲁番、巴里坤、古城、哈密、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阗、乌什、库车、喀喇沙尔等诸多城镇。
其四为青海地区,清廷在此设置八旗驻防大臣,负责管辖青海蒙古的诸多旗部,其中涵盖青海蒙古五部共计二十九旗,具体包括青海和硕特部二十一旗、青海淖罗斯部二旗、青海辉特部一旗、青海土尔扈特部四旗以及青海喀尔喀一旗。同时,该地区还设有西宁镇与道,其管辖范围兼及贵德、循化两地。

在清代地方治理体系中,西藏地区别具一格。彼时,以驻藏大臣总领前藏与后藏地区的军政事务。于此同时,达赖喇驻锡拉萨,班禅额尔德尼驻锡日喀则,且设有“边营”以巩固边防。而在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等省份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朝廷采取了不同的治理策略。通过划定府、州、县等行政区划,任用当地土官进行治理,以因俗而治的方式维持地方稳定。
在清代,针对特定地区的行政管理模式独具特色。其并非采用与直省一致的方式,而是基于各民族自身传统治理方法进行因势利导。在区域划分、行政层级设定以及官员配置方面,与直省形成显著差异。然而,这种表象背后,实则反映出彼时国家政权在这些地区的管控力度,相较于汉族聚居区域,存在一定程度的薄弱。
在清代,为实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治理,特设立理藩院这一专门机构。因各少数民族地区情况各异,治理方式亦有所不同。就蒙古地区而言,鉴于其与满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较为紧密的联系,且蒙古人于国家政权架构中占据特殊地位,故而清廷在对蒙古地区的治理上,较多地保留了其原有的治理模式。

在新疆地域,清政府多施行带有军事管制属性的强制性举措。相较之下,对西藏地区的管控力度相对薄弱。至于云南、贵州、广西等区域,雍正时期开展了大规模的 “改土归流” 政策。此后,这些地区与内地一致,推行以省辖府、府辖县的行政管理制度,从而强化了中央对地方的政治掌控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