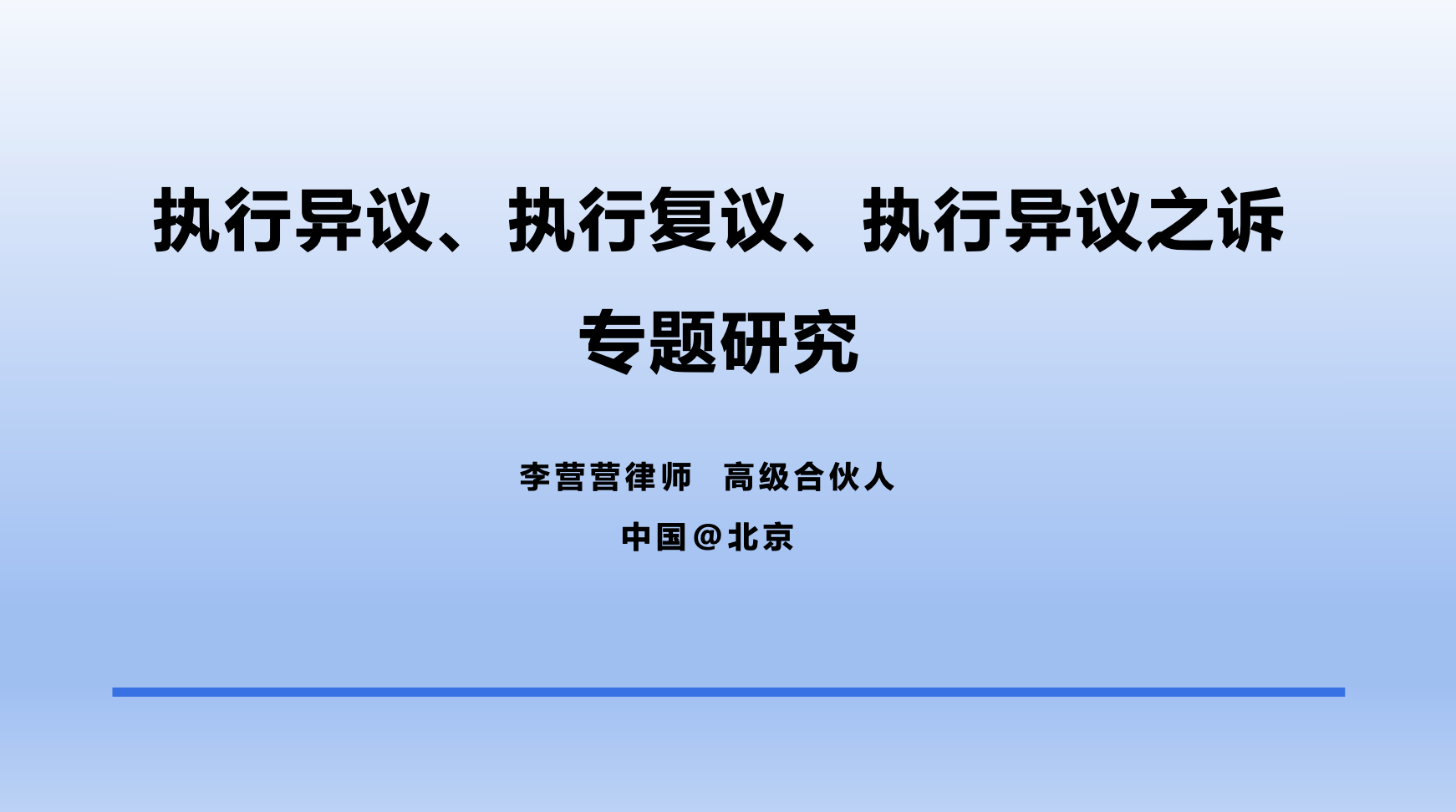
人民法院案例库:借名买房的借名人能否排除强制执行?
借名人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亦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因此借名人不能以债权排除强制执行。
阅读提示:
人民法院案例库是收录经最高人民法院审核认为对类案具有参考示范价值的权威案例,包括指导性案例和参考案例。最高法院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必须检索查阅案例库,参考入库同类案例作出裁判。这对于促进统一裁判规则和尺度,避免“同案不同判”,保障法律正确、统一适用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借名买房,是指实际出资人(借名人)借用他人(出名人)名义购买房屋并登记在出名人名下的行为。但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等采取严格的法定主义,因此在在执行程序中,就会出现出名人的债权人利益与借名人利益的冲突。此时借名人能否排除强制执行?李营营律师团队长期专注研究与执行有关业务的问题,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陆续发布。本期,我们以最高人民法院处理的执行异议之诉案件为例,与各位读者分享法院审理类似案件的思路。
裁判要旨:
被执行人与案外人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只能在二者之间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案外人不能基于代持协议所享有的债权排除强制执行。
案件简介:
1、2011年4月10日,某帝公司、某中汇公司与吴某签订《房产合作购置及代持协议》,约定共同购买深圳某广场办公楼16层整层物业,某帝公司占50%份额,以吴某名义登记。之后,某帝公司向深圳某广告有限公司转账731.058万元,用于支付购房款。
2、2011年7月10日,房产出让方深圳某广告有限公司完成过户登记,案涉房产正式登记至吴某名下。
3、2014年6月30日,吴某与某高速(深圳)能源有限公司签订《抵押合同》,以案涉房产为某满利公司债务提供最高额1亿元的抵押担保。
4、2014年7月8日,吴某为案涉房产办理抵押权登记,抵押权人为某高速(深圳)能源有限公司。之后,某高速(深圳)能源有限公司更名为某省高速公司。
5. 2017年,某省高速公司因某满利公司未履行债务,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6、2018年11月30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民事调解书,确认某省高速公司对案涉房产享有抵押优先受偿权。
7、2019年1月24日,案涉房产被正式查封。
8、2019年10月11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拍卖案涉房产。某帝公司向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主张自己是实际权利人,请求中止执行。
9、2019年12月18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某帝公司异议。某帝公司遂向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
10、2020年9月22日,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决驳回某帝公司的诉讼请求。某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1、2021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争议焦点:
某帝公司就案涉房屋是否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要点:
1、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应履行变更登记程序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规定:“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第十六条规定:“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根据前述法律确立的物权公示基本原则和不动产物权登记生效原则,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不动产物权的变动应履行变更登记程序才能发生相应的法律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所指的“法律另有规定”,指非基于法律行为导致物权变动、法律规定不以登记为生效要件或者登记错误等情形,并不包括当事人故意将不动产登记在他人名下的情形。
2、某帝公司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其基于《房产合作购置及代持协议》所享有的债权,不能对抗某省高速公司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担保物权。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案涉房屋登记在吴某名下,某帝公司与吴某签订的《房产合作购置及代持协议》只能在某帝公司与吴某之间产生债权债务法律关系,也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故某帝公司并非案涉房屋的所有权人。案涉房屋登记的所有权人吴某与某省高速公司签订《抵押合同》,约定以案涉房屋设定抵押并依法办理了抵押登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该抵押权已经设立,某省高速公司对案涉房屋依法享有担保物权。某帝公司基于《房产合作购置及代持协议》所享有的债权,不能对抗某省高速公司对案涉房屋所享有的担保物权。
综上所述,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某帝公司就案涉房屋不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
案例来源:
人民法院案例库:《某帝公司诉某省高速公司、吴某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案号: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终391号],入库编号:2023-07-2-471-007。
实战指南:
1、借名人的债权能否排除强制执行?通过检索最高院审判的案件可以发现,支持排除执行与不支持排除执行的案例都存在。多数裁判观点认为借名人的债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仅在个别案例中最高院支持了借名人的主张。例如在(2020)最高法民申4号案例中,借名人提交了相关银行转账凭证、流水记录及和出名人之间短信记录,能够证明房屋首付款及贷款由借名人支付并每月偿还,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借名人对案涉房屋享有的权益足以排除执行。在(2021)最高法民申354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也支持了借名人的主张。
借名买房形成的法律关系属于合同关系,借名人仅享有要求被借名人协助过户的债权请求权。这种债权与申请执行人的普通债权处于平等地位,不具有优先性,因此原则上不能对抗强制执行程序。不动产物权以登记为生效要件,即使借名人是实际出资人,只要房屋登记在被借名人名下,法律即推定其为权利人。因此出于对外观主义下的交易安全、申请执行人信赖利益的保护,大部分的案例包括本期入库案例,裁判观点是借名人的债权不能排除强制执行。
2、在此,我们建议借名人在借名买房时,应当签订书面协议,明确借名合意及违约责任。同时借名人要保留好购房款支付凭证、水电费缴纳记录、居住证明等证据,以增强举证能力。在符合过户条件时,借名人应当及时要求被借名人配合过户或提起诉讼。借名人要了解借名买房的风险,如果借名协议因规避政策或违背公序良俗的,后续在诉讼中借名人将无法主张权利。即使合同有效,借名人仍需承担出名人负债导致房屋被执行的风险。
法律规定:
1、《民法典》第二百零九条:“不动产物权的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依法属于国家所有的自然资源,所有权可以不登记。”(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九条)
2、《民法典》第二百一十六条:“不动产登记簿是物权归属和内容的根据。不动产登记簿由登记机构管理。”(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十六条)
3、《民法典》第四百零二条:“以本法第三百九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财产或者第五项规定的正在建造的建筑物抵押的,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本案适用的是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
延伸阅读:
在检索大量类案的基础上,北京李营营律师团队总结相关裁判规则如下,供读者参考:
1、借名人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
案例一:《辽宁中集哈深冷气体液化设备有限公司与徐沛欣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再328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徐沛欣借名买房目的在于规避国务院和北京市的限购政策,通过投机性购房获取额外不当利益。司法对于此种行为如不加限制而任其泛滥,则无异于纵容不合理住房需求和投机性购房快速增长,鼓励不诚信的当事人通过规避国家政策红线获取不当利益,不但与司法维护社会诚信和公平正义的职责不符,而且势必导致国家房地产宏观调控政策落空,阻碍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落实,影响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故徐沛欣与曾塞外为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签订的《房产代持协议》因违背公序良俗而应认定无效,徐沛欣依据规避国家限购政策的借名买房合同关系,不能排除对案涉房屋的执行。
2、申请执行人的信赖利益应受到优先保护,借名人不能根据借名买房的事实排除强制执行。
案例二:《崔某珠、王某军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最高人民法院(2024)最高法民申5649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之间即便存在借名买房法律关系,也系订立该法律关系的双方之间的内部关系,借名人所享有的债权请求权也仅在其与被借名人之间产生效力,既不能直接导致物权变动,也并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法律效果。而且,借名人亦应对其借名买房行为导致名义买房人与实际买房人不一致时可能带来的权利风险有一定的认知并应自行承担相应后果。此外,申请执行人申请启动强制执行程序付出了时间、机会等成本,存在程序法上的信赖利益。比较而言,申请执行人的信赖利益应受到优先保护。故即使借名买房的事实成立,也不能据此排除强制执行。
3、借名买房行为不存在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国家、地方政府限购政策,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等情形的,可以排除强制执行。
案例三:《陈武平、罗士奇再审审查与审判监督案》[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民申3543号]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不动产物权登记产生的公示公信效力,亦仅是一种推定效力,登记行为本身不产生物权,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为真正权利人时可以推翻不动产登记的推定,维护事实上的真实。具体到本案,罗某与陶慧君之间存在借名购房关系,罗某也提供证据证明其系案涉房屋实际出资人及占有人,案涉房屋因尚未还清银行贷款未及时变更产权登记。且罗某通过借名买房,将真实物权登记于陶某君名下,并非为了规避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国家、地方政府限购政策,亦不违背公序良俗,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二条之规定,当物权登记与实际权利状况不符时,以实际权利状况为依据认定事实的情形。故二审判决据此认定罗某为案涉房屋实际权利人,享有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民事权益,适用法律并无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