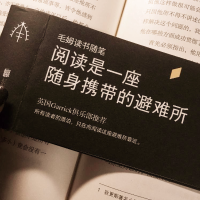武则天为了上位,干了不少伤天害理的事儿。
比如大肆残杀李氏宗族,唐氏族谱五家被灭门,其中四位是唐太宗的兄弟:韩王李元嘉、霍王李元轨、舒王李元名、徐王李元礼,越王李贞是太宗之子。
还有一些极少数存活的李唐儿孙,也被流放到亚热带,充为奴隶,下场十分凄惨。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她也做过一些有意义的事,比如将《氏族志》改为《姓氏录》,让杂色入流,打破士族与庶族之间的界限,对后世也有着极意义。
其实早在唐太宗时代,就对《氏族志》进行过一次修订,那么《氏族志》到底代表着什么,为什么唐太宗、武则天都要对它“动手动脚”呢?

氏族,就是士族,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贵族。但在唐初,社会上所认可的贵族并不包括和太宗征战天下的功臣们,就连皇室也是勉强入围。
那么,唐初社会上认可的贵族都有谁呢?当时认可的士族是南北朝时期遗留下来的旧勋贵。
东汉时期豪强大地主崛起,形成所谓的“士族”,在政治、经济上都享有特权;到东汉末期,门第成为当官的先决条件;至魏晋时期,九品中正制从国家法律层面认可了士族的特权,最大的特点就是可以世袭,由此门阀制度形成。
比如东汉末年割据时代的北方大门阀袁绍,出身四世三公之家,累世公卿,所以,厉害的可能不是他,而是他的姓氏和他的祖宗们。
在门阀观念之下,不要以为你是地主就很牛,你的姓氏不在门阀士族之列,你就只能被称为庶族、寒门。
所以能称之为士族的人,在政治地位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与庶族、寒门悬殊很大。
那么庶族有没有可能挤入士族呢?很难。
在门阀制度下,社会地位以婚配来体现,但是士族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霸主地位,他们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原则,不与庶族通婚。
东晋是以北方大族为主体,联合南方大族共同执政的政权,也是门阀制度发展的鼎盛时期,涌现出一大批大门阀,比如:琅琊王氏、颍川庾氏、龙亢桓氏、陈郡谢氏、太原王氏等。
但到了南北朝时,士族地主衰败,庶族地主崛起,并逐渐在国家事务中占有一席之地。

再到北朝北魏时期,孝文帝推行汉化,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其中就包括重新修订士族门阀,主要目的在于让鲜卑贵族门阀化,从而使他们与汉族士族处于同等地位。
不过鲜卑贵族的好日子也没过几天,到了隋朝,隋文帝废除了九品中正制,推出了科举制,取消了士族地主世袭做官、世代控制地方行政大权的特权。
这也就标志着士族特权制度化的终结,士族门阀制度走向崩溃,但要注意,这并不代表士族的彻底消失。
李唐王朝的建立,就是依靠关陇贵族,同时还有山东士族、江南士族和部分庶族地方力量的支持。
所以,在唐初,士族力量虽然衰退,但由于他们的文化底蕴深厚,所以,在社会上仍然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地位。
在婚配方面,他们仍旧牢牢把握着主动权,靠着他们的旧门第,吸引了李唐王朝的“新官之辈”。
李唐新贵虽然位居高官,有很大的政治优势,但他们的社会地位却不高。为了提高自己的社会声望,有些人不惜出高价向山东旧族买婚姻。
这种有权力而无地位的情况,对李唐王朝是一种极大的讽刺,更何况,那些山东旧族甚至没把皇室放在眼里。

太宗即位后,在朝廷重臣中,山东庶族占有很大比例。比如太宗时期的28位宰相,除高祖时的旧相外,其中22人就是山东人,如高士廉、房玄龄、魏徵、李勣、张亮、马周、崔仁师等,而且大多都是庶族,也包括李唐皇室在内。
面对这种尴尬的境遇,到了贞观初年,随着各地军事征服的结束,国家各项工作开始步入正轨,为了加强皇权统治,以及提高朝中新贵们的社会地位,太宗瞄上了《氏族志》。
唐太宗修订氏族志的要求,只有一条,那就是“欲崇树今朝冠冕”,而“不论数代已前,只取今日官品、人才作等级”,这是修订氏族志的基本原则。
由此,旧有士族继隋文帝之后,又经历了新一轮打击,而那些庶族出身位及高官的人则成为最大受益者。
同时门第观念也发生重大变化,五品之家终身免除徭役,五品以上官员则享有政治、经济上的特权。
也就是说,旧有的门阀贵族要想取得种种特权,也只能通过入仕这条路。由此,唐朝开创了以官品为本,依据官品高低不同而享有对应的特权。
从此,再高的门第,没有官职也很难再享有各种特权了。
由此,我们也发现,唐太宗修订《氏族志》的目的,重在提高皇室及当朝重臣的政治和社会地位,改变人们对以往门阀观念的认知。
那么,在武则天的怂恿下,高宗再次修订《氏族志》,又有什么目的呢?

武则天在皇后之位稳固后,于显庆四年(659年)三月,由高宗下诏改《氏族志》为《姓氏录》。
为什么要再修《氏族志》,理由也很简单,那就是武则天家族没有列入郡望。
很明显,这是武则天自抬身价的神操作。
《姓氏录》的标准很明确,皇朝得五品者皆可列入其中,而且与《氏族志》不同的是,《姓氏录》与传统的婚宦、血统、门风、家学无关,一律不注明郡望,完全以官品高下排列等级。
在我们现代人眼中,或许认为本身就应该这样排,但在唐初重视门第,门阀观念的残余影响力还很深远的情况下,对于官员而言,不论官品多高,都依旧十分看重门户、姓氏,并把立门户、传姓氏当作头等大事。
在新标准下,武则天与长孙皇后的家族并列为第一等,但长孙无忌由于在政治上的失势,已被排除在外。
李勣之家也进入第一等,许敬宗、李义府这些奸佞之臣,也以宰相资格进入第二等,连以军功至位五品以上的军卒们也跻身其中。
打破家庭出身和社会认可的门第垄断,比太宗一朝更加注重当下官员的功勋,比如在军功上,新收录的大多是近期对外战争中涌现出的新的英雄人物。
即使是庶族出身的普通战士,通过军功累积,达到五品,就可上升为士族,这种利益的重新分配,也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这样一来,五品以上的人就成了钦定的士族,在中层以上的官员中,特别是在武官中,武则天成功收买了一批拥护者,军队指挥官中的不少人,都成了武则天的党羽。
长孙无忌的失败,主要原因之一也在于在兵权上的丧失,导致再没有能力发动政变,相反,武则天则逐渐控制了军队,由此掌握了主动权。
由此,不难看出,对《姓氏录》的修订,不只是抬高武则天宗族的地位,更有一大批中下层官员的地位也得到了提升,这些人自然会在政治上倒向武则天,从而巩固武则天的地位。
除了修订《姓氏录》,武则天还把大量“杂色”放入“流内”。
正统的官僚阶层称为“正色”,也就是流内官,“杂色”与“正色”相对,指的是流外官,就好比足球场上的替补球员。
正色与杂色的关系就是,只有流内官退下一小批后,流外官才能相应的替补上场,这叫做“入流”。

“流外官”一向为高门大族所不齿,一般都由庶族担任,这就好比孙悟空在意识到弼马温这个官职后,说这是一个不入流的小官,而且一生以此为耻。
尽管官小,但杂色入流在太宗朝也不容易,也是要经过严格铨选的,所以入流量并不大。
但武则天夺得皇后位后,入流量便突然猛增了,而且几乎不经过什么铨选就可入流。
所以,杂色入流也是武则天大批收买人心的一种手段,大批胥吏得以入流,从而在流内低层官员中,武后得到了一批拥护者。
此外,再说一下科举制,虽然隋朝就开创了科举,但由于当时门阀制度的影响,科举制仍然不是很流行。
到唐朝时,科举入仕的人员也很有限,进士每年平均也就十几个人,庇荫为官的制度仍然盛行,而且贵族子弟上升的速度非常快,勋旧大臣的子孙一下就可以跃居高官行列。
在武则天上位后,科举制也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些变化,那就是“制科”考试开始多了起来。
制科是皇帝临时下诏选拔特殊人才的途径,高宗永徽三年之后,不断设科举人。比如张九龄就是制科入仕的。
武则天也看到了通过制科选拔人才在收买人心方面的效应,所以在她后来临朝称制后,便大开制科,既以禄位收天下人心,又选拔出一批经世治国之才。
综上所述,一本《氏族志》,太宗修订,高宗又修订,修来修去,目的都一样,都是为了自抬身价,以此拉拢当朝官员人心所向,武则天就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