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集贸市场里摆着各式各样的篾货很少有人关顾,我就会想起村村寨寨周围一簇簇的竹子也是无人理睬。我不禁在心里发问:“难道竹器真要淡出现代人的生活了吗?竹子可是陪伴着人类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老辈流传着一句话:“养儿子不如栽竹子。”每年卖竹子的确有一笔可观的收入,打酒买烟、买油盐酱醋、缝套新衣服过年,无需向儿女伸手、看他们的脸色。许多人年轻时候都会在房前屋后、田头地边、河畔沟湾栽下一些竹子,为养老作准备。只要有竹子,买竹子的人会自己砍,主人站在旁边指挥,过度砍伐会导致来年的竹笋又瘦又小。砍竹子的活不算重,但是考验着人的观察和思考能力。如果只想瞄准目标砍几棵是很难做到的,左顾右盼刀子都砍不到竹子上,甚至还会擦伤手上的皮肤。好不容易砍断了,夹在竹林中间的竹子也是纹丝不动地站着。砍竹子要从外到内,一层一层地砍倒,拖到一边修掉细枝,按粗细长短分类放好,捆起来卖给人家拉走。哪怕是被虫蛀过的断尖竹子也要砍下来,留出位置给新生的竹笋。修下来的枝叶留在根上腐烂变成肥料——回报竹根,来年让子孙长得更多更肥。新生的竹笋都包着一层层带绒毛的笋叶,一棵棵竹桩还是不放心地守护着子孙。


前人栽树,后人享受,是种树的乐趣。现在变成了前人栽竹,后人受苦。公路边、村子旁的竹林一片生机勃勃,一棵棵标致的竹子长得挨挨挤挤、密不透风。有一大层皮都发黄的竹子,好似在展示着自己的年龄,祈求着有人发现它的价值。田边地头的竹子生长快,形成一大片树荫遮挡庄稼的阳光,还会吸食水分。有人干脆放火烧,大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势头。竹子的生命力确实很强,也很会保护自己。久旱无雨的时候,它就让叶子全部枯死,减少水分丧失,等到雨水落地又重新长出新叶来。要彻底铲除竹子就只有连根刨起,费时费力,哪怕是寒冷的冬天也要弄得汗流浃背、腰酸背痛。


许多人认为竹子被遗忘是竹器都被塑料制品所代替,只有种山药的人会砍一些插到田地里供给山药藤爬。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价格太高,高出塑料制品几倍。富民的老篾匠编不动了,屈指可数的中年篾匠又不愿干这苦活,年轻人更不愿意学。做生意的人为了货物品种多样,就是所谓的一只羊要放,一群羊也是放。只好从外地进货,几次倒手,豆腐盘成了肉价钱。如果是就地取材价格降低,消费者还是愿意购买使用的。健康无公害的竹制品是其他任何物品无法替代的。记得我们小时候,村里30多岁的男人都要学编篾货,算不上是一种技能,而是自己会做不用求人。粪箕、篮子、碳箩……编篾货不光是男人的专利,女人照样能编,而且编得又快又好。多数人家都是自编自用,实在不会编的人就趁农闲的时间砍一捆竹子扛到他人家或者请人到家里来编,吃上两顿饭或是帮忙做点事作为酬谢。我父亲编出来的篮子、碳箩、粪箕都是有模有样,就是背箩的样子差一些,还会根据自己的需求编一些用具,尽管样子不好看,还是很实用。经常有人把竹子扛到院子里来,他就利用空闲时间断断续续地编,手上厚厚的老茧换来了助人为乐的好名声。


竹编是一种工具简单、技术性强的行业。利用一把篾刀、锯子和成捆成捆的竹子就能编出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和工艺品。从古到今,竹子在人们的生活中确实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篱笆、筷子、筲箕、箸篓、筛子、簸箕、箩筐、提篮、蔑帽、桌子、凳子……有人甚至还能用竹子编成蚊帐,不仅能把蚊子挡在外面,还有装饰作用。编竹器是一门传统技术,尤其是精致的筛子、簸箕、提篮等器具不是一般的篾匠就能编的。需要拜师学艺,编竹器有一系列的工序:破竹很简单,划蔑就是细活。根据需要把篾片划成宽窄不一、厚薄不等、还有的要削成圆条,一根篾片要分成五六层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了。编织就是精细活,竹器的形状、大小、严实要求考验着篾匠的技术。编竹器对双手的损伤很大,经常会留下一道道口子,戴上手套又变得不灵活。成为老篾匠的手心和手背都磨得发硬才耐得住篾片摩擦,年轻人是受不了这些苦的。现代人买东西,不光要实用,还要讲究美观,对篾匠的要求也就更高。我曾经在电视上看到,竹编工艺品的师傅也是担心后继无人。我们这里的篾匠手艺也将失传,成片成片的水竹招人讨厌就是一个信号。


竹子的种类很多,除了公园里种植的观赏竹外,富民人栽种的主要是水竹、金竹、实心竹。实心竹可以用来做粪瓢把和扁担。金竹可以用来建塑料大棚、插在地里供藤本植物爬。水竹易栽易活,用途广泛。既美化了环境,又能用来编织使用工具。粪箕、篮子、碳箩这些粗糙的用具,每个村都有几个人会编。秋冬季节,正好是农闲,砍下来的竹子编成竹器不容易遭重虫蛀。只要砍一捆竹子扛到蔑匠家里,几天就能编好,随便给点钱或是拿些自己田地里出产的东西作为酬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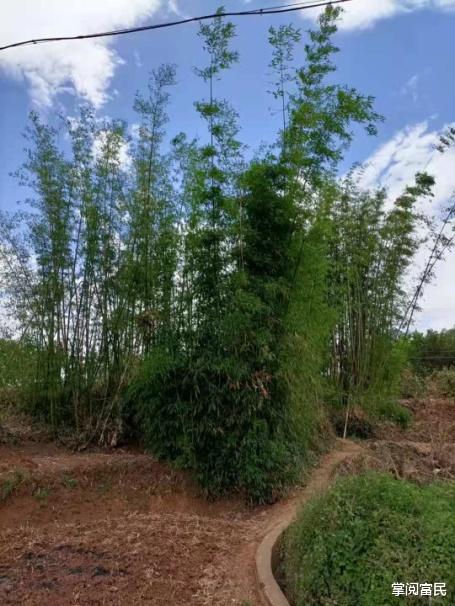

上个世纪中期,为了满足人们对竹制品的需求还成立过竹器社,后来县城南面的松林村、者北一带的公路沿线编竹器是非常有名的,一度出现竹子紧缺的旧局面。在大量的竹器被铝制品和塑料制品所代替的今天,水竹变成了废物。竹子除了编器具外,还可以用来造纸,我写这篇文章,就是希望有人发现水竹的价值,发挥它应有的作用。
END
作者/杨芝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