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祐四年(1317年),张养浩为元政府收购粮食,两次在兴和驿站中逗留,认识了一个在驿站中供役的人,叫佟锁住。以下就是张养浩讲述的关于佟锁住的故事:
近几年来,京师居民中的未成年男女,离开家门外出时往往被奸民拐胁、隐藏起来。女的强迫她们作婢女,男的则被强制作奴仆。不肯服从的,就把他们运送到边远地区,如辽东、漠北等地,用他们换取羊、马、牛、驼,获取钱财。幸而因事情败露获救的人很少,不幸而被互相转卖,使他们与父母、兄弟、姐妹等家人死生不能相闻者,到处都有。呜呼!处在皇帝眼皮底下,习俗尚且如此,难道不是大怪事吗?

丁巳年(1317年)春天,在兴和驿站,驿卒佟锁住把他的亲身经历向我述说。他原来是江西泰和县人。七岁时与一群儿童在街巷中游戏,被经过附近的一个骑者劫持而去。向北一直渡过了三条大河,翻越了不知道多少山岭,才到达兴和。骑者到一家酒店饮酒,就叫佟锁住在那里打杂。酒店老板一目失明。这时佟锁住才知道骑者已把他卖给酒店老板了。因为总算可以留在这里,不必继续北行,所以佟锁住没有抗辩。
住了几个月后,店老板又叫他跟随几个骑马的人北行,说是跟他们去取一笔债务。走了两天还一无所得,只是说住的地方还很远,等到了,就让他拿了钱回去。佟锁住已猜到他又被偷偷转卖掉了。但他听说当地的习俗,奴婢如果逃亡,被抓获后就要用烙铁烫印,所以只好假装很愿意离开旧主人去服侍新主人。所经之处,都是秃山,没有城镇住家。天气稍阴就刮起大风雪,使人难以前行。

这里的人们都以所养头畜的多少来区别贫富,身上穿的都是皮衣毛衣,食物只有马奶和肉,没有菽、粟之类粮食作物。家家户户都住在用毛毡做的庐帐里。
新主人把佟锁住叫作“察罕”(蒙语,译言白,经常被用作人名),又给他一领羊皮衣,两千多头羊,令他放牧。主人警告他说:“如果羊瘦了、伤了、逃失了或者无缘无故死了,我就要打你。”住的地方离牧地有20里,每次出去要携带路上吃的东西,与其他牧者相约共行,不然就会迷路,回不了家。同行的羊合在一起有一万多头,其他的牧畜也差不多一样多。
从高坡处望去,满山遍野,就像云霞铺散在地上。各人的羊群都互相混淆,认不出来,佟锁住又担心又害怕。其他放牧的人告诉他:“不要紧张。到回去的时候,它们就各归自己的群落了。”等到傍晚,果然如此,他这才放下心来。与一起牧羊的十几个人交谈,都是中原的良家子弟,被奸民辗转贩卖到那里去的。

于是佟锁住想,原来背井离乡、与父母亲戚不通音讯、流落到异域之地、变作他人奴婢的,还不止他一个人。他的心中也就稍获安慰。
有一天,他的羊群正在山坡的坡脚流连,突然有百余头牛从山顶冲下来饮水,羊群来不及躲避,被踩死十几只。想想难逃一顿毒打,佟锁住便脱下皮衣丢在山上,以迷惑追寻的人,下决心逃离那个地方。当时他十六七岁。一开始每天走100里,几日后,可以走200里,甚至300里。只是一路朝南。饿了就抓一把野葱和溪水咽下去,到夜里则找一家有灯火的庐帐借宿。有人问话,就用蒙古语回答,所以倒也没有人怀疑他。
后来在路上正好遇到一个朝廷使臣,于是佟锁住跪在他面前诉说自己的经历。使臣很同情他,就给他一匹备用的马,让他骑乘。佟锁住这才重新回到兴和。

这时候他到官府去状告那个酒店老板。老板以贩卖人口被治罪,佟锁住则被安置在当地驿站中当役卒。我在那里遇见他的时候,他在兴和作驿卒已经有一年多了。
听了佟锁住的身世,我十分同情他。于是就问他:“我要是让你回到家乡去,与你的父母、兄弟相见,怎么样?”佟锁住叩头流泪说:“我当然是极愿意的。”我就命令有关部门下了一道公文给沿途各驿站,供给佟锁住衣粮,护送他回到乡里。于戏!天下像佟锁住这样的人何其多呵!怎么能都像他那样碰到我,所以能够回到家乡呢?

贯云石海牙(1286-1324年),畏吾几人,元初著名的将领阿里海牙之孙,父亲为阿里海牙次子,名贯只哥,故以贯为姓氏。传说他的母亲尝夜梦神人摘天星为明珠以授,被她吞下肚里,因怀贯云石。
少年时代的贯云石俨然是一个“善骑射、工马槊”的将门之子。他在十三四岁时,曾经命壮士驱恶马疾驰。贯云石持长矛迎着奔马凝立。待马驰至面前,他翻身腾越马上,舞动长矛,四周生风。
初袭父爵,为两淮万户府达鲁花赤,驻永城。他开始对汉文化产生强烈兴趣,大概就在部令行伍的这几年当中。

有一天,他忽然对弟弟忽都海涯说:“我生来做官的志趣淡薄。祖父的爵位,当时不敢不承袭。现在已经好几年过去,应该让你来做了。”当天就写信把决定告诉父亲,并正式向政府呈交公文说明情况,解下虎符交给弟弟。
此后他整天和结交的文人游山玩水,互相唱和。或许是在姚燧做江东廉访使、养病太平的期间,贯云石去向这位名声很大的文人问学。他的文章、词曲都给姚燧留下很深的印象。
姚燧被召到仁宗潜邸做侍臣后,再三向仁宗推荐贯云石。仁宗早已听说过贯云石把三品的大官让给弟弟的事,于是把他召去做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刺(即后来的英宗)的“说书秀才”。仁宗即位后,贯云石在翰林院做学士,参加了科举考试条规的制定。

这时他颇有一点恃才用世的雄心,曾向仁宗上书条陈“六事”,建议朝廷释边成以修文德,教太子以正国本,立谏官以辅圣德,表姓氏以旌勋胄,定服色以变风俗,举贤才以恢至道。这六条建议表明,贯云石的政治主张,基本上是以传统儒学作为资源而形成的。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后来贯云石突然放弃了他的政治抱负。据说他向人宣布:“过去我辞去高官显爵而甘居卑位,现在接受翰林侍从的职位,它的名位比我辞让的军职还要高。人们会批评我沽钓美誉,贪恋高官。现在应该离去了!”乃立即辞去官职,回到江南。

壮年南下的贯云石海牙,很快变成一个颇负盛名的文学大家。他遍历名胜古迹,所至之处,高人韵士、年轻学子、方外奇人,都愿意与他结交,“得其词翰,片言尺牍,如获珙璧”。贯云石有点倦于应酬了。于是变姓易名,躲到杭州隐居晦迹。过去游历梁山泺时,他见到渔夫织芦花絮为被,心里很喜欢,要用自己的绸被子来交换。渔夫看见他以贵易贱,知道他不是普通人,对他说:“你要想得到这条被子,就要写一首诗留给我。”
贯云石“援笔立就”,这就是后来广为流传的《芦花被》:“探得芦花不涴尘,翠蓑聊复藉为菌。西风刮梦秋无际,夜月无香雪满身。毛骨已随天地老,声名不让古今贫。青绫莫为鸳鸯妒,欺乃声中别有春。”隐居杭州之后,他就自号“芦花道人”。他曾经入天目山,去见当时闻名于世的禅师中峰明本,乃每夏坐禅杭州郊区的包山,暑退方始入城。

学禅以后,他写的文章境界渐入深邃,诗歌也比从前更加冲淡简远,草书、隶书等变化古人,自成一家。晚年的贯云石,诗、曲、书、文都达到极高的造诣。当然,他在文学方面成就最大的还数元曲(又称乐府)。所制小令、套曲,清新流畅,“俊逸为当行之冠”。他旧以“酸斋”为号,同时另有徐某号“甜斋”,也擅长写曲,故时称“酸甜乐府”。
他有一首小令:“新秋至,人乍别。顺长江水流残月,悠悠画船东去也。这思量,起头儿一夜。”只用二十余字,活生生地描绘出与情人初别之夜的缠绵感情。又有《清江引》:“竞功名,有如车下坡,惊险谁号破?昨日玉堂臣,今日遭残祸。争如我避风波,走在安乐窝!
随着他的性情越来越淡泊高洁,贯云石的行踪也“与世接渐疏”。白日正午已过,他还“拥被坚卧”,宾客多不得见。僮仆受他的影响,也以昼为夜。

他就这样于“道味日浓”之间,死于钱塘寓舍,年39岁。贯云石视死生如昼尽夜来,没有什么虑惧。临终前不久,他写过一首诗云:“洞花幽草(大概是他两个小妾的名号)结良缘,被我瞒他四十年。今日不留生死相,海天秋月一般圆。”
在寄迹杭州的最后十几年间,贯云石留下了不少戏谑人生的轶事。据说他曾在杭州“卖药市肆”,但是又有一则轶闻说,他在那里立碑兜售的,乃是“货卖第一人间快活丸”。当真有人来购买这种“快活丸”时,贯云石对买者伸展两手,大笑一声。领会了他的意思的人,于是也大笑而去。

某日,杭州有一群衣冠士人到虎跑泉燕饮游观。席间赋诗,以“泉”字为韵。当轮到其中一人时,他只会哦哦呻吟“泉”“泉”“泉”,却作不出诗来。这时有一老叟拖着拐杖走过来,随口接应道:“泉泉泉,乱进珍珠个个圆。玉斧斫开顽石髓,金钩搭出老龙涎。”这群人大吃一惊,问道:“你就是酸斋贯吗?”答曰:“然,然,然。”众人于是邀请他同饮,尽醉乃去。
汪元量,字大有,号水云先生,钱唐人。南宋度宗时,以善鼓琴供奉内廷。宋元鼎革之际,当朝中重臣纷纷不辞而别的时候,他却以区区供奉琴师,不预士大夫之列,而眷怀故主,始终与赵氏的孤儿寡母共患难。不仅相伴到临安城归元,而且追随三宫北上,长期羁留大都,直到宋皇室的遗孀们先后去世。

作为一个在深宫之中目睹南宋亡国全过程的见证人,汪元量用他行吟诗人快逸奔放的才气,留下了大量的纪事诗。著名的《湖州歌九十八首》,从“丙子(1276年)正月十日三”开篇,一直写到“三殿”在大都的凄窘岁月。所以有人说,“开元、天宝之事记于草堂(指杜甫),后人以诗史目之;水云之诗,亦宋亡之诗史”。
他描写临安城破之日的诗曰:“西塞山边日落处,北关门外雨来天。南人堕泪北人笑,臣甫低头拜杜鹃。”又曰:“钱塘江上雨初干,风入端门阵阵酸。万马乱嘶临警跸,三宫洒泪湿铃鸾。童儿空想追徐福,厉鬼终当灭贺兰。若议和亲休练卒,婵娟应遣嫁呼韩。”

宋宗室北上以后,虽然不能再像从前那般摆阔,但生活富足似乎还是不成问题的。他们的悲哀,主要是来自亡国之痛的刺激。一些男女宫人在这时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意志。陈氏和朱氏两个宫娥,与两名婢姬在一起自缢身亡,在朱氏衣袖里留下的绝命诗写道:“既已辱国,幸免辱身。世食宋禄,羞为北臣。妾辈之死,守于一贞。忠臣孝子,愿以自新。”被留用于元内廷的一些宋内官中,有一个人叫罗太元,后来因病遣出。他的侄子后来成了泰定帝时很得宠的宦官,达官贵人多与之相结交,罗太元在当时却不肯见他。
有一次侄子又来求见,罗太元闭门不纳,在屋里对他说:“你阿叔病,要静坐。你何故只要来恼我?使受你几拜却要何用?人道你是泰山,我道你是冰山。我常对你说,莫要如此,只不依我。你若敬我时,对太后宫里,明白奏我老且病颓。乞骸骨归乡。若放我归杭州(罗太元是杭州人),便是救我!”离开大都之日,罗太元对着身后的齐化门说:“齐化门,从此别矣!我再不复相见你矣。”遂大笑离去。

汪元量采取的态度,与上述诸人有些不同。据说他曾奉命为忽必烈奏琴,于是得赐为“黄冠师”,从此“羽扇纶巾”。但他不得已与元室相周旋,好像是为了更方便用琴声去慰藉在大都的亡国君臣们。他演奏的时候,使听众“出于人间,落乎天上”。时人说,汪氏之琴,像是天意为了让北渡的亡国君臣稍得“娱清夜、释羁旅”而有心安排的。“琴本出于怨,而怨者听之亦乐,谓其能雪其心之所谓也”。
他时常与度宗的昭仪王清惠(这时已奉诏命出家为尼)消遣。所作《秋日酬王昭仪》云:“愁到浓时酒自斟,挑灯看剑泪痕深。黄金台隗少知己,碧玉调湘空好音。万叶秋风孤馆梦,一灯夜雨故乡心。庭前昨夜梧桐语,劲气萧萧人短襟。”

这时文天祥被软禁在大都。他曾去拜会文天祥,以“丞相必以忠孝白天下”相敦促,就是要他赶快请死。他为文天祥弹琴,演奏了““拘幽'以下十操”。汪元量留下一首题目很长的诗,记述他与天文祥的会面。这首诗的题目是《文山丞相丙子自京口脱去,变姓名作清江刘洙。今日相对,得非梦耶?》。诗云:“昔年变姓走淮滨,虎豹纵横独怆神。青海茫茫建故国,黄尘黯黯泣孤臣。魏睢张禄梦中梦,越蠡陶朱身后身。今日相看论往事,刘洙元是姓文人。”粤人谢翱将归死江南。临行之时,旧宫人会者十八人,在城边宴饮告别。汪元量也抚琴相送,“行泪雨下,悲不自胜”。

他是宋朝宫室中好几人的送终者。“女道士王昭仪”“太皇谢太后”都先他死去。汪元量为谢太后作的挽章写道:“大漠阴风起,羁旅孤血泪。忽闻天下母,已赴月中仙。哀乐浮云外,荣枯逝水前。遗书乞骸骨,归葬越山边。”少帝赵属比汪元量活得更久,他被忽必烈遣往藏地学佛。汪元量为他送行的诗曰:“木老(赵暴受封为“木波讲师',故云)西天去,袈裟说梵文。生前从此别,去后不相闻。忍听北方雁,愁看西域云。永怀心未已,梁月白纷纷。”
文天祥被处决后,汪元量也写诗咏之:“厓山禽得到燕山,此老从容就义难。生愧夷齐尚周粟,死同巡远只唐官。雪中绝寒魂何往,月满通衢骨未寒。一剑固知公所欠,要留青史与人看。”

赵累被遣往藏地萨斯迦寺,事在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汪元量在大都已没有什么人需要陪伴。他回到江南,当在此后不久。在江南,他著黄冠、据枯杖,出入于名山大湖之间,若飘风行云,世人无法知道他的去留之迹。江西人把他当成神仙,甚至绘制他的形象来供奉。
汪元量以他的“南吟北啸”来记录亡国之戚、去国之苦、间关愁叹之状。时人说,读汪公之诗而不坠泪者,差不多不能再叫他人了。
还有人说,他的歌诗,就像“再嫁妇人望故夫之陇(此指故墓),神销意在,而不敢出声哭也”。因为他的诗哀而不怨,只是“欷歔而悲”而已,所以在元代就流传于世,而没有被禁止。

自然也总会有人对他持批评的态度。比如有一种意见认为:宋朝末年,元兵压境,两宫居然仍以琴酒自娱。据说度宗在宫中就随时拿着酒壶,尽日不醉。这种情况表明,一定有人在用声色之乐蛊惑皇帝。说者婉转地指斥汪元量以琴惑君,接着说:“及大事已去,独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嘻,亦晚矣!”
中国传统文人总是把亡国的责任推到女人身上、皇帝的某个“左右”身上。现在我们又看到,还有人要把南宋灭亡的责任推给一个琴师。这当然是不公平的。宋三宫蒙尘时,像汪元量这样“其心怏怏,奔走万里若不释者”的人其实并不多。所以清代的四库馆臣要说,宋季公卿若面对汪元量,“实视之有愧”。这个评价,基本上是中肯的。

金姬名金儿,济南章邱人李素的女儿。
金姬的外曾祖李某也是章邱人,至元年间被元政府派役,运送粮钱到大都。在大都,李某遇到宋旧宫人金德淑,被她的姿色所迷,乃留都不归。生了一个儿子,因名都生。李某死后,都生从母姓金,与章邱李某的旧族不通音讯。都生成家后生了一个女儿,也长得很漂亮。这时大都城里有一个章邱籍人,叫李素,想要娶一个美人为妻。都生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她就是金儿的母亲。
金儿从小聪慧明敏,资质妙丽。识字以后,日诵古今经史和佛、道百家之书。李素得名医张明远之传,精于医卜之道,把他的技艺全都传授给了金儿。金儿对卜筮之术特别有兴趣,很快便“自极玄妙,言人祸福皆响应”,连李素也自觉及不上她。

这时已经是元末,政局动荡。李素决定举家投奔章邱族人。他们很可能坐船从大运河南归。由于山东兵乱道阻,李素一家只好沿河继续南行,辗转曲折,来到盱眙县城。相传金儿在初渡淮水到达盱眙后,曾在客舍题诗,曰:“马足燕山雪,船头泗水云。客身和雁影,飘迫过孤村。”但她的闲情逸致很快被突如其来的一场家庭风波搅得粉碎。
他们客居盱眙时正值酷暑。李素的妻子金氏身着短袄。李素偶尔发现金氏肘下有一个铜钱大小的黑痣,与自己身上所长的完全一样。于是互相细问家世。这才发现,李素原来是至元年间那个留都不归的李某在章邱老家的亲孙子。

这就是说,李素的岳父都生实际上是与李素生父同父异母的弟弟,而李素之妻金氏竟是他自己的从妹辈。这对夫妻“相顾惭恨,不能自存”,遂决定改为兄妹相称,别居于二室。他们的女儿金儿听说了这件事,便剪去头发,发誓要出家做尼姑,“以赎骨肉之耻”。
这时正是至正十四年。苏北私盐走私犯张士诚举兵反元,为躲避元廷遣往征进的苗兵军锋,从扬州移至高邮,并抄掠邻郡。李素一家在盱眙为张士诚军俘掠。不久,金儿被分配到张士诚母亲“太妃”曹氏的帐中做婢女。
这年九月,元廷发师号称百万,由丞相脱脱亲自统率,将张士诚团团围困在高邮城里。曹氏命金儿卜凶吉。金儿卜之,得“无亡之小过”,于是对曹氏宣称,“取威定霸,决于此矣”。到了十一月,城中人心危畏,张士诚想投降,又怕元廷不肯赦免他,犹移再三。曹氏召金儿再卜。

时值二更,忽然听到冬雷响空。金儿拜贺说:“明天可以出城应战了!”中夜,她登城楼仰视天象良久。天将曙,入告曹氏说:“龙文虎气,都显现在我方营上。时不可失,请赶快出兵击敌。”
据说正是同一夜,顺帝下诏削脱脱兵权的消息传到元军兵营。临阵易帅,兵心激变,元军在一夜之间气丧魄散,围城阵线顷时瓦解。张士诚乘机出击,大获全胜。金儿由此名声大振,大家都叫她“金姑姑”。虽然她从此不再剪发、穿道服,但仍修炼如故。
张士诚本来没有什么大志,满足于在苏北做自王一方的土皇帝,听说江南“钱粮之多,子女玉帛之富”,贪心渐起,但又不敢贸然深入江南,态度十分犹豫。曹氏命金儿再卜。金儿称得吉卦,并且套用当时已经流传的《扶箕诗》写成一绝云:“天遣魔兵杀不平,世人能有几人平。待看日月双平照,杀尽不平方太平”。张士诚这才决定派兄弟张士德先行领兵渡江,攻取江南。

当时“吴会(指苏州)未下,雌雄未决,乃先自空其巢穴,以犯不测之险”。张士诚此举确实需要一定的胆量。金儿的卜算,大概真的给他增加了不少的勇气。
至正十五年二月,张士德攻占苏州。三月,张士诚奉母亲曹氏至通州,预备过江。母子登狼山观长江之险。这时候张士诚第一次见到“金姑姑”。金儿奉命出见时,“青衣跣足,垂涕而出”。曹氏连忙叫她回去改装。金儿换装后再与张士诚见面,张士诚“凝志忘言,注目谛视,唯唯再三”。下狼山的时候,他对金儿说:“我听说,古代的圣人不在朝堂则在算卦人之中。诚如太夫人所说,你是真天人。怎么能让你埋没在婢女待儿之中!”
长江水深浪急,张士诚又命金儿卜渡江吉日,金儿口占十六字曰:“羊肠九索,相推稍前。止须王孙,乃得上天。”这时正好有福山富户曹氏发江船百艘、杀牛担酒来为张士诚“犒师”,于是张士诚大举渡江。乃至福山,仍纵将士肆行掳掠。曹氏迎降在先,不过免遭居戮而已。

在此前后,金儿似乎已看透张士诚不足以成大事,她奉命为张士诚卜“国运短长”,以“日月运行,一寒一暑。荣光赫赫,创业大数”为对。张士诚大喜。但她回去对父母却说,那句话的真正意思,是说张士诚的运命只有“天运一周”,即以十二辰为一纪,十二年之后难保“颠踬殒坠”。李素大惊说:“如今江南已下,鼎足势成,正好与他同享富贵,为什么出此不祥之言?”
金儿答道:“千里马不能与跛驴套在一起拉车,凤凰不能与燕雀为群。贤明的人也不能与不肖者混迹在一起。我可不愿做他们那等人的臣下。”父亲问:“那你为什么又要帮他占卦,动中事机?”金儿说:“君子虽然想高蹈远引,但还是愿意略显德泽于人,为群民除害,来显示天的好生恶杀之性。我这样做,只愿有功德于人间,不求个人的尊荣。父亲你是不能理解的。”
李素大怒,骂道:“女人就以容貌颜色来服侍人。闺门以外的事情都不是她的本分。从来没有听说女人能以王霸杂术而闻名于世的。”父女争辩再三,不欢而散。

但是张士诚却匪夷所思。他想试探金儿的心思,于是对她说:“我心中已默有所祷。你能卜得出是一件什么事吗?”卦成,金儿对曰:“不敢以告。”强之再三,她才说:“有三条蛆,因为追逐飞蝇掉进大锅里,灌饱了锅里的沸水,沉淹殪气而死,与母亲永别。”张士诚不甘心,说:“听说用龟甲占卜才能知真凶吉,你用的是中间空枯的鸡骨头,怎么可以完全相信?”他把一枝桃花插在金儿头上,说:“就以它为聘金吧。”
金儿自知不能免,于是要求先回去稍作安排。她与父母家人见面后,向天列拜,长跪私祷,然后就闭目绝虑,奄然无语。父母大惊,冲过去把她抱起来,大声叫她。金儿已经气绝身亡。

据说,明军进入苏州,乱兵掘金姬之墓,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蜕去”,棺椁中只有衣衾还在。
后来的人追述这段故事,说金儿“周旋戎幕,口不治腥膻之味(因为她修持吃斋),心不慕金玉之屋。······使强暴之主,朵颐(在这里指垂涎的意思)凝注而不敢肆为侵凌。譬之白璧夜投,贪夫自避”。金儿不满意元末社会的“不平”,却又找不到真正能解救天下的人,最后空有一副侠义心肠,只落得抱恨而死的可悲结局。
人们经常喜欢把社会比作一个戏剧大舞台。这个比喻其实有很大的缺点。观众从舞台上看到的,永远只能是很有限的几个主角的故事。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人都是众灵杂遝的一分子,都有一样活生生的灵魂,有自己的幻想、自尊、追求、辛酸和快乐。可是,要从过去的历史记载中找到有关丛脞众生的详细故事,又真是太难了!

政府编制人口统计的数字,往往是为了赋役的征收,所以这些数字是不是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总人口,也经常让历史学家猜测不已。以下讲述的,就是保留在片断资料中的元代商人、“烈女”、“节妇”、“孝友”和普通读书人的故事。
商人崔聚的故事。
崔氏本来是姜姓。姜太公之孙叔乙把封邑让给别人继承,自己跑到崔邑去居住,因以为氏。崔聚的上世是河北枣强人。北宋末遇水灾,六世祖徙家阳丘,就在那里占籍。世代以商业致富,名著乡里。崔聚的曾祖和祖父之名已佚失,父名泉,有四子,崔聚为长子。他天质博厚,有才干,懂交际。

小时候正好是金末丧乱之际,家中的财产损失殆尽。入元以后,崔聚已成人,于是以长子身份担当起重振家业的重任。他经营商业的原则,是以信用诚义为本,买卖交易灵活多变,坚持勤俭之道。不论寒暑昼夜,他都兢兢业业地盘算货物的进出有无,从不懈怠。南宋灭亡后,崔聚更把贸易范围扩大到湘湖之间,因此家赀钜万,在当地没有比他更富有的人。
家业既已丰饶,崔聚做人更加小心谨慎,和气宽厚,以诚德责己。借贷钱银与人,如果是贤人韵士,常常不收利息;遇到贫穷还不起钱的,干脆把借据销毁,不再讨还。有断炊之家,连忙去给济,生怕晚了。

乡里的人都知道他的德行。崔聚有五个儿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意识到自己老了,于是把家产平分,每个儿子都给一份,叮嘱他们不要使产业败落。他自己则拿着拐杖,从容拜访亲友,“尽东阡北陌之乐”。他在80岁时死去。
以上就是记载崔聚行迹的一块“先茔碑”所提供的关于他的全部内容。他经营的到底是什么产业,从碑文中一点也看不出来。尽管立碑时连崔聚祖父的名字也已经无法查考了,但碑文却还是硬把这一家与殷商时代的姜太公的孙子扯在一条血脉上。这两点都十分典型地反映出元代社会的精神气质和所崇风尚。

商人长年在外奔波,把妻子独自留在闺阁。商妇之怨不轻于征妇。杨维桢又有《商妇词》云:“荡子发航船,千里复万里。愿持金剪刀,去剪西江水。”要用剪刀把江河剪短,好让在外行商的丈夫早日归来。商妇的离怨又是何等深刻啊!“烈女”和“节妇”的故事。
胡烈妇,渤海刘平的妻子。至元七年(1270年),刘平当成枣阳,用车子装载了家人、行装共行。夜晚宿于沙河旁。突然窜出一只老虎,衔了刘平逃去。胡烈妇惊醒过来,连忙追上去,抓住老虎的一条腿不放,高声叫车中的儿子取刀杀虎。
老虎死,她扶持刘平到附近城镇求医,因伤势太重,终于没有救活。胡烈妇受朝廷旌表,远近闻名。时人多以“胡烈妇杀虎”为题作图。又有人题诗于图上曰:“丈夫不作屠龙举,健妇能成刺虎威。试看五行参运化,二阴(当指胡烈妇及其小儿)何盛一阳微!

霍家有两个媳妇,分别来自尹、杨两户,夫家是郑州人。至元年间,尹氏的丈夫霍耀卿死了。婆婆要尹氏改嫁。尹氏说:“妇人的德行只有贞节。再嫁而失节,我不愿意这样做。”婆婆问她:“世上的妇人,丈夫死了都要改嫁。人们并不认为她们有什么不对。为什么只有你觉得可耻?”尹氏回答:“人的志向本不相同。我只知道要按我自己的志向去做而已。”婆婆也就不再强迫她。
后来杨氏丈夫霍显卿又死了。杨氏担心婆婆会叫她改嫁,抢先对婆婆说:“我听说妯娌之间就像是兄弟,应当互相敬爱。现在您的大房媳妇守寡没有离开,我可以独自离家吗?我愿意与她一起共修妇道,终生侍奉婆婆。”婆婆说:“你如果真能这样做,我还有什么可以说的!”于是她们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这件事被上奏朝廷,受到政府的旌表。

只鲁花真,蒙古人。26岁时,她的丈夫忽都病死,发誓不再改嫁,奉养婆婆,超过25年。婆婆去世后,尘衣垢面,不事修饰,终身守在建于墓旁的陋屋里。至元年间受到朝廷的表彰。
冯淑安,字静君,出身官宦之家,被山阴县的县尹李如忠娶为继室。李如忠的前妻是一个蒙古族女子,生一子名任,才去世不久。
大德五年(1301年),李如忠病重,对冯氏说:“我很快就不行了。你怎么办?”冯氏引刀断发,誓不改嫁。李如忠死后两个月,她生下丈夫的遗腹子,取名李伏。李如忠和他前妻的族人都在北方。听说李如忠死于任上,留下很多遗产,两家一起赶到山阴。

冯氏正遇大病,他们乘机把李如忠的赀财和蒙古族母亲生的李任带回北方去了,撇下冯氏母子和李如忠及其前妻的灵柩。冯氏没有与他们计较,只是面对“一室萧然”早晚哭泣,邻里惨不忍闻。以后她卖掉陪嫁的衣妆,勉强把两人的灵柩浅埋在蕺山下,带着李如忠的遗腹子住在搭建于墓旁的小屋里。
这时她只有22岁。身体虚弱,苦自砥砺,靠做女师儒授徒维持生计。父母听说后来探视,舍不得她孤苦伶仃,劝她改嫁。冯氏爪面流血,不愿答应。这样过了20年,才凑足钱把李如忠的灵柩迁葬到汶上老家。齐鲁地方的人听说了她的故事,莫不叹息。

李顺儿,许州儒生李让的女儿,生性聪慧,能读经书。至正十五年(1355年)她18岁,未嫁在家。红巾军攻陷钧州,离许州很近了。李让对妻子说:“我家世代知书达礼,现在这个女儿要连累我们了。”女儿听见父亲的话,哭着说:“父母尽管去逃难,不要为我担心。”说完她立即跑到后园自缢而死。
陈淑真,富州人陈璧的女儿。陈壁是一个很传统的儒生。陈淑真七岁能诵诗鼓琴。元末,一家人避兵祸于龙兴。
至正十八年,陈友谅进攻龙兴。陈淑真见邻人仓皇来告,乃取琴坐在窗下弹起来。曲终流着眼泪说:“我从此再不能弹琴了!”父母听了很惊异,问她是什么意思,陈淑真说:“城被攻克以后,我一定会遭到侮辱,不如趁早死了。”次日陈友谅军进城。陈家寓所临近东湖,陈淑真投湖而死。

周如砥,女,19岁,未嫁。至正二十年,乡民乘天下大乱,揭竿而起。周如砥父是新昌县衙门中的典史,与女儿一起到县城西面的客僧岭避难。女儿被造反的人俘虏。领头的说:“我还没有娶妻,就拿你做妻子吧!”周女说:“我是周典史的女儿,死就死,怎么能答应你?”于是被杀死。
《元史·列女传》记录了一百多个妇女的事迹,用几乎相同的笔调讲述她们年轻守寡,或在元末乱世中恪守贞操而慨然自杀或被杀的“烈节”。
中国中世纪后期严重摧残妇女的两种恶劣习俗,即缠足和丈夫死后不许再嫁,都在元代,尤其是元代江南地区开始逐渐流行。官方意识形态通过旌表褒谥的阴险手段,把残酷的“礼教”内化成越来越多的妇女自觉的要求,再利用她们的行为催发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社会压力,渐渐把绝大多数妇女驱入痛苦的深渊。元代“节妇”的故事,只能是一部当时妇女的血泪史。

《元史》有《孝友传》两卷,用来“劝奖”“事亲笃孝”“居丧庐墓”“累世同居”“散财周急”等等“善俗”。这些“善俗”中间,当然沉淀着可以为现代民族精神的再建设进行创造性转换的积极因素,但它们强调吞噬个人和个性的宗族权威和父权,用死的拖住活的。所以即使在当时,也往往流于虚伪做作:在今天看来,更未免有些怪诞、悖情甚至不必要的残酷。
张闰,延安延长县人,隶属于汉军军籍。一家已经历八代而不曾分过家。家庭成员有百余口,互相没有闲言碎语。每天都令未出嫁的闺女和人门的媳妇们各聚一室做女红;完成的,收贮在同一库房里,各小家庭都没有私蓄。幼童啼哭时,凡有乳的妇人谁见到就由谁抱哺。嫁人的媳妇回娘家省亲,留下儿子,也由大家一起哺乳,不问是不是亲生的,儿辈也往往不知道谁为生母。

张闰在哥哥张显去世后,把家事全部托付给侄子张聚。张聚推辞说:“叔叔是父辈,应由叔叔主持。”张闰则说:“侄子是一家长支的后裔,应该由你来主持。”互相推让了很久,最终交给张聚。官绅大户听说张闰家的事迹,都自叹不如。至元二十八年,得到朝廷旌表。
孔全,亳州鹿邑人。父亲孔成病,孔全割下自己的股肉为父亲进补,使他痊愈。后来父亲死了,孔全居丧尽哀,在墓边搭棚守墓,亲自背土为父亲堆坟,每天挑土60次。因为风雨不能满数,等天晴后补足。为此三年,堆起广一亩、高三丈多的 坟堆。
张子夔,安西人。父死,每天夜半以背负土,用手肘、膝盖触地,匍匐到埋葬父亲的地方,筛细土为坟。

李鹏飞,池州人。生母姚氏是父亲的妾室,为正妻不容,把她改嫁给一个姓朱的人。李鹏飞年幼不知情,19岁时知道了这件事,思念生母,心情哀痛。于是立志学医救人,希望积功德,早日见到母亲。走访了整整三年,才在蕲州罗田县找到生母。这时朱家正在生流行病,李鹏飞就把她接回到自己家中奉养,很久以后,才重新送回朱家。从此时常渡江去探视。母亲死后,他总是在祭扫时节带子孙去祭墓,终生如此。
哈都赤,大都固安州人,天性笃孝。从小失去父亲,乃全力奉养母亲。母亲生病,医治不痊。哈都赤取下自己佩带的小刀,磨得十分锋利,拜天哭泣,说:“慈母生我不容易,今天我要捐身报答她。”于是割开左肋,取肉一片,做成汤羹让母亲吃。母亲说:“这是什么肉,会这样甘美?”几天后,她的病就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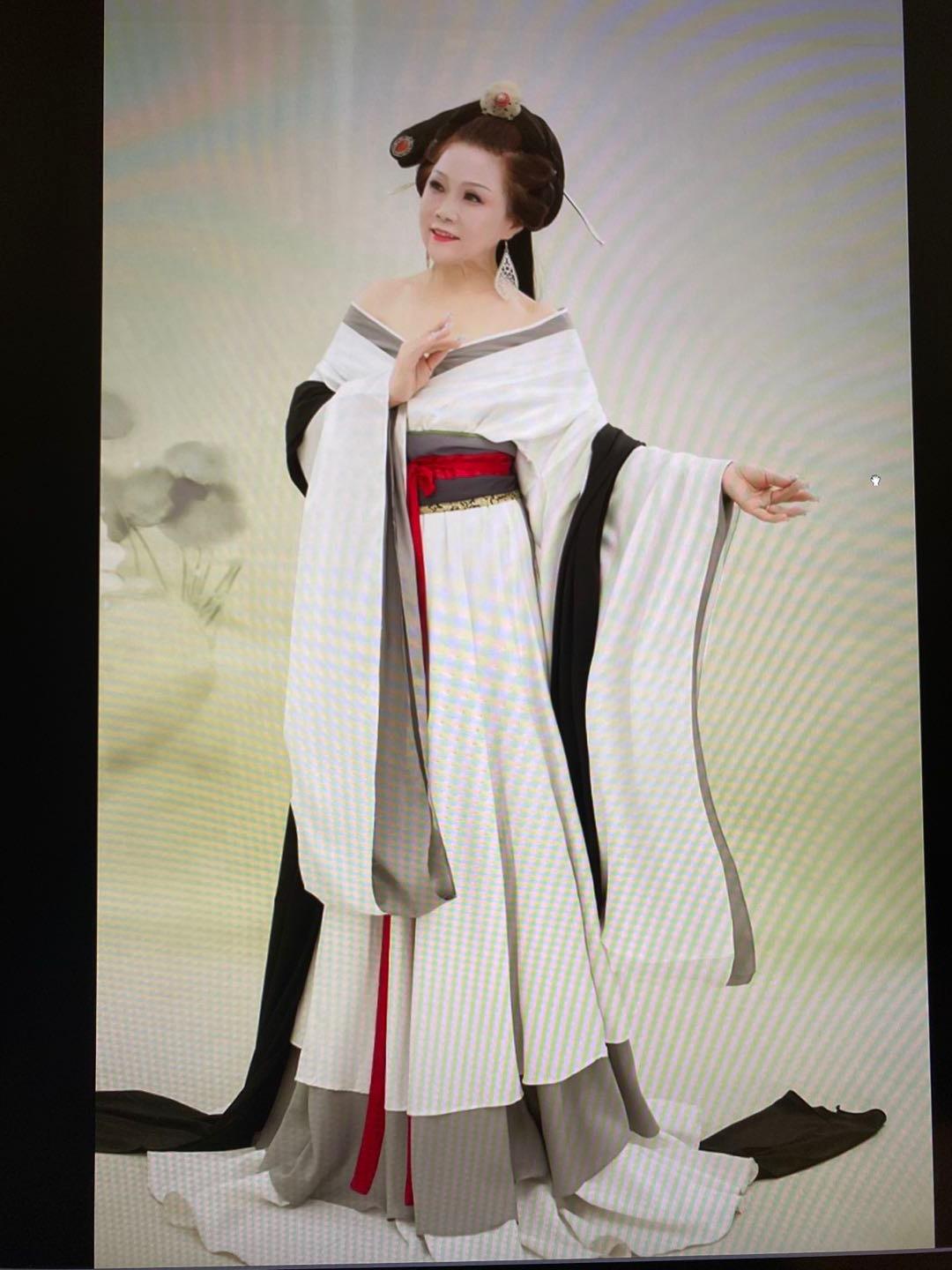
赵一德,龙兴新建人。至元十二年元军伐宋,被俘至大都,为郑留守的家奴,历事郑家三世。至大元年,他对主人郑阿儿思兰及其母亲说:“一德自从离开父母,幸得保全性命依附门下,已经三十多年。故乡万里,还没有回去省视过。虽然思念父母刻骨铭心,从来不敢说。如今父母都老了,如果有什么不幸,我就永远要作天地间不孝的罪人了。”说着伏地而泣,站立不起。阿儿思兰母子都被他感动,准许他回家,为期一年当归。
赵一德回到家里,父、兄已经死了,只有母亲还在,已经八十多岁。他择地把父兄的棺木下葬,想稍多留几日奉侍母亲,又怕得罪使主,于是如期回到大都。阿儿思兰母子感叹说:“他是一个低贱的仆隶,还能这样守信,我们能不成全他的孝心吗!”立即毁掉文契,释放他为良人。

赵一德正准备回家,阿儿思兰以冤罪被处死,家里遭抄籍。奴仆们纷纷逃散。赵一德奋然挺身说:“主家有祸难,我怎么能像陌生人一样!”他留在大都不走,与张锦童一起到中书省诉冤。事得昭雪,抄没的财产都发还了。阿儿思兰母亲对赵一德说:“我们被抄家时,亲戚不相顾,只有你冒险为我们讨回冤屈。疾风知劲草,在你身上看到了。我家产业于丧尽后得复还,都是你出的力。我应当怎样报答你?”
于是分肥田美宅给他。赵一德说:“我虽然是一个低下的人,但绝不是为钱财才这样做的。因为伤心使主无罪被诛,所以留下来报答他。如今老母八十多岁,可以回去侍养她,使主对我的恩赐已够厚了,还要田地房屋做什么?”不受而去。皇庆元年,朝廷旌表他的家门。

一般读书人的故事。
至正八年,从全国17处乡试中选拔的200多名“乡贡进士”,集中在大都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这一届会试的左榜第一名(元朝科举考试分左、右两榜发表,右榜为蒙古人、色目人,左榜为汉人、南人)王宗哲,乡试时即为所在考场第一名,以后殿试又是左榜第一名,所以被人称为“三元”。
王宗哲自己没有想到,他这个元朝十六科中唯一的“三元”,却是因为考官冤屈了另一个叫王伯恂的考生才拿到的。原来判阅会试的试卷时,考官中有一个人对王伯恂的答卷特别满意,说:“此人是天下奇才,应该列为第一名。”但王伯恂是一个“南人”,考官中另有人主张,不宜让南人居第一位,想把他置于第二,而且预先为他留出了第二名的位子。

但主张“宜置第一”的那个考官不肯让步,说:“我们评判考卷,只能以才能文学决定高下,怎么可以分南北籍贯呢?要把他置于第二,我宁可不取录他。”争论了好几天,始终没有一个结果。发榜的日期迫近,主考官只好另选别人来补足第二位的空缺,王伯恂竟然因此而落选。发榜以后,考官们自觉不公正,互相谴责;被取录的士人都感到愧对王伯恂;落榜的人们也纷纷为他慨叹不平。
鲁钝生,其名不详,江南某地人。六岁时喜爱读书,每日记诵万余言;十岁写古诗歌;成年后专攻《春秋》经学。

他的外貌奇古,被人误以为是畏兀儿人。他笑着说:“假若我出身西域种类,只需花一天的时间写卷子,就能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右榜第一人。”只可惜他生在江南,因此以孤独高洁的名声落魄于湖海之间,随心所欲,自暴自弃。浙江的廉访机构曾经辟用他为书史。
鲁钝生深不以为然,手抱文书对来人说:“这不是我的本行,也不是我的志向所在。”乃辞官而去。这时候东维子杨维桢正在浙西等地教书,鲁钝生与他同游天目山。
他酒后必歌诗、写字、画画,直至尽兴。鲁钝生性刚直,容不得别人的过失,经常当面责斥之;人有一善,必也称道不止。晚年著书,自号“金马子”,有《太平万言书》。某年忽然从葛峰往访杨维桢,说:“我要像太史公一样去周游名山大川,如果遇到伟人问我是谁,我懒得自我介绍。请你为我写一篇传记。”杨维桢于是为他写了那篇颇为有名的《鲁钝生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