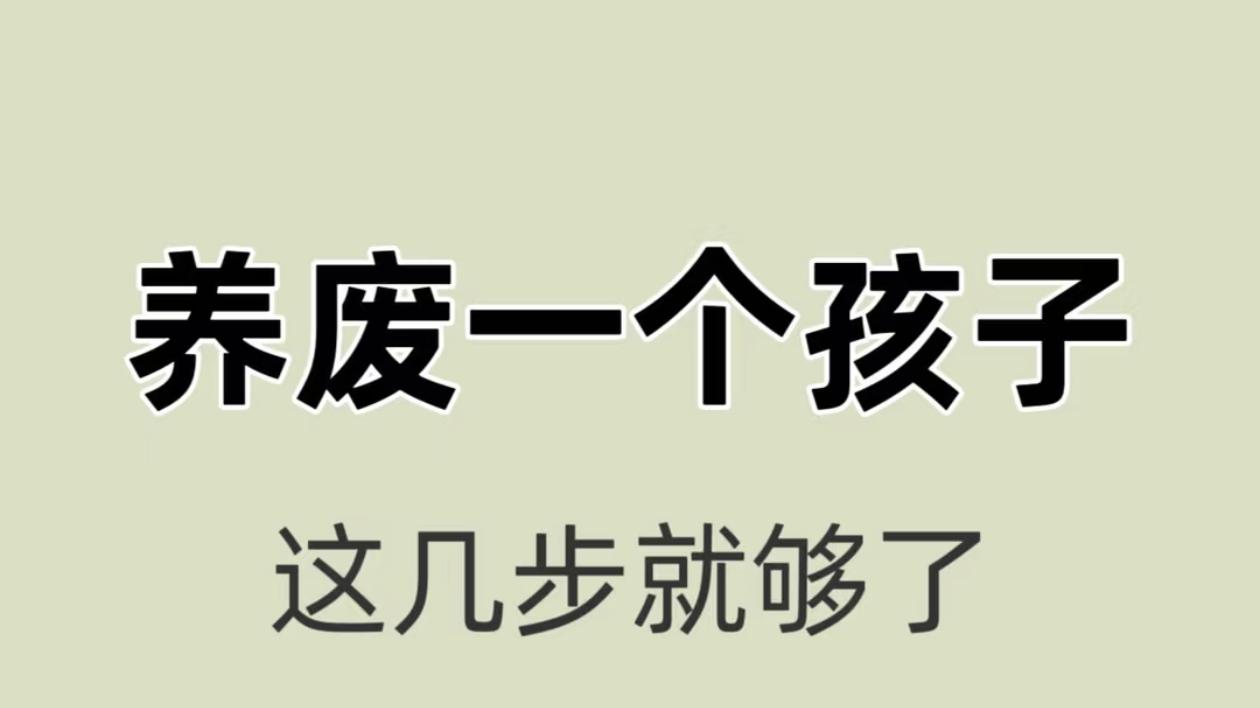你知道吗?80%的校园霸凌升级,都始于家长第一次回应时的失误。
当孩子哭着说“妈妈,他们不跟我玩”时,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是脱口而出的“别理他们”,还是怒气冲冲地要“找老师讨说法”?
三年前,我的女儿在幼儿园被孤立了整整三个月。
她每天睡觉前都会跟我讲述当天的委屈:“王小八又带着小朋友拦着我,不给我玩玩具。”
我当时试图教她“别在乎”,“自己找别人玩”,可发现她的眼神越来越黯淡,连睡前故事都不想听了。

直到某天,我发现她躲在被子里偷偷抹眼泪,我才猛然意识到——我的回应,正在将她推向更深的深渊。
原来,当孩子鼓起勇气诉说被霸凌时,家长们那些“看似正确”的回应,反而可能成为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你太懦弱才会被欺负!” 这句曾被我父亲用来“激励”幼时被排挤的我的一句话,如今又差点被我复制给了我女儿。
那些脱口而出的否定,就像一把钝刀,在孩子的自尊心上反复切割。
我的女儿在听到“别理他们”后,开始认定“被孤立是因为我不够好”,甚至主动避开其他孩子的目光——这正是“忽视式二次霸凌”的典型症状:当孩子的情感需求被漠视,他们会将伤害内化成自我攻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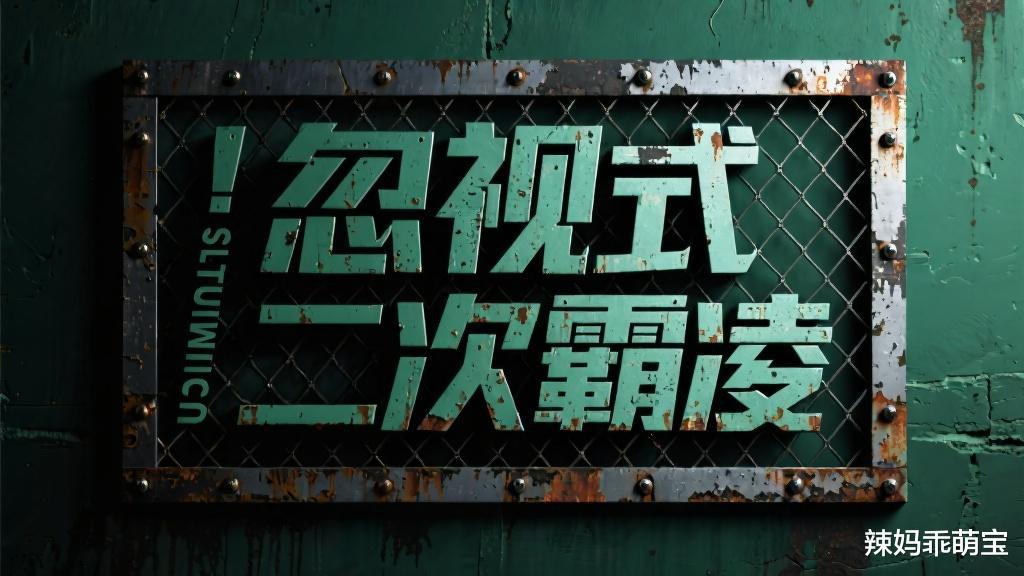
更可怕的是,一些家长以“保护”为名的激烈反应,反而让孩子陷入更大的危机。
曾有一名15岁女孩三年内遭遇三次霸凌,最后一次甚至被人持刀砍伤。她的父亲说,在前两次事件中校方轻描淡写的处理,助长了施暴者的气焰,而家长急于“讨公道”却未建立有效保护机制的行为,让孩子成了霸凌者眼中“可以随意践踏的弱者”。
霸凌的本质是一场场的服从性测试,施暴者永远在试探受害者背后的力量。
在女儿持续被孤立的日子里,我尝试了这三种办法:
给恐惧“重新命名”。当女儿颤抖着说出“王小八”时,我故作轻松地笑:“他头发炸得像只小刺猬吧?”我们给对方起了滑稽的外号,把噩梦般的经历变成可以调侃的故事。这种心理暗示法可以降低创伤记忆的敏感性。

把老师变成“战略盟友”。一开始我向老师反映这个事情的时候,老师的回应都是:我会留意的。然而事情并没有得到控制。
直到我深夜给老师发去近千字消息:先是引用《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责任,再提出“请老师在自由活动时段驻守玩具区”的具体方案,最后动情写道:“作为母亲,我希望您能成为她心中的超人。”第二天,老师主动牵起女儿的手走向玩具区。
高调宣示“妈妈是你的靠山”。我骑着贴满卡通贴纸的炫酷摩托接送女儿,当所有孩子趴在栏杆上惊呼“你妈妈好酷”时,她第一次挺直了腰板。而更多的孩子被我的摩托吸引,都跑过来问我女儿:这是你妈妈吗?我可以坐一坐摩托吗?
接送几次后,我的女儿在班级里的朋友越来越多。
那些“打回去”的怒吼、“别小题大做”的敷衍,甚至“妈妈明天就去学校闹”的冲动,都在无形中向孩子传递着两种致命信息——“你无能”或“世界危险”。
当孩子诉说被欺负时,家长首先要做的是蹲下来,用体温和心跳代替语言。
你家孩子被人欺负时,你是怎么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