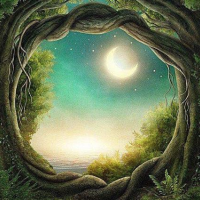成都老城区有栋墙皮剥落的居民楼,楼道里堆满邻居的蜂窝煤。
三楼最靠里的房间,常年飘着菜市场捡来的蔫菜叶味道。
这里住着一对母子,儿子整日对着闪烁的电脑屏幕敲敲打打,母亲总在暮色里拎着塑料袋匆匆出门——她要赶在超市关门前,抢购打折处理的碎肉边角料。
谁也没想到,十年后这个被亲戚议论"不务正业"的年轻人,会带着五十亿票房的哪吒震撼中国动画界。
而蜷缩在破沙发里帮儿子处理素材的母亲,正是成就这场逆袭的"无名英雄"。

时间拨回2002年,华西医科大的实验室里,穿着白大褂的杨宇(导演饺子)正盯着试管发呆。
别人眼中稳妥的医学生,内心却像煮沸的开水般躁动。
他总在解剖图旁画满涂鸦,在病历本上勾勒分镜草图。
当同学们讨论药理时,他满脑子都是如何用三维软件渲染光影。
转折发生在大三某个深夜,室友电脑屏幕上跃动的三维建模,瞬间点燃了这个医学生眼里的光。
在家人的支持下,他花了上万元扛回一台当时堪称奢侈的进口电脑,要知道那时成都的房价也就2000一平米,这样奢侈的行为引起一众同学的艳羡。
从此,医学院的"土豆"(同学给他起的外号)变成了动画世界的探索者。

"那时候他像着了魔。"老同学至今记得,杨宇能为一帧画面连续熬三个通宵,实验室里总见他边调配试剂边念叨"镜头调度"。
当同龄人开始实习时,这个身高一米八的肌肉男却蜗居在十平米小屋,开启了外人眼中的"疯狂赌局"。
真正让人揪心的,是门后那位沉默的母亲。
丈夫肝癌去世留下的债务尚未还清,儿子又放弃医生金饭碗,每月仅靠她千元退休金度日。
菜市场收摊后,她总佝偻着腰翻捡菜叶;超市冷柜前,她反复比较着打折肉的价格标签。
有次邻居看见她冒雨背回半袋发黄的青菜,忍不住劝道:"让孩子找个正经工作吧。"她却笑笑:"我儿眼里有火苗。"
这簇火苗在幽暗的小屋里燃烧了三年,杨宇的电脑里躺着三百多个废弃剧本,键盘缝隙积满泡面碎屑。
为做出满意的特效,他曾连续72小时守着渲染进度条,耳鸣到听不清母亲唤他吃饭。
而那位总被误认为"保洁阿姨"的母亲,竟自学Photoshop帮儿子处理基础素材,布满老茧的手指在鼠标上笨拙地点击。
2008年,16分钟的《打,打个大西瓜》横空出世。

当业内惊叹这部个人动画的精良时,没人知道它诞生于油污斑驳的折叠饭桌。
更无人知晓,首映当晚,母子俩就着捡来的菜叶煮了碗"庆功面"——这是三年来他们第一次舍得放整勺猪油。
命运的转轮自此开始加速,2015年,当彩条屋影业CEO听完杨宇的哪吒构想,当场拍板投资。
可真正的考验才刚开始:剧本推翻66稿,哪吒形象迭代101版,申公豹的变身镜头逼疯三家特效公司。
有制作人员崩溃道:"导演的要求简直变态!"
这种"变态"源自刻在骨子里的执着,杨宇记得某个雪夜,母亲把发热的电脑主机抱在怀里保温,只因屋里暖气管道年久失修。
她总说:"要做就做到最好,别让人看轻了咱。"这份近乎偏执的坚持,最终凝练成银幕上那个烟熏妆、插裤兜的叛逆哪吒。

2019年盛夏,《哪吒之魔童降世》点燃了整个中国。
当票房冲破50亿时,杨宇在庆功宴上突然离席——他跑回老房子,和母亲蹲在当年捡菜叶的楼道里吃了碗泡面。
远处CBD的霓虹照亮母亲的白发,他突然明白:所谓逆天改命,不过是有人甘愿垫在脚下当台阶。
如《哪吒2》早已冲破百亿票房,在全球影史上都快冲进前十了,而导演杨宇也成为中国票房最高的导演,仅两部作品就达到如此高度,不得了。

而在杨宇办公室始终挂着两幅画:一幅是哪吒撕裂天劫的剧照,另一幅是母亲在菜市场弯腰的背影。
前来洽谈的投资人常疑惑后者寓意,他总会摸着画框轻声说:"这才是真正的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