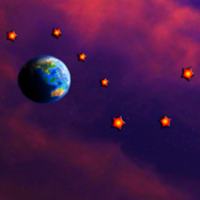文丨李嘉怡
人应当至少有一个梦想,有一个理由去坚强,心若是没有栖息的地方,到哪里都是在流浪。
——三毛

前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巧遇了我的一位旧友,他顶着硕大的背包,行色匆匆。正要目不斜视地从我身边走过,我就在这时叫住了他。他先是一惊,随即呆愣在原地,一言不发。我有心化解这尴尬的氛围,便打趣道:“难不成‘贵人多忘事’,不认得我了?” “没有,就是好久没听见别人叫我名字,一时没反应过来。”也许是意识到这牵强的解释不足以让我信服,他努力从那干枯的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老友重逢,免不了寒暄几句,但无论我说什么,他都只是“嗯嗯”地应着。交谈中,我仔细打量着他,他头发凌乱、一脸疲态,我看着他的双眼,企图从目光中捕捉他的情绪,可那简直不像是一双活人的眼睛,神情呆滞、空无一物,仿佛冻干的鱼眼一般冷硬无神。
诧异之余,我不禁疑惑:一个人到底要麻木到什么地步才会连最基本的情绪波动都失去了?况且在我印象中他一向家境殷实,也并非是需要为了生活而劳苦奔忙的人。片刻之后,他终于开了口:“好累!”“怎么了?”我问。
“上课、兼职、活动、志愿……”他滔滔不绝地向我背诵工作日程表的时候,脸上的神情似乎第一次显得容光焕发了。我忍不住打断他:“这么累,为了什么呢?”他再一次呆愣了,恢复了最初那种茫然的神态,大概他迟滞的大脑已经太久没经过思考,已经不能完全领会我的意思。
“人这辈子总要为了什么而活着吧?”
“当然是为了……” 他的语气很笃定,可话到了嘴边,他又好像意识到什么似的迟疑了,脸上浮出一阵苦笑:“为了得到……为了拥有、拥有……”他忽然改口,声音也提高了一倍,像是发表某种宣言似的正色说:“为了拥有别人都认为对的那种人生。”我还想说些什么,他的闹钟却不合时宜地响起来了,他被这“催命”的铃声吓得惊慌失措,扔下一句“回见”便逃也似的去了。
我望着他的背影,那背影西装革履,似乎很是体面,可我隐隐觉得那体面的躯壳之下,是一个流浪者的灵魂。
这固然是一次太无趣的见面,但他留给了我一个很值得思考的话题:关于拥有。
“拥有”是一个带有明显主观倾向的谓语,其后的中心语往往是正向且积极的,比如拥有幸福、拥有快乐,从没有人说拥有伤心、拥有悲哀。“拥有”不仅是陈述一个事实,更是寄托一种期许。有人说外在的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富足,我却不能将精神层面的需求定义为更“高级”的拥有,人是该拥有一些东西,才能解放心灵中象征自由的那部分空间,以一个健全的“人”的身份发出对生命的叩问。一个人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内心要如何富足起来,我实在想不出。
那么拥有具有哪些属性呢?我的朋友将“得到”换成“拥有”的举动,引起了我的兴趣,他想必是觉得,“得到”存在某种“被施舍性”,太过短暂;而“拥有”听上去似乎比“得到”更趋向于永恒,于是用词汇的替换为自己换取一些可怜的安全感。
可站在历史的角度看,无论“得到”还是“拥有”都具有暂时性,“拥有”的本质是失去,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死亡。而我们对死亡那种天然的恐惧,是因为那一瞬间的到来会让所有“拥有”变为虚无。人们常说,“拥有时不知道珍惜,非要等到失去了才追悔莫及。”我想,这是一个经验,但何必把它当做一个教训来挖苦人呢?生命的两极总是要同相对出现,才能让人刻骨铭心,一无所有的心不会失去,未尝领悟失去的人也不可能懂得拥有。

杨绛先生在97岁高龄时曾写过一本书,名为《走到人生边上》。她说,“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可见,有关拥有的命题,事实上也是关于生命的命题。但为何杨绛先生在面对即将降临的失去时可以十分坦然,而我这位朋友却惶惶不安,不仅不能接受失去,甚至还要逃避失去呢? 因为他的心是无根的,他不知道何为拥有,更不明白为何拥有。
“拥有”应当是个性化的,每个人的所有之物应当带有其所属者独特的气质,它们可以与生俱来,也可以是后天选择的结果。总之,“拥有”是不需“调教”的。但是现代社会,我们习惯性以一套自以为成熟的规则去审判他人,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关于“拥有”的角逐,仿佛不能拥有某些东西就注定失败,正像我那可怜的朋友所说的那样。
这套标准无时无刻不教唆着我们要拥有同等优渥的家庭环境,如果没有,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或者,说的更冠冕堂皇一些,叫做原生家庭带来的不幸;我们要达到相同的学历,找相似的工作,走相仿的人生路。仿佛不幸走错一步,就会成为众矢之的、被千夫所指,人们好像特别喜欢说“这人废了”,这是相当恶毒的一句话,它从根本上否认了一个人全部的人格、尊严、价值,比直接叫人“垃圾”更伤人心。多数人没有机会形成一个赖以生存的独特精神内核,所以理所当然的将自己全部的价值托付给一群无关紧要的陌生人,无形之中认定了要做他人茶余饭后的谈资。
其实,不被他人理解又有什么紧要,从来如此便对吗?司马迁的故事我们都再熟悉不过。以前以为司马迁著成《史记》,实在是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可纵观他的一生,才发觉《史记》竟可以算是他最微不足道的成就了。他有理想、有信念、有追求,即使面对满朝文武的质疑,他也丝毫不惧为李陵发声,即使遭受宫刑依然不忘著史使命。司马迁能在历史上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大人物,不是因为他权倾朝野、高官俸禄,而是因为他一直坚定的做自己。这一点放在当今这个同质化严重的时代,也是相当难能可贵。
除了暂时性、独特性这些客观属性,我们往往会忽略“拥有”的主观因素,这是直接作用于我们幸福感和满足感的关键。常言道,“知足才能常乐。”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痛苦焦虑是因为想要的太多,于是拼命向前追逐,甚至不顾想要的是否是自己应得的,直到被理想与现实的落差伤得体无完肤。可回头看看,会发现我们早在不知不觉间拥有了许多东西,所有人都说要学会“珍惜”,可这个词实在太大、太飘渺,叫人难以把握。我们不妨换种说法:学会欣赏自己所拥有的。
毕淑敏的散文《提醒幸福》里有这样一段话:“人们常常提醒危机、提醒忧患,但很少有人提醒幸福……你不要期许轰轰烈烈的幸福,它通常只会悄悄的喷洒甘霖。”人们常常“身在福中不知福”,而把所承受的苦难无限放大,这又何尝不是对我们所有之物的一种亵渎。一直以为掰玉米的猴子,是因为粗心大意才最终一无所获,后来才发现,其实它的失败,恰恰是由于什么都想要,所以即使小心又小心,谨慎再谨慎,也避免不了“一路走一路丢”的结局,可倘若它不只是看着树上的,而是低下头看看自己怀里的果子,然后心满意足地离开,它应当是全世界最幸运的猴子。“拥有”要靠争取,而想让拥有之物发挥它的全部价值,还需调整自己的心态。
拥有是一种欲望,可不要让你的欲望变得妖魔化。欲望也可以让你很心安,让你明白内心深处总有着美好的期许。看清拥有的本质、选择自己所爱的路,如此,我们便能远离贪婪和彷徨。
阿多尼斯写道,“风没有衣裳,时间没有住所,他们是拥有全世界的两个穷人”。我想,这句话后半段的语序可以做一个调整:它们是穷人,可他们拥有全世界。衣裳、住所对我们而言是必需品,但对风和时间却不然,它们没有的东西恰恰也是他们所不需要的,不会因为少了这些而有所不平。
于是,不被约束的风里装满了四季,不能停留的时间里住满了回忆。人活百年,我们和它们一样都是世间的流浪者,也应当有勇气活出自己期许的样子,试着让自己的心放下来,看清自己真正所求为何,只要心里拥有一个安身之所,即使流浪也不迷茫。

☆ 本文作者简介:李嘉怡,就读于北京语言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从小热爱文学创作,先后在现代教育报、雷锋杂志等报刊发表过文学作品和理论文章。曾获“叶圣陶杯”全国中学生新作文大赛省级三等奖,多篇征文获奖作品被收录结集出版。
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编辑:易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