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被视为现代“龙学”的奠基作,然而相对于《文心雕龙》原著五十篇而言,“黄札”仅有三十一篇,学界对其残缺性深表遗憾,并从多方面尝试解释或进行质疑。不过,现有各种材料及熟悉“黄札”写作的人士都证明:“黄札”确为残缺之作。而且“黄札”的残缺性还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正是黄侃精心选择相关的讲授篇目并为之撰写札记,才使“黄札”一方面在篇目形式上呈现出古典性残缺,另一方面在讲疏内容上凸显出现代性完美,最终黄侃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文心雕龙》的教学任务,而且其授课讲义《文心雕龙札记》也因具有一种独特的残缺美而成为一代学术名著。
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以下简称《札记》)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具有一种残缺美!而这种残缺美又是作者有意为之,即作者受现代文学观念的影响,对古典文论名著《文心雕龙》的讲授内容进行精心选择的结果。因此,《札记》相对于《文心雕龙》全部内容而言所存在的古典性残缺,恰好凸显出其自身所选择内容的现代性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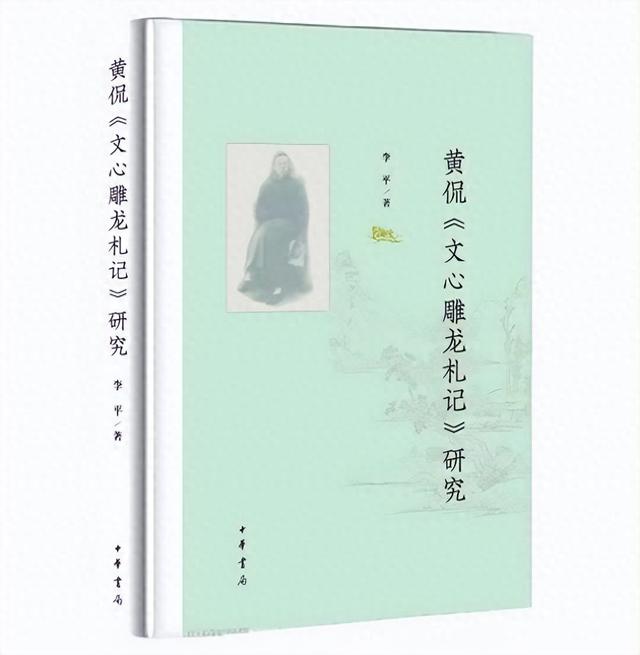
李平:《黄侃〈文心雕龙札记〉研究》书影
一、《文心雕龙札记》为残缺之作《札记》作为现代“龙学”的奠基作,历来备受学界关注。然而,人们在盛赞《札记》的学术价值和重要意义的同时,也对其篇目的残缺性表示了极大的遗憾!《文心雕龙》体大虑周,结构完整,包括“文之枢纽”(总论,五篇)、“论文叙笔”(文体论,二十篇)、“剖情析采”(创作论,二十四篇)和“长怀序志”(绪论,一篇),分上下篇、四个部分;全书依经立义,据《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建构体系,结构上“跗萼相衔,首尾一体”。末篇《序志》为“体”,其余总论、文体论和创作论四十九篇为“用”,所谓“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展现出体用结合的完美性。
而黄侃在北京大学讲授《文心雕龙》,所撰授课讲义《札记》,总共只有三十一篇,即总论五篇,文体论六篇(缺十四篇),创作论二十篇(含《序志》,缺《时序》以下五篇)。1927年,黄侃“手自编校”的《札记》,即《神思》以下的创作论十九篇,加上《序志》一篇,附录骆鸿凯撰《物色》札记一篇,合计二十一篇,由北京文化学社正式出版。1935年黄侃逝世后,前南京中央大学所办《文艺丛刊》,又将《原道》以下十一篇讲义(即总论和文体论部分)发表。1947年四川大学中文系曾将上述三十一篇合印一册,在校内交流,绝少外传。1962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将三十一篇合为一集,由黄念田重加勘校并断句读正式出版。至此,《札记》全璧方流行于世。
对于黄侃《札记》的残缺性,学界有不同的猜想。首先是1914—1916年在北大课堂听黄侃讲授《文心雕龙》的范文澜,他说“《文心》五十篇,先生授我者仅半,殆反三之微意也”。这只是弟子的一种美好设想,认为老师没有完整地传授《文心雕龙》,是要让弟子们举一反三。与范文澜一起听黄侃讲授《文心雕龙》的还有金毓黻,他说“余受业于先生之门凡二年,时为民国三年秋至五年夏”,并认为“黄先生《札记》只缺末四篇”。这一说法显然有误。金氏大学毕业离开京城后,回故乡东北任中学教师多年,后又投身仕途长期从政,虽然保留着书生本色和学者素守,但毕竟置身学界之外,故对“黄札”和“范注”的相关著述情况难免暌隔。就其师黄侃和同门范文澜而言,其于《札记》具体篇目存佚情况,《史传》篇“黄札”训释问题等,所述皆与事实不符;而对范氏《文心雕龙讲疏》及新的《文心雕龙注》之间修订沿革关系也不甚了了,故谓“《讲疏》又称《注》”,其实《讲疏》与新《注》实为范氏两部著作。有鉴于此,《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1辑重新刊发金氏遗稿《〈文心雕龙·史传〉篇疏证》时,将篇首原叙中“然《札记》于《史传》篇训释甚简,范君取之,更不复别白”删去,因为《札记》根本就没有《史传》篇。近年还有人猜测,黄侃因弟子范文澜在《讲疏》中大量袭用《札记》,导致其“不爽”,甚至恼怒,以致成了“心病”,最终“悄然中断了《文心雕龙札记》的写作,且终其一生不再讲授《文心雕龙》”。此乃故作惊人之语,实则不明就里。
不过,学界还是时常有人怀疑黄侃《札记》并非残缺,可能尚有存佚而未经刊布者,以致黄念田不得不在中华书局版《札记》后记中,特别对“黄札”的存佚情况作了详细说明:“或疑《文心雕龙》全书为五十篇,而《札记》篇第止三十有一,意先君当日所撰,或有逸篇未经刊布者。惟文化学社所刊之二十篇,为先君手自编校,《时序》至《程器》五篇如原有《札记》成稿,当不应删去。且骆君绍宾所补《物色》篇,《札记》即附刊二十篇之后,此可证知先君原未撰此五篇。至《祝盟》讫《奏启》十四篇是否撰有《札记》,尚疑莫能明。顷询之刘君博平,刘君固肄业北大时亲聆先君之讲授者,亦谓先君授《文心》时,原未逐篇撰写《札记》,且检视所藏北大讲章,讫无《祝盟》以下十四篇及《时序》下五篇。于是知武昌高等师范所印讲章全据北大原本,并未有所去取,而三十一篇实为先君原帙,固非别有逸篇未经刊布也。”尽管如此,仍然有人认为黄侃在法定开设的课程中,必定将《文心雕龙》全书讲授完毕,理由是其师章太炎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仅用五次就把五十篇讲完了,且黄侃将其“龙学”文章和著作称为“札记”,是效仿其师章太炎。这是一种想当然的说法,太炎师走马观花地五次讲完五十篇,与黄侃是否将五十篇讲完没有必然关系。再者,太炎师讲授《文心雕龙》的记录稿本封面上的“文心雕龙札记”为听课人之一钱玄同所书,钱氏所用“札记”的含义与黄侃文章和著作名称中的“札记”意思完全不同,前者是指记录笔记、整理笔记,后者则指考订类的学术笔记。
二、《文心雕龙札记》残缺缘由当我们对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并撰写《札记》作为授课讲义的具体情况仔细研究之后,就会发现《札记》的残缺性乃黄侃有意为之,就是说他是特别有选择地讲授了三十一篇内容,并为讲授篇目撰写了授课讲义,而其“手自编校”的由文化学社出版的《札记》,则又是他认为最有价值的二十篇讲义。那么,黄侃为什么只选择《文心雕龙》三十一篇作为授课内容,又为什么只精选二十篇授课讲义正式出版呢?
黄侃侄儿黄焯在《季刚先生生平及其著述》一文中说:“故自甲寅秋,即受北京大学教授之聘(时年二十八岁),讲授词章学及中国文学史,讲义有《文心雕龙札记》、《诗品疏》、《咏怀诗补注》等。”可见,黄侃进入北大初期是在“词章学”的名目下讲授《文心雕龙》的,但他讲授的内容既不是《文心雕龙》全书,也不是现存《札记》的三十一篇,而是《神思》以下的二十篇,即舍人之书的创作论部分。1917年后,黄侃又在北大讲授“中国文学概论”课程,这是从日本进入中国的一门综合性、概括性很强的理论课,主要讲授文学基本概念和知识,当时在这门新课的名称后有一括号说明:“文学概论(略如《文心雕龙》《文史通义》等类)”。这正好提醒黄侃可以顶着“文学概论”的名义来讲《文心雕龙》,只不过为了照顾这门新课的性质和特点,黄侃此次讲授的具体内容与“词章学”课堂上讲的有所不同,这次讲授的是“文之枢纽”五篇,因为这些篇目属于《文心雕龙》的总纲,阐述了贯穿全书的基本理论和建立体系的指导思想,而这正好契合“文学概论”新课的性质和特点。当然,无论是创作论部分还是总论部分的讲授,都要辅以一些例证材料,因此黄侃又选择了文体论部分的六篇。
黄侃根据课程的性质与特点,从《文心雕龙》中选择了三十一篇作为讲授内容,而他的文学观和他对《文心雕龙》的认识,又决定了他为什么选择这些内容来讲授。首先,就课时而言,当时的“词章学”贯穿本科三年,“文学概论”课时至少也有一年,黄侃完全可以把《文心雕龙》全书讲完;即使在北大的五年没能写完五十篇札记,后来黄侃在武昌高等师范、南京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都曾继续讲授《文心雕龙》,若想续写缺篇以成完璧,也是完全可能的。然而,在他看来,彦和之书虽然是古代文论的经典,但是其中有些内容并不适合时代需求,所以必须作出选择,尽量讲授那些富有现代精神,贴近当下文学思潮的内容。因此,《札记》的残缺是有意而为。其次,就“词章学”课堂讲授的创作论部分而言,黄侃认为《神思》至《总术》及《物色》篇乃“析论为文之术”,即讨论“为文之用心”的创作方法,系“剖情析采”的精华,属于文学的内部研究;而《时序》至《程器》五篇,除《物色》外,为“综论循省前文之方”,即概述考察前修之文章的鉴别途径,基本是文学的外部研究,且其弟子骆鸿凯已撰有《物色》篇札记,故未予选讲,亦未撰写札记。再次,“文学概论”课堂选择总论五篇是因为“文之枢纽”是一个整体:“道”为本体,故原之;“圣”为主体,故征之;“经”为正体,故宗之;“纬”为异体,故正之;“骚”为变体,故辨之。其中,以《宗经》为核心,可以上溯中国文学之本源,下考中国文学之流变。最后,即使作为例证材料的文体论部分,黄侃亦尽可能选择纯文学的有韵之文,如《明诗》《乐府》《诠赋》《颂赞》,且总论五篇和文体论有韵之文的四篇讲义,1925—1926年都曾在《华国月刊》发表。而无韵之笔仅选了《议对》《书记》两篇以备参证,因《札记·原道》在分析泛文学观时,曾提到“《文心·书记》篇,‘杂文多品,悉可入录’”;《札记·总术》在分析文笔论时,也曾提到“《书记》篇末曰:‘笔剳杂名,古今多品’”“文藻条流,托在笔札(《书记》篇赞)”;且只有这两篇札记未在杂志单独发表,以表明其仅为教学参证材料。
至于其“手自编校”的文化学社版《札记》为何只选择《神思》以下的二十篇讲义,也与黄侃富有现代性的文学观分不开。《札记·原道》论“文辞封略”说:“彦和泛论文章,而《神思》篇已下之文,乃专有所属,非泛为著之竹帛者而言,亦不能遍通于经传诸子。然则拓其疆宇,则文无所不包,揆其本原,则文实有专美。”可见,黄侃是秉持纯文学观来选择他“手自编校”的《札记》内容,即《神思》以下的“专有所属”的“专美”之文,也就是他在“词章学”课堂讲授的内容。他认为这部分内容乃《文心雕龙》精义所在,故花大气力疏通讲解,所谓“下篇以下,选辞简练而含理闳深,若非反复疏通,广为引喻,诚恐精义等于常理,长义屈于短词;故不避骈枝,为之销解,如有献替,必细加思虑,不敢以瓶蠡之见,轻量古贤也”。而总论和文体论部分的十一篇札记,因非“专有所属”的“专美”之文,亦非精心结撰,故弃之不取。
三、《文心雕龙札记》的残缺美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艺思潮的涌入,中国学者在回应时代关切之际,开始把目光投向本土的固有资源。受太炎师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启发,黄侃在受聘担任北大教授,讲授“词章学”和“文学概论”课程时,也选择了《文心雕龙》作为讲授内容。黄侃与太炎师不同,或者说超越其师之处,是并非五十篇全讲,而是精选了三十一篇讲授内容,并撰写了《札记》作为授课讲义。这就使得其书相对于《文心雕龙》原典来说,存在一定的残缺性,而这种残缺性又是由于作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参照现代文学观念,对讲授篇目精心选择导致的。故其篇目结构上的古典性残缺,反倒折射出思想内容上的现代性完美,因此可以说《札记》具有一种现代性“残缺美”。对此,学界多有忽略,管见所及,只有韩经太在这方面略有所悟。他在分析黄侃《札记》“依傍旧文,聊资启发”的特点时曾说:“黄侃在讲说《文心雕龙》一书时,对原书章节是有选择地进行讲疏,这就与完整全面的专书研究不尽相同。……现在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黄侃当年为什么要有所取舍呢?关于这个问题,似乎没有怎么引起人们的注意。殊不知,在此取舍之间,恰恰体现着黄侃的学术理路。按今见黄侃《札记》31篇篇目为:《原道》《征圣》《宗经》《正纬》《辨骚》《明诗》《乐府》《诠赋》《颂赞》《议对》《书记》《神思》《体性》《风骨》《通变》《定势》《情采》《镕裁》《声律》《章句》《丽辞》《比兴》《夸饰》《事类》《练字》《隐秀》《指瑕》《养气》《附会》《总术》《序志》。与刘勰原作相比照就可以发现,除关乎‘文之枢纽’和创作、批评者,黄侃所以舍去不讲《祝盟》以下14篇,显然出于‘文学’性的考虑,与这里所选讲的诗、骚、赋、颂、乐府、书记、议对相比,祝盟等文体明显不属于文学的范围。于是,问题的实质已很清楚,黄侃讲的是文学的《文心》,而不再是文章的《文心》了。这当然是一个时代的进步。”
《札记》的现代性“残缺美”,首先表现在对太炎师泛文学观的超越上。章太炎在其《文心雕龙》开讲前曾与弟子讨论文学定义,他从泛文学观的角度认为:“《文心雕龙》于凡有字者,皆谓之文,故经、传、子、史、诗、赋、歌、谣,以致谐、隐,皆称谓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彦和之见高出于他人者也。”故其对《文心雕龙》五十篇全讲。黄侃虽然认为其师的泛文学观和阮元的骈文观各有所宜,并调和两者观点,提出了张弛有度的“文辞封略”说,即推而广之,则文无所不包,不限于文饰、句读与否;缩小而言,有句读者皆为文,不论文饰与否;至于文章,则尚韵语偶词、修饰润色、敷文摛采;但从《札记》的实际内容来看,黄侃明显站在文选派立场,倾向于阮元和刘师培的骈文观,故把目光集中于“剖情析采”的“专美”之文上,且特别重视下篇“析论为文之术”的篇目,只选择这些篇目的札记单列出书。其“手自编校”的《札记》,宁愿附录弟子骆鸿凯的《物色》篇札记,也不将自己撰写的总论和文体论札记编入,可见其对“为文之术”的重视几乎到了固执的地步,从而使得其书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其次,《札记》的现代性“残缺美”还表现在与桐城派的抗争上。民国前后,北大教坛一直被桐城派所把持。桐城派宗奉儒家道统,秉承程朱理学,以唐宋八大家古文为楷式,标榜“桐城义法”。黄侃与民国时桐城派重镇姚永朴同于1914年进入北大,黄氏讲授“词章学”,姚氏讲授“文学研究法”。姚氏讲义《文学研究法》“发凡起例,仿之《文心雕龙》”,尤其对《文心雕龙》文体论津津乐道,在讲义中不厌其烦地引用;黄侃则与之唱对台戏,在“词章学”课堂只讲《文心雕龙》创作论,对姚氏看中的《章表》《奏启》《诏策》《诔碑》之类过时的古文文体,一概弃之不顾。同时,黄侃还在《札记》中不遗余力地揭批桐城派,或以汉学家身份斥其不学,或藉骈文家名义责其无文,对“阳刚阴柔”“起承转合”之类的“桐城义法”进行了无情的驳斥,由此彰显出其书强烈的战斗性。太炎师曾回忆:“余弟子黄季刚初亦以阮说为是,在北京时,与桐城姚仲实争,姚自倚老耄,不肯置辩。”不过,在黄侃等章门弟子的大举进攻下,姚永朴最终还是招架不住,不得不于1918年辞去北大教职。有意思的是,后来黄侃在南京中央大学也曾开设“文学研究法”一课,并“用《文心雕龙》作课本”。
当然,《札记》的现代性“残缺美”更集中地体现在对西方纯文学观点的回应上。受西方文学独立思潮的影响,近代中国文坛特重文学的偶丽韵律和美感情思,提倡将“纯文学”与“杂文学”区别开来。黄侃治学本以小学著称,而1914年受聘担任北大教授,选择在课堂上宣讲《文心雕龙》大义,在课余时间撰写《札记》讲义,将《文心雕龙》作为本土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以此应对外来文化的强势渗透,顺应时代文学思潮的发展趋势。为了更好地应对西方纯文学观点,找到与之相侔的本土思想资源,黄侃推崇文选派的文学观,以“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瀚藻”为标准,从文术、辞采、偶丽、情思的角度,选择《文心雕龙》的“专美”之文进行讲授,并出版“手自编校”的《札记》专书,从而走出其师倡导的泛文学、杂文学传统,直接以《文心雕龙》的“专美”之文和“为文之术”对接西方的纯文学观念,由此奠定了《札记》一书突出的现代性。
四、《文心雕龙札记》成功的原因黄侃在北大课堂讲授《文心雕龙》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与黄侃同时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不仅有其同门朱蓬仙,还有其对手姚永朴,甚至黄侃执贽行弟子礼的刘师培也专门讲授过《文心雕龙》。然而,他们或被学生赶下讲台,或被黄侃斗得落荒而逃,就连刘师培也不过默默无闻,若不是罗常培笔述其《文心雕龙》讲录二种,后人则很少知之。那么,为何唯独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能大获全胜呢?仔细推究,这与黄侃的三次选择密切相关。
第一次是受太炎师在日本讲授《文心雕龙》的影响,黄侃亦选择《文心雕龙》作为其在北大任教的讲授对象,使传统诗文评的龙头之作进入现代国立大学的课堂。这一选择意义重大,因为黄侃不是偶然、随意地选择了《文心雕龙》作为讲授对象,而是有着自觉的意识和充分的理由。他在《札记·题辞及略例》中说:“论文之书,鲜有专籍。自桓谭《新论》、王充《论衡》,杂论篇章。继此以降,作者间出,然文或湮阙,有如《流别》、《翰林》之类;语或简括,有如《典论》、《文赋》之侪。其敷陈详核,征证丰多,枝叶扶疏,原流粲然者,惟刘氏《文心》一书耳。”
与黄侃同时代的陈柱,对《文心雕龙》一书的价值和意义,也与黄侃有相同的看法,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昔周秦诸子,生当道术之裂,各以其术鸣于天下,莫不著书以自见。或出自一人之手,或出乎其徒之展转传述。其言虽有纯驳之不同,然莫不有其专家之学,故世谓之诸子。《汉书·艺文志》叙九流,莫不曰某家者流,其识卓矣。自汉以后,继踵而作者尤夥,然大抵皆周秦诸子之绪余,虽各有可观,而方诸古昔,瞠乎后矣。唯刘彦和《文心雕龙》之作,独为专家之学,足补周秦诸子之所不逮。虽其时挚虞《流别》,钟嵘《诗品》之类,亦名专书,然或则已阙而不全,或则甚略而弗备。至于魏文《典论》,士衡《文赋》,以及陈思之书,休文之论,尤为具体而微者矣。其传于今日而小大毕具,有条弗紊,足以卓然并列于诸子者,则刘氏此书而已。
陈柱自叙其治舍人之书久矣,且“时有省悟”,唯“无暇记录”;1924年为锡山国学馆诸生讲授《文心雕龙》,次年又在上海大夏大学为诸生讲论是书。“随笔而记,不觉裒然成册。兹为述其略例如下。一曰补……二曰订……三曰校……四曰原……五曰评……六曰参考……”,遗憾的是,陈氏《文心雕龙增注》今已失传,唯《叙例》尚存,原载《国学周刊》1925年第87期。《叙例》胜义纷披,且多与黄侃暗合,上引之外,又如谓彦和之书,“其立论也,一则曰自然,再则曰自然。夫曰雕则非自然矣,曰自然则非雕矣。曰雕曰自然,得毋近于矛盾之说邪?呜呼!知乎此,则可以语文矣。”这种辩证的酌中之论,与黄侃何其相似乃尔!惜无以窥其详矣。
周秦诸子时代,专家之学盛行,专门之书迭出,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专家之学渐为正统经学所取代,专门之书亦遂被治经之术所遮蔽,博学通儒成为士子的奋斗理想。及至近代,受西方学术思潮的影响,诸子学重新抬头,学者务为专家之学、专门之书。诚如钱穆所说:“中国重和合,西方重分别。民国以来,中国学术界分门别类,务为专家,与中国传统通人通儒之学大相违异。”于是,《文心雕龙》开始进入学人的视野,成为上接周秦诸子,下启近代新学,外应西学思潮的中华宝典。这就是黄侃选择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时代背景和根本原因。因此,他不是像其他学者那样,或毫无准备地就在课堂讲授《文心雕龙》,以致被学生轰下台,如朱蓬仙;或只是零星地讲授一二篇,因此难以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如刘师培;或大量引录过时的文体论,只能落得食古不化的结果,如姚永朴。相反,黄侃顺应现代学术思潮,沿着专家之学、专门之书的治学路径,有选择、有准备地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故太炎师谓其“研精彦和《文心》,施之实事”。
第二次是选择《文心雕龙》中的三十一篇,作为现代《大学规程》新列的专业课程“词章学”和从日本引进的舶来课程“文学概论”的具体讲授内容,积极参与并配合北大文科的教学课程体系改革,并在讲授中突出“剖情析采”的创作论,尝试“文辞封略”的义界探讨,提升有韵之文的文学地位。虽然“词章学”是现代《大学规程》中新列的专业课程,但是黄侃却觉得这门课程的讲义编写起来“不甚费力”,因为他决定在这门课上主要讲授《文心雕龙》创作论,而文章作法正是其强项,太炎师曾谓“季刚尤善音韵文辞”。“文学概论”是当时《文科改订课程会议议决案》规定在1918年开始执行的文学门通科课程,黄侃只是在原课程名称前加上“中国”二字,就在这门新课上讲起了《文心雕龙》总论,并综合太炎师的泛文学观和阮元、刘师培的骈文观,提出了闳通不党的“文辞封略”说,以致所授课程大获全胜。当时的听课人杨亮功回忆说:“当时中文系教授有刘申叔(师培)先生讲授中古文学史,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黄晦闻(节)先生教诗,吴瞿安(梅)先生教词曲,皆是一时之选。”“黄季刚先生教文学概论以《文心雕龙》为教本,著有《文心雕龙札记》。”与杨氏同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又同年毕业的萧劳,也对黄侃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印象深刻。他在《六十年前我在北大的几点回忆》一文说:“黄侃先生当时在北大教授《文心雕龙》,他对古典文学有相当造诣。”
第三次是选择“析论为文之术”的二十篇讲义作为专书出版,使其“手自编校”的《札记》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强烈的战斗性和突出的现代性。黄侃对著述要求严苛,一生不轻易出书。其师章太炎说:“(黄侃)始从余问,后自为家法,然不肯轻著书。余数趣之,曰:‘人轻著书,妄也。子重著书,吝也。妄不智,吝不仁。’答曰:‘年五十当著纸笔矣。’今正五十,而遽以中酒死,独《三礼通论》声类目已写定,他皆凌乱,不及第次,岂天不欲存其学耶!”黄氏所撰《札记》讲义,虽然陆续在报刊有所发表,但是他本人仍不急于出书。不过,及门弟子则坚决请求其将《札记》结集出版。门人兼女婿潘重规在其所编《文心雕龙札记·跋》中说:“先师平生不轻著书,门人坚请刊布,惟取《神思》以次二十篇畀之。”一方面,黄氏门人因为深知其师“平生不轻著书”,在刊布著述方面极为“吝啬”,故而“坚请刊布”,恳请其将零星刊发以及箧中所藏有关《文心雕龙》的讲章裒为一集,正式出版,以飨天下。另一方面,黄侃所谓“年五十当著纸笔”也不能一概而论,在“门人坚请刊布”的情况下,他也会适当顾及弟子所请。1927年7月,他将“手自编校”的《神思》以下二十篇交文化学社印行,名曰《文心雕龙札记》。但没有将《华国月刊》已发和未发的上篇部分《札记》收入书中,这既反映了他严苛的著述态度,也表明了他合乎时代潮流的文学观。黄侃正是通过他“手自编校”的文化学社版《文心雕龙札记》,向世人宣告他所讲授的是文学的《文心雕龙》,而不是文章的《文心雕龙》。
从选择《文心雕龙》这部书作为教学对象,到选择其中的三十一篇作为教学内容,再到选择二十篇讲义作为专书出版,这一递减过程使得其“手自编校”的《札记》,与古典原著《文心雕龙》相较残缺性越来越大。然而,从回应时代关切,正视西方文艺思潮的挑战,适应现代文学观念的发展来说,这种古典性残缺正是《札记》现代性完美的体现,而且选择越精粹,残缺性越厉害,则现代性越鲜明!就此而言,黄侃“手自编校”的《札记》要比后来整理出版的三十一篇全璧,时代性更强,现代性也更突出,当然价值也更大。
来源:《学术界》2025年第1期。本转载仅供学术交流之用,版权归原作者所有,若有侵权,敬请联系,万分感谢!
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