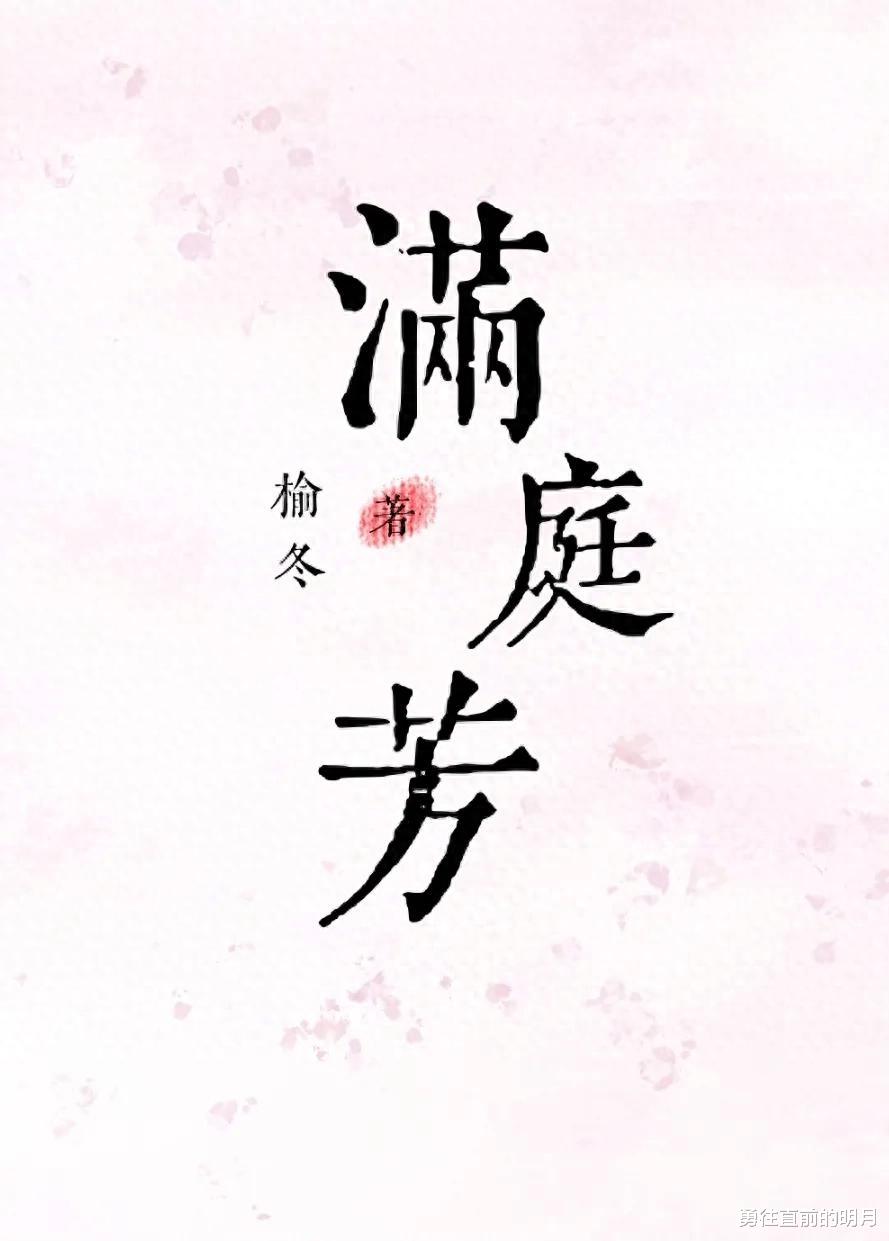
简介:
林稹一睁眼,穿成了乡野破落户。
早起打猪草,夜里纺桑麻。
才了蚕桑又插田,一天到晚不得闲。
她勤勤恳恳的劳作,兢兢业业的昧钱。
这一日,继母告诉她,说要上京投亲。
好不容易到了京城,这才知道,大宅门里是非多。
光同辈姐妹就有五个,个个婚嫁都不容易。
其中,尤以她的婚事,最折腾人。
韩旷在上京路上偶遇了一位小娘子,颇感有趣。
回京后,又得知自己还有个未婚妻。
他想,我总不能娶一个不认识的人罢。
于是,他认认真真把婚事给退了。
精彩节选:
三月,清明时节,细雨纷纷。
绵密的雨丝打在人身上,惹来好一通抱怨。
“天天下雨!天天下雨!比黄梅时节还烦人!”
娇姐儿踢踢踏踏,不情不愿地取了个笸篓,把院里院外几棵桑树的叶子捡起来。
三月桑叶刚长成,翠滴滴的挂在枝头,昨夜疾风骤雨,到底还是掉了些新叶。
农户俭省,落下的嫩桑叶稍晒一晒就能喂蚕,实在不行就拿去喂给里正家养的猪,到底也是个人情。
牛毛细雨密不透风,穿了蓑衣也不管用,娇姐儿越捡越烦,撅着嘴呶呶不休地抱怨——
一会儿说“要吃姜汤祛寒”,一会儿又说“母亲偏心,凭什么珍娘不用捡”,说着说着,还若有若无的瞪了林稹几眼。
一旁的林稹搁下手里的线锭,暗自苦笑,心道她天蒙蒙亮就起来洗衣、做饭、劈柴火、打猪草……你不过是睡到太阳高起,再穿上蓑衣院里院外捡捡桑叶罢了,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更别提要不了一会儿,这蓑衣就该她来穿了。
果不其然。
“好了,娇姐儿,快把蓑衣给珍娘,还得下田看秧水去呢。”
钱氏从东稍间走出来,已经换了套破旧的葛布短打,又套好了蓑衣斗笠。
一听不用再捡桑叶,娇姐儿喜上眉梢,抱起笸篓就进了屋。
即使穿了蓑衣,娇姐儿面上、头发上还是沾了雨水,一双草鞋底都是烂泥,叫钱氏看了,不由得心疼起来。
要不是怕院子外的桑叶被别人捡了去,也不至于叫女儿冒雨去捡。
“灶头有姜汤,快去喝一碗。”钱氏先给娇姐儿擦了擦雨水,又盯着她灌了两大碗姜汤。
见娇姐儿脸色暖起来了,钱氏这才转头对着林稹客气道:“珍娘要是冷了,也去喝一碗祛祛寒气。”
林稹点点头,客气地道了谢,接过娇姐儿递来的蓑衣,转头去东稍间的灶台,灌了满满一大碗姜汤。
湖州多山林,当地最不缺的就是柴和炭。相较于感染风寒后的花销,做饭时耗些柴火煮锅姜汤祛寒,反倒俭省。
一碗姜汤入肚,从喉咙到腹部,五脏六腑都热辣辣的,林稹微微冒汗,这才跟着钱氏一起出了门。
三月里,田间地头稻苗青青,陇上散落着七八个劳作的农人。
又有几个梳着包髻、合围掩裙的妇人,袖子卷的老高,露出粗壮的胳膊,正踩着草鞋冒雨回来。
“阿钱,这是干什么去?”热心的农妇招呼道。
钱氏细声细气的应了一声,又客气道:“陈娘子好”,语罢,还解释:“地里雨水多,怕淹了苗,得看看去。”
陈娘子看了眼钱氏,提高了声量,生怕别人听不见似的:“阿钱,这么大的雨,出门怎么只带珍娘,不带你家娇姐儿?”
话一出口,周围几个妇人互相挤眉弄眼,又都窸窸窣窣地笑起来。
钱氏被笑得面皮涨红,这是明里暗里指她偏心呢。
她正要回嘴,身后的林稹反倒先开了口:“是我憋在家里许久了,娘架不住我歪缠,这才应了我,叫我跟着她出门透透气。”
人家苦主都这么说了,一众妇人也不好再说什么。
钱氏松了一口气,添补了一句:“珍娘已经十六了,要不了多久就得议亲,农桑针黹,洗衣做饭,样样都得学起来。”
话说得倒是好听。
陈娘子从鼻腔里飘出一个哼来,也不知道在哼谁。
林稹眼看着钱氏的脸皮又涨红起来,忍不住劝道:“娘,我们走吧,地里还有活儿呢。”
再吵下去,被人看笑话也就算了,地里的活儿干不完,明天还得冒雨继续干!
钱氏得了个台阶,也不再多话,带着林稹匆匆往前走。
只是走得远了,还能听见后头窸窸窣窣的议论声,什么“珍娘也是个傻的”,“到底不是亲生的”,时不时还伴着几句劝和,“算了算了”、“后娘也难做啊”……
林稹全当自己没听见。
那不然呢?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大病初愈,既没生计,手头又没积蓄,惹恼了钱氏,她吃什么?住哪里?
两人冒雨走了半里,终于到了自家的地头。
江南人多地少,田地多数狭窄散乱,除非是大户人家,否则十几亩地鲜少有连在一起的,多半是这里半亩,那里三分。
林家的田也不例外。
林稹跟着钱氏,冒雨去了四五处地方。
头顶的雨水又斜又密地打在人脸上,双脚插在田陇泥巴里看水位,水少了就得弯腰挖开泥巴,把沟沟壑壑里积存的雨水汇集起来,多了又怕泡死秧苗,得把水引走。
仅仅三分田地,林稹就干了快半个时辰。
冰冷的雨水,冻僵的双脚,土坷垃划破手掌,长时间的弯腰导致腰背肌肉抽搐……
捡桑叶算什么,这才叫苦呢。
更苦的还在后头。
两人匆匆巡看完几亩薄田,刚回家,气儿还没喘匀,钱氏连蓑衣都来不及脱,取了两片细细的竹板递过去。
“一二月那会儿刚刮过头蟥,按理二茬蟥要在清明前刮的,可前些日子你生了病,家里忙的厉害,来不及刮。本想着忙完了就好,偏又撞上清明连下三四日的雨。如今实在拖不下去了。”
冒雨都得刮。否则再拖下去,桑蟥病一起,地里一千多棵桑树都得完蛋。
被雨泡了大半日,即使灌了姜汤都不管用,林稹脸色发白,整个人冷的厉害。
她本想拒绝,可看着钱氏被冻的发白的脸色,竟也不好开口。无论钱氏怎么偏心,苦活累活儿她自己也干了。
更要命的是,要是桑树真完蛋了,家里养蚕的收入没了,日子只会更窘迫。
那时候,林稹会不会被嫁出去换聘礼或者被卖掉……她不知道,也不敢赌。
“好。”林稹接过竹片。
见她答应了,钱氏匆匆往院外走去,院子外头还有七八棵桑树要刮呢。
“娘——”林稹喊住她,在钱氏疑惑的目光中开口道:“我病刚好,又淋了雨,实在冷的厉害,可否和娇姐儿轮换着来?”
钱氏脚步一顿,细声细气道:“刮蟥是个细致活儿,但凡有一粒蟥卵没刮干净,整片桑林都废了。你也知道,娇姐儿她心糙,又粗手粗脚的,我实在不放心。”
大概是怕林稹心有不平,钱氏又补了一句:“你放心,娇姐儿也不闲着,我叫她上灶头忙活晚饭去。”
话已至此,林稹只能再度披好蓑衣,戴上斗笠,匆匆出了门。
一亩地种了数百棵桑树,望眼望去,密密匝匝。
所幸家里种的桑树早早截了枝,都是矮桑,伸手一够就能碰到枝丫。
林稹双脚踩在泥地里,轻轻压弯一根枝条,细细的、一点一点看过去——桑蟥卵是乳白色的,在青褐的树皮上应该挺好认的。
可一棵桑树得有多少枝桠啊,看了一根还有一根……没过多久,林稹的眼睛就开始酸涩起来。
再加上斗笠遮住了视线,怕祛不干净蟥卵,她只能把斗笠抬得高高的,雨丝密密的打在脸上,本就倦怠的身体越发僵冷疲惫……
好不容易刮完桑蟥,已经是夕阳垂暮,终于到了晚饭时间。
一盘姜辣萝卜,三碗赤豆饭。
这就是全部了。
林稹累得胃口全无,加上胳膊酸麻,连筷子都使不上劲儿。可要是不吃,一会儿还得干活,只怕更没力气。
没办法,她取了个木勺,舀着豆饭就往嘴里送。粗砺的豆饭划过嗓子眼,简直是上刑。
好不容易熬过一餐,林稹正想起身去房里歇一会儿,钱氏又匆匆嘱咐道:“珍娘,你去屋里理一理线,待我洗净了碗,稍后就来。”
林稹没回嘴,只是疲惫道:“娘,已经快酉时了,今儿只怕织不完一匹布。”
钱氏摇摇头,细声细气解释:“熬一熬罢。家里穷,又没有别的进项,再不勤恳些,就得断炊了。”
林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只是点了点头,拖着身子往正屋走。
自祖父去世、祖母被二房接去汴京后,正屋是钱氏和林父住着,为了借日光织布,又怕被雨淋湿,就把腰机放在离窗户不远处。
连日多雨,支摘窗早早的阖上了,屋子里暗沉沉的。
林稹点了一盏豆油灯,淡淡的臭气飘出来。
借着这点微末的光亮,她坐在小凳上,开始整理七八个线筒,再把经线一根根对齐,用竹片相邻着穿过扣眼……
脚踩踏板,手持梭子,咯吱咯吱的机杼声响起。
三人轮换织布,熬到月隐星稀,一匹绢终于织完。
钱氏数了数堆在柜子里的两匹生绢、五匹麻布,松了口气:“可算是凑齐了,明儿就去县里卖了。”
去县里?娇姐儿只觉浑身都松快起来,她凑巴巴凑过去:“娘——”
亲女儿,都不用开口就知道对方什么德行,钱氏板起脸:“不许去茶馆听小唱满嘴胡吣,见了路岐人也不许留下看,更不许乱跑。”
这就是答应她跟去县里了!
娇姐儿笑嘻嘻地搂着钱氏胳膊撒娇:“娘,你真好——”
钱氏抚了抚娇姐儿的鬓角,只觉浑身的疲惫都散了些。她忙里忙外,不都是为了这个孽障吗?
“好了,累坏了吧,快去歇息。”钱氏轻轻推了推娇姐儿。
娇姐儿正要开口,一旁的林稹已经站了起来,她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只是点了点头就往外走。
林稹腰背几乎板结,僵硬得连弯腰都疼,四肢犹如坠了铅块,又酸又涨。
她忍着倦意去灶台打了热水,擦了擦身子,这才躺在榻上倒头就睡。
朦朦胧胧间,林稹觉得床上一沉。林家不大,两个女儿同住一间房,大概是娇姐儿回来了。
林稹迷迷糊糊地想。
极快,她就再度进了梦乡。
林稹睡得沉,同在一张榻上的娇姐儿却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
她推了推林稹:“别睡了——快醒醒!”
林稹不欲理她,却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只是不动弹。
见她这样,娇姐儿索性卷了她身上薄被,又抬脚——
“你要是敢踢我,明天我就告诉隔壁陈娘子,说你睡相不好。”林稹睁开眼,倦怠道。
“你——”娇姐儿气急。陈娘子最喜欢闲磕牙,什么事儿经她一传,全村都知道了。
“我不闹你了,你不许去说!”
林稹应了一声,室内再度静默下去。
月华渐隐,细雨如织,在这样的静默里,娇姐儿翻来覆去,到底忍不住兴奋:“明儿我要去县里了!”
林稹阖上眼,继续睡觉。
“买一根红绫,叫娘给我缝个边,系在头上。”
林稹蹙眉,又听见娇姐儿继续絮叨——
“再买一朵照水梅。”
“石家的青铜照子也好,听说他家的靶镜……”
林稹睁开眼,淡淡:“没听见娘说的吗?家里都快断炊了。”
娇姐儿不说话了。
她再傻也能感受到,家里每况愈下。自祖父去世、祖母被京里的二房接走后,白米面成了籼米饭,最近又变成赤豆饭,足不出户的母亲开始冒雨下田、两个女儿没日没夜的织布……”
娇姐儿满腹喜悦烟消云散,沉默半晌,小声道:“那我明日不去县里了,再多织点布。”
没用的。
林稹睁开眼,望着黑漆漆的房梁。
家里的收入并不低。
一匹生绢要价一贯三百,扣除买生丝的钱,不算人工,其中至少有四分之一的利润。日织一匹,一年算一百匹,最少也能赚二三十贯。
再加上林父之前在县里教书,又有京里二房送来的钱……
林林总总加起来,年收入百来贯总是有的,林家好歹算是上等富农了。
之所以穷成这样,是因为要供林父和他儿子读书赶考。
寻常农户供一个读书人已是不易,钱氏一供供两个,可不就得咬紧牙关,能抠一分是一分嘛!
在这样的情况下,娇姐儿努力织再多的布,也是杯水车薪,根本填不满科举这个无底洞。
见林稹不说话,娇姐儿又嘀嘀咕咕:“爹都走了半个月了,也不知道到没到汴京?”
说着,娇姐儿又自我安慰:“等爹考上进士就好了。”
或许是这样的期盼让娇姐儿振奋起来,她心情颇好的翻了个身,没过一会儿就发出轻鼾声。
一旁的林稹阖上眼,却再无睡意,只余下满腹叹息。
她一言不发,只是静静地望向窗外。
白雨簌簌,绿桑飒飒,时有料峭春风吹打窗纸声,连宵不绝。
林稹想了许久,终于阖上眼,沉沉睡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就在她意识昏昏之际,忽然听见外头“砰砰”声。
有人在拍门。
林稹被“叩叩叩”的敲门声吵醒。
已是第二日,鸡叫三遍,天色微白。
“娇姐儿,快起来。”是钱氏在外面喊门。
好吵。
林稹蹙眉,翻了个身。
她四肢乏力,实在不愿起来。一旁的娇姐儿更是捂住耳朵,哼唧两声继续睡。
钱氏见里头没动静,又是好气又是好笑,知道小孩觉多,更舍不得喊醒自家女儿,偏偏骡车到了时辰就得走。
“娇姐儿,你若再不起,娘可就自己走了。”钱氏高声道。
娇姐儿哼哼唧唧的在床上扭了几下,这才分开黏糊糊的眼皮,迷迷瞪瞪的坐起来。
一旁的林稹虽然肌肉酸麻,但心里记挂着进城的事儿,勉强分开眼帘,趿拉上自己的平头布鞋,径自去取铜盆、刷牙子。
两人丁零当啷一通洗漱,娇姐儿嘴里含着冰凉的井水,含含糊糊的问:“你又不去县里,起得这么早做甚?”
林稹正取了笸箩,把昨天淋了雨的桑叶摊开来,好让太阳晒一晒。闻言,说道:“谁说我不去?”
娇姐儿的眼睛一下子瞪大了。她赶忙吐掉井水:“娘只答应了我,可没说要带你。”说着,搁下刷牙子,直奔正屋,嘴里还喊着“娘——娘——”
林稹懒得理她,又去东厢房取出几坛桑叶。乘着早起还有些功夫,先把之前存下来的桑叶切了。否则明儿的活计更多。
她坐在小杌子上,抓一把桑叶在麦秆铺出来的砧板上,咔擦咔擦拿刀切得稀碎。
农户就是这样,一天到晚做不完的活儿。
钱氏正在绕线锭,想乘着自家女儿洗漱更衣的时间再干些活儿。谁知她刚绕了没几圈,就听见娇姐儿噔噔噔的冲进来。
“慢些跑,像什么样子!”钱氏嗔她一眼。
“娘——”娇姐儿楼住她胳膊,歪缠起来,“你要是带她去,可不许给她花钱。”
钱氏一愣,下意识往窗户外张望一眼,见林稹面对支摘窗,正低着头、充耳不闻的切桑叶。
钱氏抿抿嘴,拍了拍娇姐儿胳膊:“可不许胡说八道!她是你阿姐,你但凡能学到她三分好,娘就安心了。”
娇姐儿撅起嘴:“你总说她好!她比我强在哪儿!”
钱氏又瞥了眼林稹,见对方照旧低头不语,不由得推了推自家女儿:“好了好了,天色都要大亮了,还不快去洗漱。”
娇姐儿牛股糖一般粘糊在钱氏身上,吵嚷着要她给自己梳双髻,要换时新的杏黄旋裙,不肯再穿麻布衫子。
钱氏被吵嚷的没办法,又舍不得怪她,只好从自己的官皮箱里取了朵照水梅的通草花替她戴上。
娇姐儿抚着照水梅,对着正屋的铜镜照来照去。
钱氏心知她臭美,也不管她,继续坐在窗口绕线锭,嘴里还提醒道:“快别照了,去把布搬出来,要走了。”
她话音刚落,一直在切桑叶的林稹搁下刀,抬头道:“娘,我也好了。”
钱氏微愣,从窗户里望出去,见林稹不知何时抬起了头,目光沉静的盯着她。
她“哎哎”的应了两声,又为难道:“珍娘,家里总得要有个守门的。”
林稹淡笑:“娘,进城卖布是大事儿,娇姐儿她心糙,又粗手粗脚的,我实在不放心她。”
钱氏噎住。
这竟是她昨日叫林稹刮蟥时的原话。
钱氏抿紧嘴,两条细眉压得低低的,她攥紧了丝线,不发一言。
一个坐在竹木椅上,高高的从正屋支摘窗望出去,另一个坐在四面透风的庭院小杌子上,仰着头,手上还沾着桑叶汁。
两人遥遥对视,俱不说话。
良久,钱氏起身,抚了抚身上的褙子褶,笑笑:“珍娘也大了,有自己的主意了。”
林稹也笑,轻声细语道:“我在家里待着闷,只是想出去散散心罢了。”
钱氏温声道:“这本就是应该的。方才娇姐儿作怪,我已骂过她了,你别往心里去。”
林稹笑了笑。
钱氏也不好再说什么,只管督促娇姐儿一起,抱着布一同出门。
林稹跟着钱氏的脚步往前去,刚转过一个弯儿,大老远见有几个小童把桑叶箩筐撂在一边,凑在杨树下比赛谁尿的远。
约莫是比输了,有个小童不服气,一把抓起泥巴扔进对方的箩筐里:“叫你拣雀屎去!”
对面的小孩哇哇大哭,扑上去扭打起来。
“这是怎么了?”哭声惊来了个少年人。
见有大人来了,小孩子们生怕挨骂,抱着箩筐一哄而散。
林稹看得发笑,却听见钱氏笑盈盈招呼那少年:“三郎今日也去县里?”
“师母。”孙吉抱着两匹布,侧开半步行礼。
林父在县学教书,教过孙吉几年。
“家母织了两匹布,想去县里卖了。”孙吉解释。
“三郎孝顺。”钱氏愈发满意。
听见自家母亲夸孙吉,娇姐儿嘴角微翘,又赶忙压下去,脸也红扑扑的,却只敢拿眼角余光偷瞄孙吉。
林稹一心惦记着去县里,生怕耽搁时辰。委婉提醒:“娘,天色不早了。”
钱氏正要点头——
“三哥——”人还没到,粗里粗气的嗓音先传来。
林稹转头一看,竟是那一日臊了钱氏的陈娘子。
她匆匆追上来。
“哎呦我的儿啊,娘来拿,娘来拿!”陈娘子赶忙把手里的空木桶撂在地上,想帮她儿子扛布,嘴里还念叨着“你说你,非要逞这个强!累坏了吧?”
“娘!”孙吉扯着布,抬眼一看,林稹正笑盈盈看着自己,霎时脸都涨红了。
陈娘子扯着布,不肯叫自家儿子沾手:“你赶紧回去温书,娘拿的动!拿的动!”
孙吉实在拗不过她,只好说道:“我把布送到骡车上就走。”
陈娘子这才肯罢休。转过头见钱氏母女三人各自抱了一匹布,就嗤笑起来:“家里男人不在,阿钱也动动脚,卖起布来了?”
钱氏脸上那点笑就淡了。
“贴补家用罢了。”她冷淡道。
陈娘子就哈哈大笑起来:“阿钱生得富贵,嫁得富贵,哪里就要补贴家用了!”
钱氏只将嘴唇抿得紧紧的,胸脯起伏数次,想骂,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娘,天色不早了,怕赶不上骡车。”林稹见了,赶忙解围。
“走罢。”钱氏一甩袖,拽上娇姐儿一马当先往前走。
林稹跟着她,一行人转了个弯儿,到了一扇乌木门口。
“杨大郎!杨大郎!”陈娘子砰砰敲门。
“来了——”乌木门咯吱一声开了。
门口站着个麻布宽衫的汉子,两手湿答答的。
他先请林稹一行人进去。
院里黄泥地上已经立着个穿葛布衫子的妇人,正把胡麻种子和湿草木灰搅拌在一起。
见有人来,她笑着招呼:“都来了啊……大郎,你快去把骡子套好,该走了。”
杨大郎就去木头棚里把骡子拉出来,又套好平头车。
见日头差不多了,再也没人来,杨大郎这才粗声粗气说:“走罢。”
一只骡子拉的平头车不大,最多也就能拉点货,载个人,再多就不行了。
故而杨大郎站在一旁赶骡子,其他人跟在平头车前后走。
今天不是开墟市的日子,进县里的人少。
除了林稹等三人,也就陈娘子,加上同村人王七郎和他浑家阿李,再无旁人。
众人走着走着,陈娘子闲不住,问起钱氏:“你家大郎还没消息啊?”
钱氏脸色就有些不好看。林家祖籍在河北,林父半个月前进京赶考。
时至今日,尚无音讯。
“刚走,哪儿那么快。今儿才三月,到了八月才解试,少说还要再等五六个月,才能知道中没中。”钱氏笑笑,解释道。
“五六个月!”陈娘子惊叹起来:“真是个奢遮人物,好阔气哩!一走就是半年,京里米价腾贵,也不知道要花多少银钱才够!”
钱氏脸色青白,勉强笑笑:“要不了多少钱的,大郎入京,自有亲兄弟投靠,不劳陈娘子操心。”
“亲兄弟?”陈娘子好奇,“你们京里还有亲兄弟,那怎么不去投奔?留在我们这山坳子做甚?”
钱氏嘴唇紧抿,一时竟说不出话来。投奔?她难道就不想进京吗?都是林家子,怎么二房就在京里享福,她却只能在乡下煎熬!
偏钱氏不知道林家大房二房到底为什么分隔两地,就只能勉强笑笑,描补道:“娘早早的被二房接去了京里,许是再过些日子我们也要进京了。”
娇姐儿眼前一亮,巴巴的凑过去问:“娘,我们真要上京吗?”
钱氏微愣,只觉周围人的目光刺挠挠的,都盯着自己呢!
她被架住了,哪里好反口,一咬牙:“要去的。”娘还在京里呢,总不至于扔下他们大房不管吧!
一听她这么说,娇姐儿眼睛亮晶晶的,一个劲儿的追问什么时候去?是不是爹来接他们?弟弟呢?弟弟也回来吗?
听得林稹头大如斗。这种谎哪能撒呢?万一最后没上京,这舌根子能在村里被人嚼十年。
果不其然,陈娘子已经乐了,大声道:“等林家大郎回来,就要接阿钱去京里,做状元夫人喽!”
“轰”的一声,好像热水泼进油锅里。众人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
有说“林大郎都快四十了还考状元呢”,也有艳羡不已,说“阿钱要发达了”,更有甚者,直接问钱氏“你们搬去京里,那家里的田地佃不佃?”
香的臭的,一股脑往钱氏耳朵里涌。
直听得钱氏又羞又臊,恨不得撕了陈娘子的嘴。
见钱氏脸色涨红,陈娘子竟还在兀自大声说笑,林稹赶紧解围:“诸位说笑了,去不去京里还没定下呢。总得等我爹回来再说。”
大庭广众的,她不好拂钱氏的面子,只能替她描补:“便是真要去京里,那也不过是探亲罢了,还得回来的。”
又赶紧岔开话题,“别说京里,这县里我都没去过几趟。说起来二位娘子去县里做什么?也去卖布吗?”
“瓦锅坏了,去县里找人补。”阿李蹲下来,瞧见黄泥路旁有坨干牛粪,手里两根树枝一夹,扔进了背篓里。
林稹眼睛微圆,颇为震撼,但见众人不以为意,也只能默不作声,继续往前走。
“眼睛真尖,怎么看见的?”陈娘子都顾不上钱氏了,酸唧唧的。
牛粪是个好东西,不晓得哪个败家玩意儿,拉在路上也不捡。
见陈娘子为了块牛粪酸了吧唧的,叫钱氏越发看不上。
她秀眉微蹙,想想孙吉,再看看捂住鼻子的娇姐儿,不由得叹气。
十三岁了,总得慢慢寻摸起来。
日头一点点上移,陈娘子全副心神都沉浸在如何排查路上的有机肥料,再也顾不上跟别人聊天了。
一行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说了几句,没过多久就到了县里。
大伙四散开来,卖布的卖布,补锅的补锅。
林稹抱起布,跟着钱氏往前走,但见这县里家家户户白墙乌门、青檐黛瓦,又多数临河而居,河流纵横交错,时有船夫摇橹行于水上……
街面两侧都拿油布竹竿搭了棚子,底下有饮子摊叫卖着玫瑰卤子,老书生支了个摊子佣书兼卖酸诗,菜农大剌剌地把黄花菜摆在地上,又有挑了蜜橘来卖的……
一路行来,民居、川广生药铺,专司绸缎生意的牙行、铁铺、染坊、米铺、典当行、裱褙铺……
看得越多,林稹心里就越松快。当地百姓日子还过得去,至少能让人安安稳稳的做点小本生意。
只是走得久了,总能看见三五个闲汉,嘬着牙花子,大剌剌的站在棚子底下挑三拣四,嫌弃荏油太贵,不如胡麻油便宜,又嚼了几颗蜜饯棠球,非说甜坏了喉咙,要那店家赔钱。
待林稹等三人路过,那群地痞又挤眉弄眼地吹口哨,还有不知羞的故意扯着嗓子唱——
“脚步儿必定是冤家来到,悄悄地站多时,怎不开言叫?见你衣衫轻又薄,想来是浑身似火烧……”
说着说着竟还敢伸手。
“你们干什么!”娇姐儿又气又怕,带着哭腔骂道。
钱氏面色发白,心脏狂跳,硬挺着把娇姐儿护在身后。
“哪儿来的捣子!”林稹厉声呵斥,“娘!你去衙门找爹,叫他带几个兄弟来!快去!”
几个无赖面面相觑,到底没再敢伸手。又是青天白日的,围过来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只好钻进人群里,蔫头耷脑的走了。
林稹一缓下来,才发现自己心跳得砰砰的,这会儿腿都软了。
她深呼吸一口气,看着脸色发白的钱氏,问道:“娘,我们要去哪里卖布?”
钱氏腿也软的厉害,神色复杂的看了她一会儿,这才憋出一句“银孩儿布帛铺”。
“就在细米街,前头有棵大柳树。”
钱氏说完,心神稍定,取出香妃色绣帕,给哭哭啼啼的娇姐儿揩眼泪,哄她:“不哭了,再哭就不好看了。娘一会儿卖了布,给你买朵瑞香花戴。”
娇姐儿带着点哭腔:“我不要瑞香花,要粉团花。”
眼看着哄好了,钱氏连忙答应:“好好好,娘一会儿就找货郎买。”
林稹愣愣的看着这一幕,半晌,抱紧了怀里的布,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进了布帛铺,迎面就是个穿秋香色褙子的娘子,正抚着一匹布与另两个妇人攀谈。
“娘子,这可是正宗的建阳小纱。你摸摸,这质地……”
钱氏便上去与她们攀谈。
那掌事娘子见钱氏来了,只管笑着对两个妇人说:“二位且稍待……芸娘——你带着钱娘子去后头喝杯茶水。”
却见正拿掸子扫灰的芸娘应了一声,掀开布帘,拉着钱娘子进了后院。
娇姐儿正张望着铺子里的各色布料,眼珠子都舍不得挪开。
林稹硬生生把她拽进后院。
刚进后院就听见钱氏在说:“怎么又低了?”钱氏皱眉,“生绢且不说,这些麻布以前都是三百二十文的。”
芸娘暗自撇嘴,又叹气:“家里做生意也难啊,住税又涨了,从前都是千钱抽三十,如今要交三十五文了。我娘收了你的布,要是卖不出去,岂不蚀本?”
钱氏抿着嘴,想讨价还价,又怕惹了对方不快,日后不收她的布。
她犹犹豫豫,竟不敢开口。
林稹看了眼她,上前一步,招呼道:“小娘子,这布虽是苎麻土布,但你瞧,我织得密密匝匝。寻常人家买回去,春秋两季穿,决计不亏。”
富贵人家才要上好的苎麻,夏日穿来轻薄透气。穷人家夏季少穿些就是了,买起布来更在乎结实便宜。
芸娘犹豫了一下,还是不肯答应。她娘说了,县里就她家开的布帛铺,收苎麻布价最高。
别人家都只给两百八十文的,她家给三百文,足够了。
两人再三拉扯,林稹见她不肯答应,忽然为难道:“这价钱实在有些低了。我和我娘做不了主,得回家问问爹去……娘,你说呢?”
钱氏一愣,点了点头,没拆穿她。
两人掀开布帘,从后院出来,见掌事娘子还在招待那两个客人。
“前些日子刚进了些杭绢……钱娘子,这就走了啊?”掌事娘子见三人抱着布进来,又抱着布出去,脸色就有些不好看。
客人还在呢,她也不好说什么,只能笑盈盈地目送林稹三人出门
刚出门,钱氏就有些后悔:“要是咱们这会儿再去卖布,只怕她们又要压价。”
林稹摇摇头:“娘,你自己说,你往日里要是想买这样一匹布,得花多少钱?”
钱氏愣了愣,低声道:“少说也得四百文……珍娘,那掌事娘子给得是少,可要是我们自己卖,上哪儿找客人去?再说了,寻常人家做衣裳,只要个两三尺,五匹布得卖到什么时候去。”
钱氏越说越后悔:“是我想岔了,悔不该听你的。”说着转身就要回布帛铺。
偏又想到林稹说要去找爹,总得过一会儿才能进铺子,否则进去了,别人一句“钱娘子这就找完夫君回来了?”
真真是臊得慌!
她又气又悔,又怕一会儿丢脸,只好立在墙角,等时间过去。
“娘,没客人不要紧,我抱着布挨家挨户去打听便是了。”林稹说。
钱氏心里不快。她是官宦之后,娇姐儿更是御史家的孙女,哪能到处丢人呢!
见钱氏不说话,心知她多半是拉不下脸来,林稹劝道:“娘,家贫无着落,脸面哪有生计重要?”
钱氏不说话,只是冷冷道:“家里不缺这份卖脸面的钱!”
一旁的娇姐儿少见她娘冷脸,这会儿被吓了一跳,喏喏道:“娘,你别气,三百文也挺好的。”
钱氏神色稍缓:“娘不气。”又道:“珍娘你大了,有自己的主意,娘管不住你了。待你爹回来,我自会请他来管教你。”
寻常人被这么一吓,只怕就要低头了。可林稹实在受不了不沾油腥的日子了。
她低声道:“娘,我鸡鸣就起,点灯熬油到戊时才睡,眼睛都快累瞎了。就这么熬着,两日才织一匹,你若叫我舍了这一百文的差价,我不甘心。”
钱氏也是吃过苦的,闻言神色稍缓,安慰道:“等你爹考上进士就好了。那时候你就是官宦人家的女儿,再不用吃苦遭罪。”
那要是考不上呢?况且就算考上了,不贪污受贿,家里能有多富裕?还不是要为了生计奔波。
林稹没说话,只是无奈道:“娘,我也不要你们去,我自己去卖就是了。”
钱氏犹豫了一下,没说话。
这就是默认了。
“傍晚我在布帛铺等娘。”说完,林稹抱起布就走。
娇姐儿还傻乎乎地问:“你去哪儿?”
林稹径自消失在了街尾。
“娘!她自己卖布去了!”娇姐儿疾呼。
“叫她去!我劝了,她不听,又有什么办法!”钱氏又拿指头戳娇姐儿额头:“你站在这里不许走动,娘去一趟布帛铺,马上就回来。”
她哪里舍得女儿跟她一块儿进去挨白眼。
“娘——”娇姐儿搂着她胳膊撒起娇来,非要钱氏带她一起去。
那么多的料子啊,缠枝纹的轻绢、四合如意的建阳纱、双凤穿牡丹的小绫……
多漂亮。
买不了看一看也好啊。
钱氏受不住她歪缠,等了一会儿,到底带着她又进了布帛铺。
“钱娘子问完了?”掌事娘子早已送走了客人,拨了拨算盘,盯着钱氏笑。
钱氏讪讪点头,低声道:“劳烦樊娘子了。两匹麻,两匹绢。”
樊娘子这才笑盈盈地接过布,取了钱,又道:“方才差点忘了……钱娘子,前几天你爹托了个急脚子带口信来,叫你有空回家一趟。”
钱氏微愣,这才想起半个月前大郎要走时,写了封信给她爹,请岳丈多多照看她们母女三人。
这也没什么,抽空回一趟娘家便是。
钱氏虽不高兴自己不卖布,樊娘子便不肯捎口信,却也不愿得罪她,便点点头,道了声谢,径自带着娇姐儿出了门。
却说此时林稹已经出了街口,正抱着布,四处张望。
为了不被那群闲汉纠缠上,林稹专往人多的地方去。
瞧见瓦片齐整的、是青砖房的,她都要敲开门来问一问。
“娘子,要买布吗?”林稹抱着布笑盈盈站在门前,又忽而艳羡道:“娘子你这半月木梳背是哪儿买的?真好看,插在娘子头发上,比画上的神妃仙子还好看呢!”
梳合髻的妇人不由得漾出一点笑来。又见这小娘子稚弱,不像个坏人,便问道:“你这布多少钱?”
“不贵的,一尺只要九文钱。娘子你摸摸,自家织的麻布,结实耐磨,春秋穿起来正正好,便是夏天穿,苎麻也凉快。”
一尺九文是真便宜。布帛铺里要卖十一文呢。别看就差两文,哪个精打细算的人不在乎这个钱?
见她有些心动,林稹又笑盈盈道:“娘子若买得多,我再给娘子抹个零头。”
那妇人就笑道:“我家里有剪子,你给我扯个三尺。”
林稹当场给她抹了两文的零头,临走了还要送人家一句吉祥话:“娘子心善,保管能发大财!”
把人家逗的前仰后合。
林稹就这么一家一家的敲门卖。
她生得俏,瞳仁又大又亮,看人的时候就显得无辜可怜。逢人就带三分笑,话说得又好听。就算有人不买,她也客客气气的。
到了半下午那会儿,林稹几乎要把布卖光了,只剩下最后一尺两寸。
她跑得浑身是汗,鬓发湿漉漉的搭在耳畔,脸也红扑扑的。
挣钱真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