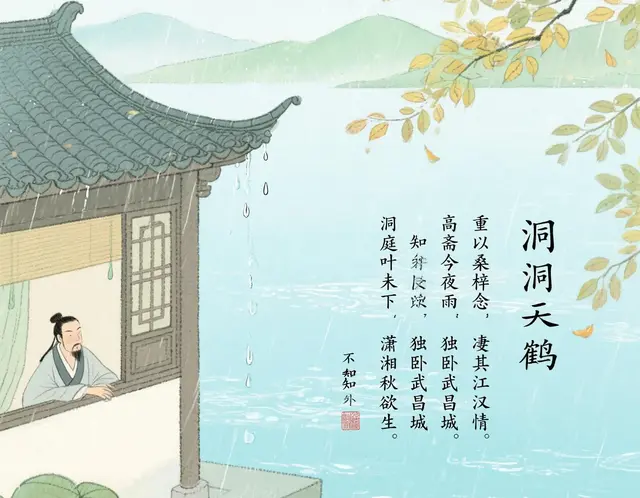读书,品诗,看电影
悟人生
我是威评书影史

01
《关山月》
唐·储光羲
一雁过连营,繁霜覆古城。
胡笳在何处,半夜起边声。
储光羲,是唐代诗人,他的籍贯有两种说法,一种说他是山东兖州人,一说他是江苏润州人。他于开元十四年(726年)进士及第,与崔国辅、綦毋潜同榜,初任冯翊县尉,后转汜水、安宜等地县尉。
不过他却在安禄山攻陷长安后受职,在唐朝复克平乱后,被贬岭南,客死他乡!
简单来说,他也是经历了唐朝从盛世到坍塌的一个过程。并且由于其自身漂泊的经历,写的诗也充满一种惆怅和落寞叹息之感。

02
这首《关山月》是他的代表作,则以边塞为背景,孤雁、连营、繁霜、古城、胡笳,构成了一幅苍凉、雄浑的画面,暗含戍边将士的思乡之情。
夜深人静时,那孤雁的哀鸣掠过连绵军营,在霜气凝重的古城上空久久回荡。不知何处飘来的胡笳声,裹挟着塞外风沙的粗粝,将戍边将士的思绪引向更遥远的故乡。
帐中老兵辗转难眠,起身拨亮将熄的炉火。火光映照着他甲胄上的冰凌,折射出星星点点的寒芒。二十年前初至玉门关时,他曾在同样的月夜听见新制的胡笳试音,那时曲调里还带着长安乐工的生涩。如今这浸透风霜的旋律,早已与漠北的朔风融为一体,时而呜咽如泣,时而激越似刀,在城墙垛口间碰撞出金戈铁马的回响。
马厩传来战马不安的踏蹄声。这些随军多年的伙伴,竟比哨兵更早察觉远方动静。老兵掀起帐帘望去,见巡营的年轻校尉正仰头凝视雁影,手中长枪的红缨在月光下像一簇不肯熄灭的火苗。他忽然想起阵亡的同袍曾说,南飞的鸿雁会捎去阵亡者的家书——可那些永远留在祁连山下的少年,他们的家书又该托付给谁呢?
霜色渐浓时,城楼传来换岗的鼓点。老兵系紧佩刀走向哨位,身后传来此起彼伏的胡笳应答。这跨越关山的声浪里,既有对故园的牵念,亦藏着寸土不让的誓言。当第一缕晨光染白戈壁,昨夜所有声响都将化作冰河下的暗流,继续滋养着边塞永不褪色的传说。

03
储光羲有出使西北边地的经历。这首诗是其把所见所闻凝练而成。
除了征戍离别之情,还透露出一份淡淡的惆怅,还有孤独。
在这片苍茫的边塞,月光如霜,洒落在连绵的关山之上。征人的脚步早已踏碎了沙砾,却踏不碎心底的思念。夜风呜咽,仿佛在低诉着那些未及寄出的家书,字字句句都被吹散在无尽的戈壁之中。
储光羲笔下的孤独,并非仅是形单影只的寂寥,更是一种与天地对话时的渺小感。站在高处远眺,烽燧孤烟直上,与冷月相对,人便成了这宏大画卷里最微不足道的一笔。他的惆怅,源于对战争无休的疲惫,也源于对生命如草芥的悲悯。那些倒下的身影,最终化作了沙丘的一部分,连姓名都被风沙掩埋。
然而,在这份沉重的底色中,诗人仍以克制的笔触留下了一丝温度。或许是帐外偶然传来的一曲羌笛,又或许是黎明前篝火旁老兵讲述的故乡旧事。这些细微的闪光,让铁衣冷甲的寒夜有了短暂的松动。
当后人再读此诗时,看到的不仅是盛唐边塞的壮阔,更是一个文人站在历史裂隙中的凝视——他用诗句接住了那些即将坠落的叹息,让千年后的我们依然能触摸到,那一轮关山月曾照过的、未凉的体温。

04
唐朝的边塞诗在前期以豪迈雄壮闻名,到中后期,尤其在“安史之乱”之后,变得有些沉郁惆怅。
安史之乱的战火不仅焚毁了盛唐的繁华,也在边塞诗人的笔端淬炼出新的锋芒。中唐诗人李益的《夜上受降城闻笛》中,"回乐峰前沙似雪"的凄冷月光,已全然不见岑参笔下"忽如一夜春风来"的蓬勃气象。
当戍边将士的铠甲不再反射着开疆拓土的荣光,而是浸透着思乡的寒露,边塞诗便从马背上的战歌逐渐演变为沙碛中的低吟。
这种转变在陈陶的《陇西行》里体现得尤为深刻。"誓扫匈奴不顾身"的壮语之后,紧接着"五千貂锦丧胡尘"的惨烈现实,最终凝结成"可怜无定河边骨"的沉痛叹息。
诗人们开始用更复杂的笔触勾勒战争图景:烽燧台上的狼烟与闺阁中的泪痕,校尉的虎符与农妇的捣衣石,在对比中形成强烈的叙事张力。就连边塞常见的"大漠孤烟",在张籍笔下也化作"欲祭疑君在"的恍惚烟缕。
值得注意的是,晚唐边塞诗在沉郁中又滋生出新的美学特质。当杜牧在《河湟》中写下"牧羊驱马虽戎服,白发丹心尽汉臣"时,那种混合着历史沧桑感的忠诚,已超越了单纯的豪迈或哀伤。这种在绝境中依然坚守的精神底色,恰似戈壁滩上的胡杨林,在风沙的磨砺中展现出更为深邃的生命力。

05
而储光羲的这首边塞诗《关山月》的关注点,则从一种广阔转变到个体身上,让人感受到细节的那种思乡情浓的微妙情感。
当诗人将目光从苍茫的戈壁收束到戍卒冻裂的手指时,那轮亘古不变的月亮突然就沾上了人间的霜。"一雁过连营",一个"过"字里藏着多少欲说还休——是思乡的无奈,是梦回故乡的恍惚,更是把漫天月光都望成家书的痴念。
这种个体化的抒情视角,恰似在历史画卷的留白处点染的朱砂。当其他边塞诗还在描摹"黄沙百战穿金甲"的壮阔时,储光羲偏偏注意到士兵夜晚的失眠。他写"半夜起边声",不是泛泛的乡愁,而是具体到某个深夜惊醒的士卒,摸着贴身藏着的桃木梳——那是临行前妻子塞进他战袍的,梳齿间还缠着几根青丝。
最动人的是诗中那种克制的抒情。诗人不说思乡有多痛,只写"繁霜覆古城"的悬想,此刻故园的楼头,是否也有人正望着同一轮月亮?这种双向凝视的笔法,让荒寒的边塞与温软的江南产生了奇妙的共振。让人仿佛看见月光像银梭般在天地间来回穿引,织就一张笼罩所有离人的情思之网。
这般细腻的感知,源自诗人对生命温度的珍视。当盛唐的边塞诗人们竞相用金戈铁马丈量帝国版图时,储光羲却用胡笳之声敲打了一颗心的重量。他让人们明白,历史不仅是将军的功名册,更是无数平凡士卒用冻伤的指节,在长城砖石上刻下的无名诗行。
-作者-
威评书影史,自评自说自开怀,更多诗评、书评、影评,给您不一样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