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解析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考
解析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基于罪刑法定原则的思考一、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争论的焦点
(一)“纽扣案”与解释论之争
刑法学者经常会因对刑法规范解释的分歧,而对同一案件的判决结果做出不同的评价。

以“纽扣案”为例,几名妇女因为自己一方在前日的冲突中意外死亡,跑到对方住宅兼纽扣厂哭闹。
她们将摆在庭院四周的200种不同型号的纽扣倒在地上,掺杂在一起。
这些纽扣有成品,也有半成品;有合格品,也有不合格品。

经有关鉴定机构的鉴定,纽扣厂损失为12万元。
对此案,控方以故意毁坏罪起诉,将毁坏解释为对他人财物造成损失;辩方认为是民事侵权导致的纠纷,并认为如果将毁坏解释为造成财物损失,那无疑是脱离了公众认知的范围。
此案的关键是如何解释故意毁坏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75条的规定,故意毁坏罪是指故意毁坏公私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行为。
而关于毁坏的含义,刑法理论上存在不同的主张。

物质的毁弃说认为,从物质上破坏、毁损财物的一部或者全部,因而侵害财物的本来的效用的行为,才是毁坏。
理由是,毁弃、损坏概念的本来含义不在于实施有形的作用,而在于通过这样的方法,物质性地破坏、毁损财物的全部或者部分,从而造成侵害财物效用的结果。

有形侵害说认为,通过对财物有形的作用,毁损财物的无形的价值,以及毁损财物的物体的完整性的行为,就是损坏。
此说旨在限制处罚范围。

但是,“有形的作用”的界限并不明确,结局与效用侵害说没有实质区别。
效用侵害说认为,凡是有害财物的效用的行为,都属于毁坏。
因为本罪的核心就是损害财物的效用,而财物效用的减失与财物物质性的破坏,在反价值性上是完全等同的,都是导致财物不能使用。

从上述的描述来看,辩方采用了物质毁弃说,认为纽扣的物理性质并未更改,所以不影响使用价值,纽扣在分离之后仍然可以正常使用,这是形式解释的结论。
控方采用了效用损害说,毁坏包括了减少或毁坏纽扣效用的一切行为,而不仅限于从物质上损坏纽扣。
因此将200种纽扣掺杂在一起造成难以原价售卖使用的行为是毁坏财物,这是实质解释的结论。

至此,本案两种迥异的解释结论的背后是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对立。
形式解释论主张解释应基于刑法文本的核心意义,以文理解释作为首要方法,确认刑法的安定性和人民的可预测性,保障公民自由。
实质解释论主张解释刑法法规的构成要件应当以处罚必要性为出发点,通过目的解释为首要方法来实现个别正义,避开语言的静态性弊端,防止恶法亦法的局面。

两者的解释理由都具有双刃剑的效果,文理解释虽然可以限制刑罚权的滥用,确保刑法之盾的安定性和可预测性,但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滞后,严重威胁和侵蚀刑法适用的正当性。
而目的解释虽然可以克服刑法的僵化危机,焕发其生命力,发挥刑法之网的严密性与灵活性,但同时也不断挑衅着罪刑法定的制约机制。
因此,两种解释论的对立从解释理由的角度来看是文理解释与目的解释的对峙。

(二)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分歧焦点
实质解释论的支持者,张明楷教授引用了庞德《机械化的法理学》中的观点,认为形式解释论效仿机械化的法理学,法官判决案件的过程就像工人使用磨米粉机器那样机械僵硬。
正像马克斯·韦伯百年前所设想的那样,现代法官是自动售货机,投进去的是诉讼费和诉状,吐出来的是判决和法典上抄下来的理由。
这些观点似乎将形式解释论推向法律形式主义的立场定位,即形式解释论不会采用实质判断,而实质解释论却绝不支持对刑法进行纯粹机械式的解释。

此观点把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描述为要不要实质判断之争(目的解释作为实质判断的核心方法,所以此问题实际为要不要目的解释之争)。
这其实是曲解了形式解释论,将形式解释论中的“形式”偷换为法理学中的“形式”。
而这两者的“形式”是不同内涵的,前者的“形式”是用来强调构成要件符合性的形式判断,而后者的“形式”是用来描述一种去价值因素后的纯粹逻辑的法律思想。

在实际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形式解释论并不反对目的解释的使用,而是将目的解释视为俄罗斯套娃中的一个小娃。
在文理解释的大娃的包涵内发挥机能,形式解释论支持者不会进行偏离刑法规范实质的机械化解释。
从工具论的角度看,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的分歧焦点在于:当对刑法条文进行解释的时候,形式解释与实质解释之间的位阶关系,具体表现为解释理由间的位阶关系问题。

尽管方法论一直以来都在尝试确定各种解释理由的抽象顺序,来解决在个别案件中,不同的解释理由分别推导出互相对立的结论的难题,可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答案。
但是为了避免最混乱的局面出现,必须抉择文理解释与目的解释的决定性权限。
所以,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争其实是判断理由决定性之争。

文理解释的决定性在于:文理解释是任何刑法解释的初始解释理由,通过文理解释得到的文义范围不能超过刑法用语可能具有的含义。
否则都是违反罪刑法定原则的解释(有利于被告人的类推解释除外),即使符合刑法条文的目的,也不能被采纳。
目的解释的决定性在于:一个法条通过多种解释理由可以得到多种的解释结论时,必须要选择符合法条目的的解释结论。

进行目的解释,意味着考虑文字背后的真实目的,根据具体情境权衡各种解释理由,形成具体的协调标准。
但是,目的内容似乎成了一个超法规的实质解释标准,而目的解释僭越了罪刑法定原则。
对此,有学者做出了以下辩护:“凡是解释,不管是形式解释还是实质解释,都是以文本为依据的,否则就谈不上是一种解释。

实质解释论事实上也是坚持罪刑法定主义的。
只不过在实质解释论者眼里的罪刑法定,不仅具有形式的侧面,而且还具有实质的侧面。”
在笔者看来,罪刑法定的实质侧面是刑法学发展的必然成果,也是刑法实质化运动的折射产物。

它意味着罪刑法定原则完善形态的确定,这是一个自发的进化过程,实现了从追求形式合理性向追求实质合理性的超越。
罪刑法定原则只有一个,但其内容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角度和思考逻辑也是有不同方向和侧重点的,所以才会诞生形式解释论和实质解释论。
从本体论的角度看,形式、实质解释论之争实际上是罪刑法定原则发展过程中的不同理解之争。

综上所述,形式解释论与实质解释论之间的分歧焦点从外部来看是文理解释和目的解释两种解释理由的位阶关系问题,而从内部来看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理解分歧问题。
在此,笔者将由里及外,从矛盾内部出发,从罪刑法定原则对两种解释论进行正本清源,再解决外部的位阶问题,完成两种解释论从本体论到工具论的逐步解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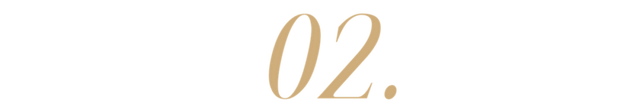 客观化预测可能性主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客观化预测可能性主体———大数据和人工智能考夫曼曾说:“确定生活事实是否对应于规范事实,一直是一种目的论的判断。”

对于可能文义范围是否符合国民的预测可能性,也是一个生活事实对应规范事实的判断,因此避免不了个人目的的思考。
文章开头提及的“纽扣案”,陈兴良教授对此案关键的毁坏含义的理解是选择物质的毁弃说,强调因物质性上的破坏而导致财物效用的损失,这比较符合毁坏的原义。
同时还谈道,如果采用效用侵害说,一切使他人财物造成损失的行为都属于毁坏,这很可能超出了大多数民众的认知水平。

现代辞书是这么解释毁坏的,如《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损坏、破坏:不许毁坏古迹,毁坏他人名誉”。
辞书所举的例句,“不许毁坏他人名誉”中毁坏的含义可解释为价值的损失或减少,不一定要求有物质性的破坏,而陈兴良教授却认为这一含义是超出民众认知水平的。
词典是符合时代的规范标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语言变化而不断编纂和修正的,当然可以代表国民的认知水平。

所以,认为毁坏含义不包括价值的减少或丧失这一论断,归根结底,还是来源于陈兴良教授对法条目的的理解。
而刑法中的人一般是以标准人的形象,被假设为具有平均能力,那么一般公民的预测可能性也应该是符合标准性,尽可能地符合客观现实中标准人的认知水平。
预测可能性本应该是一种公民的客观反映,但事实上主体只能由独立个体的解释者担当,这是一种不幸。

罗尔斯将正义分为功利正义与直觉正义,预测可能性要实现的是功利正义的要求,但现实中的解释者必然会对预测可能性做出包含直觉正义的判断。
万幸的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即客观化的预测可能性主体可能在未来会实现。
今天,人类社会进入到一个大数据、人工智能的时代,但这不意味着能实现韦伯所说的那种情形———把案情扔到自动售货机,判决自动就能吐出来。

智能时代真正的意义是,促进科技辅助审判的新型司法工作模式的革新。
如上海的“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统”、北京市法院的“睿法官”等一系列智能系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就是第一波革新浪潮。
客观化预测可能性的难点是如何预测社会民众对文义范围的判断结果。

这一结果不仅在数量上是浩瀚无际的,在表达程度上也具有高度的模糊性,即在判断资料和判断标准上都有技术的难度。
大数据可以解决判断资料上的难点,通过广泛的传感技术、大规模数据存储和通信技术的应用,建立系统的语言使用数据库,来搜集民众对语言的使用情况。
大量的数据是建立精准模型的前提,可如何建立精准模型来准确理解语言是一个难题。

人与人之间在一个大致相同的文化背景、预设目的的前提下,是可以正常交流的。
但过去的计算机智能还远未达到像人一样理解交流环境和语言的水平。
例如约翰·希尔勒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中文房间”的思维实验。

假设一个不懂中文只会英语的人关在一个房间内,他被要求回答几个中文书写的问题,而房间内有一本中英文对照手册,他只要依靠这本对照手册就能用中文回答问题。
希尔勒用“中文房间”这一思维实验来思考人工智能的局限性,电脑(对照手册)尽管能回答中文问题,但它不可能理解一种语言中句子的意义,这是虚假的智能印象。

因为电脑只能模拟人类大脑左脑思维,按照既定的程序来分析处理问题,而缺乏人类右脑思维方式,即抽象的、跳跃的线性思维,所以无法做到理解语言的意义。
而现在的人工智能技术已经有了极大的突破,21世纪以来,传统的人工智能模式受到质疑,人工智能学家提出了一种全新的模式,即“人工神经网络”,也称为“联结主义模式”。

这是一种模拟延展人类思考的神经元模式,模拟人脑的构造和运行状态,形成质的突破。
借助此深度学习算法,各大实验室在机器学习领域均取得了很多突破性成果,如Google发布了新一代的Google Translate将机器翻译与人类翻译的准确率差距缩小了55%到85%。

所以人工智能作为判断标准的技术支持是合理的。
通过深度学习人脑的判断准则,模拟人类对自然语言的思维逻辑,准确地理解语言使用的真实含义,争取最精准地分析民众对文义范围的判断结果。

大数据时代的来临,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让客观化预测可能性主体具有实现的希望。
相比科学发展,法律制度总是滞后的,我们要以前瞻性的眼光去思考法律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