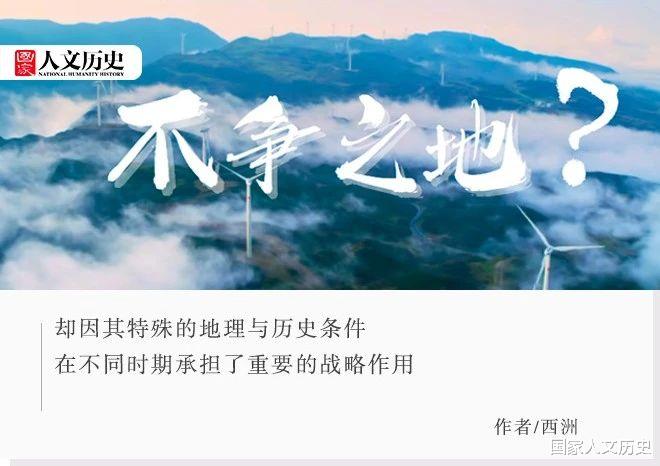
提起贵州,你会想到什么?是茅台酒,老干妈,酸汤火锅?还是长征路上那场遵义会议?又或者是那句十分出名的旅游传广告:走遍大地神州,醉美多彩贵州。
贵州位于我国西南部,山地和丘陵占据了全省面积的90%以上,是我国唯一没有平原支撑的省份。这片遍布喀斯特峰林、溶洞和峡谷的土地,在古代文人笔下是“瘴疠之乡”,在中原王朝眼中更是“化外之地”。俗语称贵州“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也有很多人戏称,贵州这地方在古代是妥妥的“兵家不争之地”。

贵州。来源/CCTV9《航拍中国(第三季)》
但若翻开史书细看,我们不禁要打个问号,贵州的军事价值真就只配得到一句 “不争之地”的评价吗?
为何“不争”?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地势崎岖,是岩溶化高原山地,且地形被河流切割得极为破碎。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黔游日记》中写道:
“山势如犬牙交错,马不能行,人须攀藤附葛。”

雁荡山徐霞客石像。摄影/张景珍。来源/图虫创意
在冷兵器时代,军队的机动性和后勤能力均受地形影响,贵州这种“地无三里平”的地形(喀斯特地貌),蜿蜒曲折的山脉、深谷、河流,都使得大规模军队行军难,补给更难,对古代军队来说堪称灾难。

贵州地势图。来源/星球地图出版社编制《贵州省地图册》,星球地图出版社2017年版
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主力从四川入云南,却避开贵州腹地,只因“牂牁(zāng kē)道险,粮运不继”。《平播全书》记载,明代平定播州之役时,24万明军翻越娄山关,粮草全靠民夫肩挑背扛,“运粮一石,费银十两”——听起来就挺费劲的。

来源/《三国演义》
再来说说“天无三日晴”。贵州地处亚热带季风气候区,气候复杂,多阴雨天气。古代贵州森林密布,加之湿热多雨,导致瘴气(疟疾、霍乱等传染病)横行。
民国《贵州通志》记载:
“黔处万山叢谷中,地穷而气,……大抵黔地气候不齐,一日之间,乍寒乍暖,百里之内,此燠彼凉,稍一不慎,易生疾疹。”

贵州军事屯堡建筑。摄影/奇怪的食客,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供图

安顺天龙屯堡。摄影/刘聪,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供图
外来军队难以适应这种“谜一样”的气候,而且疫病肆虐也会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唐代时,安南(今越南北部)一带的战事就屡因气候和疾病导致唐军折损惨重,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贵州。在明朝平定西南的过程中,驻扎贵州的明军常因水土不服和疫病困扰而进展缓慢。林则徐途经贵州时,也曾哀叹:
“士卒病亡者十之三四,非战之罪,实天亡之。”
众所周知,古代战争的核心目标是控制人口密集、资源丰富的经济中心。当时贵州经济较为落后,加之气候地形的限制,农业生产有限,粮食供应困难,不仅难以支撑大规模军队长期作战,而且就算打下来了也没饭吃。这对于需要大量后勤支持的中央军队而言是致命的。

来源/《大明风华》
直到明代,贵州仍是“刀耕火种,不通牛耕”,中原王朝即便占领此地,也需从湖广运粮供养驻军,成本极高。由于贵州地瘠民贫,从洪武时期开始,朝廷便常常予以蠲(juān)免。
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后,财赋实力在全国各省中排名最末,由于财政窘迫,财赋所出不能自给,全仰邻省协济。据巡抚何赵鸣《严催协济疏》:
“贵州开省,原设贵州、黄平等二十卫所,额设屯粮仅共九万二千有奇,一岁所入,不足以供官军半岁之用。”
巡抚江东之《责成川湖协济疏》也云:
“贵州汉少夷多,不得不镇以兵威之重;田少山多,不得不望于邻省之济。”
也就是说,当时占领贵州就是一门赔钱买卖,所以这地儿也不是非得争。相比之下,中原和江南地区土地肥沃,经济发达,成为各大势力争夺的核心。

民族风歌曲《奢香夫人》中提及的响水滩实景。摄影/王纯亮
另外,贵州自古是多民族聚居地,少数民族势力与中原王朝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历代王朝在贵州的治理大多依靠土司制度,即由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统治,向朝廷进贡并接受册封,以换取自治权。这种模式有效降低了中原王朝的治理成本,但也导致中央政权对贵州的直接控制较弱。贵州的多民族聚居特性,也使其成为地方势力与中央政权博弈的焦点。这种情况下,确实也不是非争不可。
从“不争”到“必守”
但这并不意味着贵州毫无军事价值。贵州的地形气候是障碍不假,但利用好了也可以成为一道很好的防御屏障。南宋末年文天祥在南方抗击元军时,曾考虑利用西南山地作为抵抗蒙古铁骑的屏障;明朝平定西南时,贵州的山地同样成为防守与游击战的有利地形。

地形复杂的贵州。来源/CCTV9《航拍中国(第三季)》
因此,贵州虽难以成为大规模进攻的前线,但在防御战中却不失为一块天然的军事要塞。贵州很少被“争”,但始终被“守”。
此外,贵州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其在古代战争中的特殊性。它既不是边陲防线,又不属中原腹地,但作为云贵高原的一部分,贵州称得上是西南地区的锁钥,不仅连接中原与西南边陲,更是通向滇缅的重要通道。
所谓“得贵州者控云南”,中原王朝对贵州的态度,始终与云南绑定。元代为控制云南,曾强行在贵州设立“八番顺元宣慰司”,驻扎军队,还修筑了多条驿道。明代朱元璋派傅友德征伐云南,30万大军过贵州,留下“调北填南”的移民军团。贵州从此成为“滇之喉舌”,被纳入卫所体系,朝廷通过在贵州设立都指挥使司,修建湘黔、滇黔驿道和军事驻防点,使贵州成为控制西南的支点。

贵州的地理位置。来源/天地图
清代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对贵州军事战略地位有更精准地阐述,其云:
“尝考贵州之地,虽偏隅逼窄,然驿道所经,自平溪、清浪而西,回环于西北凡千六百余里。贵阳犹人之有胸腹也,东西诸府卫,犹人之两臂然。守偏桥、铜鼓,以当沅、靖之冲,则沅、靖未敢争也;普安、乌撒,则临滇、粤之冲,则滇、粤不能难也;扼平越、永宁,以扼川、蜀之师,则川、蜀未敢争也,所谓以守则故也。”
可以这样说,在古代中国,经营中原之关键在关中,经营江南之关键在荆益,而经营西南之关键则在贵州。在经营西南边疆的军事行动中,贵州是“冲要之地”,具有战略通道的地位,占据贵州,就等于控制了西南。这样看来,贵州还是挺重要的。
而且,贵州虽非中原王朝的“必争之地”,却是本地土司的生死战场。
统治播州(今遵义)700年的杨氏土司,曾建起亚洲最坚固的山地城堡——海龙屯。2015年海龙屯遗址申遗成功,考古学家发现其城墙厚达6米,箭垛、瓮城、暗道一应俱全,堪称“山地军事建筑奇迹”。掌控黔西北的水西土司,巅峰时期拥兵可达十万,《明史》称其“雄长诸蛮”。吴三桂剿灭水西时,甚至需要动用象兵和火器营。
1600年,播州土司杨应龙反明,万历皇帝调集24万大军,耗银200万两,血战114天攻破海龙屯。此战被视为“万历三大征”之一,凸显了贵州地区的军事重要性。杨应龙凭借山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倒逼明军发明“云梯车”“火龙炮”等特种装备,属实是促进科技发展了。战后贵州设遵义、平越二府,但《明神宗实录》称:“平播之费,十年赋税不能偿。” 明神宗表示:这很难评。

明神宗。来源/台北故宫博物馆
明朝“改土归流”政策实施后,贵州逐渐被纳入全国治理体系,明清之际,贵州成为平定西南叛乱的重要战场。清朝康熙年间“三藩之乱”时,吴三桂势力盘踞西南,贵州成为南明流亡政权的最后据点之一,也说明了贵州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
另外到了明代以后,贵州的丰富矿产资源逐渐得到开发,成为朝廷的重要铜矿、汞矿供应地。除此之外,贵州的特产如茶叶、药材、木材等在古代也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特别是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掌握的木材、草药资源,在明清时期成为军需物资的一部分,贵州也逐步融入全国的经济体系。
从“边缘”到“枢纽”
从历史长河来看,贵州的战略地位经历了从边缘到枢纽的演变。
在春秋战国时期,贵州远离中原战乱,的确并非兵家必争之地。但到了明清时期,随着中央政权对西南边疆的重视、改土归流的推进,贵州成为西南防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在防范缅甸、苗疆和滇藏地区的军事冲突时,贵州地理位置的重要性愈发凸显出来。
到了近现代,贵州的战略地位更是显著提升。贵州的地理环境使其成为红军长征中的重要节点。1935年,红军在贵州境内进行战略转移,利用地形四次突破围剿。遵义会议会址的选址,正是看中贵州“易守难攻”的特性。遵义会议的召开不仅改变了红军的命运,奠定了中国共产党在长征中的方向,也使贵州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贵州遵义会议会址。来源/CCTV9《航拍中国(第三季)》
抗日战争时期,随着日军进攻华东、华南,国民政府迁都重庆,贵州成为抗战大后方的重要战略支撑点,贵阳、遵义等地均成为军事要地。贵州的“险山恶水”变成天然屏障,保护了内迁的工厂、学校。1944年日军发动“黔南事变”,因山高路绝,机械化部队机动困难,最终止步独山。
抗战时期的黔桂铁路更是发挥了重要的运输和保障职能。此外,贵州的溶洞还改造为战备仓库——20世纪60年代建设的“083军工基地”,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2016年,世界最大射电望远镜FAST落户贵州平塘,恰因FAST需要直径500米的巨型“锅形”结构,而贵州喀斯特地貌区天然形成的洼地(如大窝凼)形状与望远镜所需的凹坑高度契合,能够大幅减少人工开挖量。再加上贵州人口密度低,群山环抱,能有效隔绝电磁波影响——当年阻挡军队的天险,如今守护着人们探索宇宙的梦想。

贵州的中国天眼。来源/CCTV9《航拍中国(第三季)》
由此可见,贵州在一些历史时期确实不是兵家争夺的焦点,但其军事地位却不容忽视。贵州虽非传统军事核心地带,却因其特殊的地理与历史条件,在不同时期承担了重要的战略作用。
如今我们站在海龙屯废墟上,还可以看到当年杨应龙刻在石壁上的楹联:
“养马城中,百万雄兵擎日月;海龙屯上,半朝天子镇乾坤。”
这份狂傲,印证了贵州绝非无足轻重——它只是在等待属于它的时代。
参考资料:
[1](明)徐宏祖.徐霞客游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2](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M].北京:中华书局,2005.
[3](民国)刘显世、谷正伦修,任可澄,杨恩元纂:《民国贵州通志(四)》
[4](清)张廷玉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0.
[5](明)李化龙.平播全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6]李中清.中国西南边疆的社会经济:1250-1850[M].林文勋编,秦树才译,人民出版社,2012.
[7]彭恩.明清贵州城镇地理研究(1368-1850)[D].西南大学,2022.
[8]胡振.明代贵州军事地理研究(1368-1644)[D].安徽大学,2018.
国家人文历史原创稿件,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