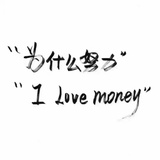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2年东北抗日义勇军实力达到顶峰时,有四支主力部队:马占山部、冯占海部、李社部、苏炳文部。四支主力部队的斗争陆续失利后,有两个大的撤退方向。冯占海部义勇军从东三省撤退到了热河。这支义勇军一直在坚持抗战,1937年又以53军91师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等几路义勇军,则是在斗争失利的情况下,越过国境线退入了苏联的境内。

其中,苏炳文和马占山部义勇军是从海拉尔分乘四列火车撤退苏联的,“第一列车是军政官长和眷属,第二列车是民众,第三四列车是军人,到达西伯利亚的多木斯克”。

苏炳文
12月4日,苏炳文部义勇军“残部和商民、眷属、铁路员工,特、路两警共计四千余人,由满洲里退入苏联”。马占山深恐苏联不许入境,改名方秀然,列为苏炳文部义勇军的总司令部参议,以资掩护。

1932年底,日军大举进攻吉林省勇义军,第10师团为主力分三路向绥芬河、下城子、密山进犯。李杜部义勇军撤出密山转虎林。1月6日、日军占虎林,李率一部退入苏联境内,余部由王德林部收容。日军骑兵第10联队进攻东宁。1月10日,王德林部在东宁抗敌,因弹尽粮绝,王德林部退入苏联国境。李杜、王德林部是从“佳木斯、富锦,经绥芬河,退至苏联的克洛斯那牙城”。

东北抗日义勇军部分人员加入苏联军队
撤退到苏联的义勇军,是分两路回国的:
“一、抗日官兵(包括部分随军家属在内),分批取道新疆回国;二、爱国平民百姓,取道海参崴乘船回国”。
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王德林、张殿九、谢珂、孔宪荣、王尔瞻、金奎璧、吴德林、高峻岭等主要将领及其随行人员,则是1933年4月被苏联方面护送至波兰边境,由欧洲绕道回国。将领们本是准备取道海参崴乘船回国,苏联担心日军劫船,故让他们取道欧洲。马占山、苏炳文、李杜等抗战名将到达上海时,受到社会各界的热情欢迎。

马占山随后在上海向欢迎的人们发表了演说。《马占山将军在上海市欢迎席上的演说》内容:
“东三省为我国东北屏藩,带海襟山,气势雄厚,以农业言,则土地肥饶,物产丰富,尤以黄豆为出口大宗;以矿业言,则已经开采,及已经调查,尚未开采者,几乎无所不有;以森林言,则向作燃料,取之无穷;以交通言,则水陆畅行绾毅欧亚,南满路素号黄金,不过东北之一部耳。如语其全,曷可胜道!日本以区区三岛,尚能定霸称雄,侵占东三省以求达大陆政策之目的,更如虎附翼,经营开辟,势所必至,侵侮数年,其实力之膨胀,安知不什百倍于今日!是我失地一日不收复,即增加一层之困难,况极其野心之所至,将更有不忍言者乎?言念及此,我国人应如何觉悟,如何团结,如何其救国难,如何共图生存,此等重大问题,似非空言所能解决,亦非空言所能达到。而今不图.必更生异日之悔,茫茫前路,焉有津涯”。

海参崴
义勇军之中没有军人身份的人员(例如随军的官吏、学生)和一些官兵的家眷,按照中苏的约定,从海参崴坐“无恙”号轮船回国。为了在海上的安全,防止被日军袭击,“无恙”轮悬挂的是智利的国旗。

大部分义勇军官兵成建制前往了新疆,他们很多人的家誉却是随“无恙”轮到达了天津。不少的一家人从此会分隔两地,再难有重逢之时。

到达新疆的义勇军,利用他们的知识、技术和热情,为新疆的建设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全面抗战开始时,为了接收苏联的抗日援助而紧急在新疆抢修“西北国际大通道”。义勇军官兵又在修筑道路和维护工作上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全民族抗战的最后胜利,也有他们当之无愧的一份功劳!
1945年抗战胜利时,据当时的国内媒体报道,留在新疆的义勇军官兵“多找到了安定的职业,以军政两届为最多”。这十余年中,义勇军老兵们都在思念着东北的故乡。可是抗战胜利后又过了一年,1946年9月,国民党政权才开始登记散居各地的义勇军老兵。

义勇军老兵还乡
又过了8个月,1947年的5月中旬,义勇军老兵们才开始分批踏上还乡之路。义勇军的返乡之路,也是漫长而艰辛的路程,他们乘车和步行结合,从新疆省会迪化到哈密,再从哈密经过甘肃省的肃州(即酒泉)到达兰州。兰州转到陕西省的咸阳后,坐火车沿着陇海铁从徐州坐火车沿着津浦铁路线到南京,再转车沿着京沪铁路线到上海。在跨越到达东北的营口,终于再次登上了东北的土地。
义勇军老兵回家的路线,经过西安、开封、洛阳到徐州,经冠了大半个中国后,义勇军老兵在上海坐轮船,穿过漫漫的东海、黄海、渤海、前后有五批义勇军老兵从新疆返回东北。第一批865人,第二批1608人,第三批280人,第四批1238人,第五批509人。第五批还乡义勇军老兵是1947年9月19日到达东北的,恰好是“九一八”事变过去了整整十六年。第一批老兵之中,有十余位已年届古稀。其中有一位老兵“九一八“事变时七十五岁,此时终于踏上回乡之路时已九十一岁高龄。

胡宗南
第六批还乡义勇军老兵到达陕西省咸阳时,正值标志着解放军在陕甘宁战场开始内线反攻的沙家店战役取得胜利。忙于内战的胡宗南集团无心关注他们的返乡问题,竟直接就地“资遣”了这一批义勇军老兵。满怀着思乡之情的义勇军老兵们,就这样被丢弃在了陕西省。
返回东北的义勇军老兵,却处在被国民党政府遗弃的状态。当时的媒体说,“他们自己不是不知上进的人,要屯垦,据说员额满了无法收容……要就业,没有机会”。贫困的压迫下,一些义勇军老兵,只好去煤矿背煤。其中已在新疆做到了南疆督粮专员、有少将军衔的董时进,辞去了新疆的公职返回东北。可是,他“回来屡次呈请求录用,但是辗转推托,迄无着落,他也投奔了背煤的一条生路”。
堂堂一个国军少将,返回东北尚且如此困难,那些普通的义勇军老兵在返回东北老家,因身份和党派问题遭遇各种不公平的待遇,为义勇军悲壮的斗争历史,在结局增添了悲凉的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