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口那块荒地,长了有十来年的杂草和灌木,是村里出了名的”废地”。黑乎乎的土,一到夏天就裂得像老人的脸,布满深深的沟壑。那地方离村口不远,村民们经过时总是避开走,生怕鞋底粘上那黏糊糊的泥。
王大爷——全名王福顺,是我们村里出了名的”犟脾气”。七十多岁的人了,腰板倒是挺得笔直,走路带着一股风,活像个年轻小伙子。他左腿有点跛,村里人都知道那是他年轻时从拖拉机上摔下来留下的,但他从来不提这事,谁问起来他就摆摆手,说:“早忘了。”其实大家都看见,雨天他就揉那条腿,脸上皱纹都挤到了一块。
十年前,王大爷突然跟村委会提出要承包那块荒地。当时村长老陈笑得前仰后合:“王叔,您老人家是不是脑子糊涂了?那块地连杂草都懒得长,种啥都不行!”
王大爷那天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磨得起了毛边,围着一圈人,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红双喜,抽出一支递给村长,自己也点上一支,深吸一口,看着那块荒地,眼里有光。
“我有办法。”他只说了这么一句。
村里闲人多,三五成群地站在村委会门口看热闹。村长拗不过他,又觉得那地反正也没人要,就让他签了承包合同。
“老王是真糊涂了,那地连农科院的专家都说没法种,他凭啥行?”
“听说他爷爷以前也是个种地的把式,说不定有啥祖传秘方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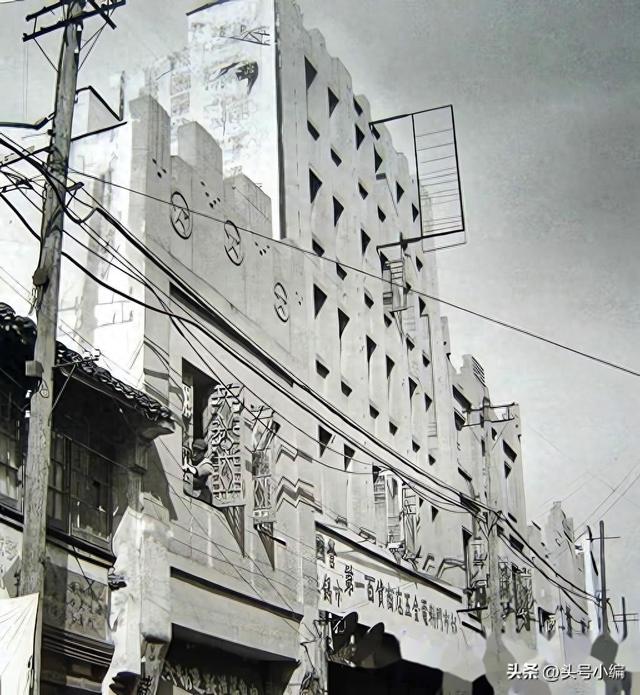
“放屁,他爷爷种的是河边的肥地,跟这死地有啥关系?”
王大爷对这些议论充耳不闻。他每天天不亮就骑着那辆吱嘎作响的老自行车去荒地。车后座绑着锄头、铁锹,车把上挂着一个开了口的军绿色水壶。那水壶磕得坑坑洼洼,但他从不换,我曾问过为什么,他只是摸摸壶身说:“老伴用过的。”再多的话就没有了。
他的老伴五年前走的,肺癌,走得很安详。村里人都知道,这对老两口感情好得没话说。老伴走后,王大爷像变了个人,话更少了,但眼神却更亮了,仿佛把所有的精气神都灌注到了那片荒地里。
刚开始几个月,我路过那块地时常看见王大爷弯着腰,一锹一锹地挖着土,然后掏出个破塑料袋装一点带回家。村里人都偷偷笑话他:“老糊涂了,挖土还挖上瘾了。”
一年过去,荒地还是荒地,只是被王大爷清理出了几块小方田。但种下的玉米只长到半尺高就蔫了,豆子也是黄叶子多过绿的,没一样长得好。村里人看着直摇头,但也没人去劝,都知道王大爷的犟脾气,说了也白说。
但王大爷不放弃。每天天不亮就出门,带着他那个破水壶和一个小布包,里面装着啥没人知道。
第二年,我发现王大爷的方法变了。他把地分成了小格子,每个格子都放着不同的东西。有的洒了草木灰,有的铺了树叶,有的撒了一些不知名的粉末。每个格子旁边还插了根小木棍,上面拴着不同颜色的布条。
“王叔,这是干啥呢?”有一次我实在好奇,路过时问了一句。

王大爷抬起头,脸上的汗水混着泥土,形成一道道黑色的痕迹。他扶了扶腰,眯着眼看了看天,又看看我,笑了笑:“试验呢。”
就这两个字,没有下文。
我注意到他随身带着一个破旧的笔记本,纸页发黄,边角都卷起来了,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字。有一次,他坐在地头休息,翻着那本子,我假装经过,偷偷瞄了一眼,上面画着奇怪的符号和数字,还有一些我看不懂的记录。
“这是啥啊,王叔?”我厚着脸皮问。
王大爷赶紧合上本子,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的口袋,摇摇头:“没啥,老糊涂乱写的。”
第三年,有一小块地居然长出了些不一样的作物,绿油油的,从远处看还挺精神。村里人来了兴趣,几个人结伴去看,发现是些不认识的草。
“王叔,这是啥草?能吃吗?”村里的小刘问。
王大爷正在旁边的地里忙活,闻言抬起头,顶着烈日笑了笑:“药草。”

“值钱吗?”
“不值钱,但治病。”王大爷继续低头干活,不再多言。
那段时间,村里流传说王大爷在种毒品,被村长大声训斥了一顿:“胡说八道!王叔是啥人?老实巴交一辈子,能干那缺德事?”风言风语这才平息下来。
日子一天天过去,王大爷那块地渐渐有了变化。虽然大部分还是贫瘠,但已经有几块小方田种出了玉米和豆子,虽然比起好地里的产量差远了,但总算能有点收成。村里人渐渐也不那么笑话他了,但还是不明白他为啥这么执着。
第五年的时候,出了件怪事。王大爷从地里回来,经过村口的小卖部,破天荒地买了瓶啤酒。他坐在小卖部门口的长凳上,一口气喝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村里几个老头正在打牌,被他吓了一跳。
“老王,咋了?中彩票了?”
王大爷摇摇头,指着远处的荒地:“见好了,有戏了。”
没人明白他在说什么,但从那天起,他更勤快了,连下雨天都要去荒地转悠一圈才安心。有时候晚上村里人还能看见那边亮着微弱的灯光,是王大爷打着手电在那儿忙活。

第七年,村里来了个大学生,说是回乡创业的。看见王大爷的地,很感兴趣,主动跑去搭讪,问他用了什么方法。王大爷难得开口,跟那大学生聊了大半天。后来,那大学生又带了几个同学来,拿着仪器在王大爷的地里取样,还称赞王大爷是”民间科学家”。
村里人这才对王大爷的地另眼相看了。
“听说王大爷在改良土壤呢,有科学道理的。”
“人家读过书的都来取经,咱们别瞎说了。”
王大爷对这些评价依然不置可否,只是每天骑着那辆吱嘎响的自行车,带着他那个破水壶,日复一日地耕耘着那片荒地。
又过了两年,王大爷的地已经有一半能种庄稼了,虽然产量不高,但看着郁郁葱葱的,村里人路过时都会停下来赞叹几句。王大爷的笔记本越来越厚,他偶尔会在地头翻看,嘴角带着笑。
去年冬天,王大爷生了场病,高烧不退,村里几个老头轮流照顾他。我去看他时,发现他床头放着那个笔记本,翻开的一页上写着”碱性土壤改良第三阶段成功”,下面还画了些图表。我不懂那些内容,但能感觉到这对他来说有多重要。
病好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地里看了一圈,然后找到村长,说想申请个什么”土壤改良示范”的项目。村长被他说得一头雾水,但看他这么认真,就帮他在县里打了招呼。

没想到,这一打招呼竟引来了天大的变化。
今年春天,县农业局来人了,带着仪器和设备,在王大爷的地里到处取样。王大爷在一旁看着,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了。
“这老头神了,”农业局的小伙子对我说,“他这是在做土壤改良试验呢,而且方法特别科学,跟现在国际上的一些做法不谋而合。”
我一脸迷糊:“就是让死地能种庄稼呗?”
小伙子笑了:“远不止这么简单。你们这一片的土壤都是重碱地,全国有上千万亩这样的地,几乎都是废地。如果他的方法真行,那可是能造福很多地方啊!”
一个月后,省农科院的专家组来了,七八个人,带着各种设备,在王大爷的地里忙活了整整三天。最后一天下午,我正好路过,看见一个白头发的老专家拿着报告,激动得握住王大爷的手直摇,然后竟然在地头跪下来,用手抓了一把土,放在鼻子前闻了闻,眼睛湿润了。
“王老先生,您这十年没白费啊!您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老专家激动地问。
王大爷不好意思地摸摸脑袋:“就是小时候听我爷爷讲过,说这地是离了魂的地,得一点点给它喂回来。我就琢磨着,一样一样试。”

后来我才知道,王大爷这十年来一直在做的,是通过特定植物的轮作、有机质添加和微生物培养,让贫瘠的碱性土壤逐渐恢复生机。他那个破旧的笔记本里,记录的是每一块试验田的变化和处理方法,密密麻麻写了十年。
最让专家们震惊的是,王大爷无意中培养出了一种能在高碱土中生存的微生物菌群,这对全国乃至世界上的碱性土壤改良都有重大意义。
“您这个发现,保守估计能让全国几百万亩废地重获新生啊!”白发专家声音都颤抖了。
王大爷站在地头,看着自己的荒地,眼睛里有光,但没有得意,只是轻轻地说:“我老伴生前总说,人活一辈子,得干点有用的事。”
他说这话时,夕阳正好洒在他身上,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坚持十年如一日地耕耘这片荒地。那不仅是为了证明自己,更是为了完成一个承诺,一个对已故老伴的承诺。
消息很快传遍了村里。村长立刻召开了村民大会,宣布王大爷的事迹,还说省里要来人表彰他,说不定还能上电视呢。
王大爷坐在台下,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捧着那个破水壶,脸上的皱纹里盛满了阳光。当大家起立鼓掌时,我看见他悄悄擦了擦眼角。
会后,我特意等在村委会门口,想跟王大爷聊聊。等人都散了,他慢悠悠地走出来,看见我,笑了笑。

“王叔,恭喜啊!”我真心地说。
他摆摆手:“有啥恭喜的,就是个老把式。”
“那个……你为啥选中了那块地啊?明明知道那么难种。”我终于问出了这个困扰我多年的问题。
王大爷沉默了一会,看着远处的荒地,轻声说:“那是我跟老伴第一次见面的地方。”
我愣住了。
“五十多年前,那地还不是荒地,是村里最好的一块水田。我去割稻子,看见一个姑娘在田埂上摘野花,一抬头,四目相对,就……就这么定了。”
他停顿了一下,摸了摸那个破水壶,“后来那地让化工厂的废水给毁了,成了荒地。我老伴临走前,摸着我的手说,希望能再看一眼当年的好田。我答应她,要把地恢复原样。”
我的眼眶湿润了,说不出话来。

“其实我就是个老农民,没啥文化,但我知道,任何事只要用心去做,总能找到办法。这十年,我每天跟这地说话,好像是在跟老伴说话。”
夕阳下,王大爷的身影显得那么高大。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骑上那辆吱嘎响的自行车,慢慢地向家骑去。
车后座上,那个破水壶在余晖中闪着光。我这才注意到,壶身上刻着两个字:永福。
那是王大爷老伴的名字。
如今,王大爷的故事已经传遍了整个县城。县电视台来采访了他,省里的领导也来看望他,说要把他的技术推广到全省甚至全国的碱性土地上去。更让村里人震惊的是,有个国际农业组织也派人来考察,说王大爷的方法对全球荒漠化治理都有启发意义。
而王大爷依然每天早出晚归,骑着那辆老自行车,带着那个破水壶,一如既往地照料着他的土地。只是现在,每天跟着他学习的人多了起来。
上周,村委会门前竖起了一块牌子:碱性土壤改良示范基地。
牌子下面的小字写着:王福顺劳模工作室。
前天早上,我又路过那片地,看见王大爷正蹲在地头,教几个年轻人识别土壤。晨光中,那个破水壶依然挂在自行车把上,闪闪发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