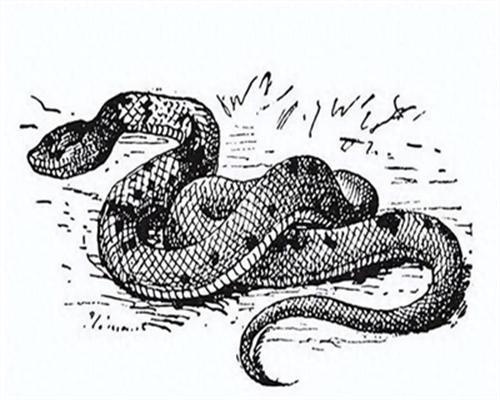"啪!"戒尺拍在紫檀木书案上,震得铜烛台里的火苗儿直晃悠。我攥着《礼记》的手心全是汗,纸页上"大学之道"四个字早糊成了黑疙瘩。
"张举人,您这书念得可够热闹。"东家王老爷倚着雕花门框,狐裘领子沾着外头飘进来的雪粒子,"三更半夜的,我这宅子都快让您敲出安塞腰鼓的动静了。"
我慌忙起身作揖,袖口扫翻了砚台。墨汁顺着《中庸》书脊往下淌,活像条黑蛇钻进了青砖缝里。这王老爷是京城有名的皇商,宅子九进九出,光下人住的偏院就比我家祖宅阔气。可自打半月前接了这份西席差事,我就没睡过囫囵觉——每到子时,后园方向就传来丝竹声,混着女子银铃般的笑。
"对不住老爷,学生……学生听见后头有动静。"我支支吾吾指着西厢房。月亮正悬在飞檐角兽上,照得窗纸上的剪影忽大忽小,像是有人在跳舞。
王老爷脸色忽然阴沉,像六月天吞了秤砣。他甩袖掩上门,铜锁"咔嗒"咬住门闩:"张举人,这宅子有些规矩,您最好还是装聋作哑。"说罢扭头就走,袍角带起的风扑灭了半桌蜡烛。
我盯着那扇紧闭的雕花门,喉咙里像堵了团棉花。打更的梆子声漏进来,已经三更天了。忽然,西厢房传来琵琶弦断的声音,紧接着是瓷器碎裂的脆响。我再也按捺不住,抓起案上镇纸就往门外冲。
月亮钻进云层时,我正踩着湿滑的青砖往西院摸。后园子种着大片湘妃竹,夜风一吹沙沙作响,活像上百个女人在低声啜泣。忽然,竹影深处亮起两点红烛,映出个婀娜的身影。
"是张公子吧?"那女子转身时,头上的金步摇碰出细碎响动,"奴家等您许久了。"
我浑身一激灵,烛光照得她眉眼如画,唇角一颗朱砂痣艳得像滴血。更奇的是她穿着月白襦裙,外头却罩着件茜素红比甲——这季节穿夹袄都嫌冷,她竟像不觉着寒似的。
"姑娘是……"话没说完,她忽然掩口轻笑,腕间银镯撞得叮当响:"公子连日苦读,倒不如来陪奴家饮几杯暖酒。"说着拎起酒壶,琥珀色的液体汩汩流进白玉杯。
酒香钻入鼻腔的刹那,我浑身骨头都轻了三两。再看那女子,眼波流转间竟带着三分狐媚,偏生又混着七分仙气。恍惚间已接过酒杯,液体入口绵软,却辣得直冲天灵盖。

"这是西域传来的葡萄酒。"她指尖划过我掌心,"能照见人心里的念想。"说罢突然凑近,吐气如兰:"公子想要什么?"
我踉跄后退,后背撞上竹节。月光从云缝里漏下来,照见她裙裾上绣的并不是寻常花鸟,而是密密麻麻的佛经偈语。正要细看,她忽然旋身起舞,水袖甩出满园梅香。
"这宅子底下埋着好东西。"她边舞边唱,"前朝宰相藏的《推背图》,西域高僧的舍利子,还有……"忽然足尖一点,人已飘至我跟前,"还有公子想要的功名。"
我猛地惊醒,发现自己还坐在书案前。烛泪在铜盘里凝成珊瑚状,案头《礼记》摊在"修身齐家"那一章。难道方才都是南柯一梦?可袖中分明揣着个冰凉的物件——掏出来竟是枚羊脂玉牌,刻着"缘定三生"四个字。
次日晌午,我被前院吵嚷声惊动。王老爷的独子王少爷正揪着个丫鬟用鞭子抽,那丫鬟的惨叫声惊飞了檐下的家雀儿。
"偷老子玉佩的小!"王少爷鞭子甩得噼啪响,玉佩碎片在雪地里闪着冷光。我认得那玉佩,是前日老爷赏他的成年礼,据说能辟邪。
"且慢!"我冲上前去抓住鞭梢,"王少爷,这丫鬟……"话未说完,忽见那丫鬟脖颈处有道青紫勒痕,形状像极了昨夜女子裙上的佛经纹路。
王少爷甩开我,肥脸上堆着横肉:"张举人还是少管闲事,这宅子死的人,比您教的书还多。"说罢拖着丫鬟就往柴房去,雪地上拖出蜿蜒的血印子。
入夜,我翻着《礼记》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玉牌在烛火下泛着幽光,突然,西厢房又传来琵琶声。这次还混着女子娇笑:"张公子,您再不来,奴家可要跟那舍利子说话了。"
我攥着玉牌冲出门,夜风卷着雪粒子往领口里钻。穿过回廊时,忽见王少爷屋里的灯还亮着,窗纸上映出两个纠缠的人影。正要细看,后颈突然挨了闷棍。

再睁眼时,人已在西厢房。琵琶声停了,红烛烧得只剩半寸。那女子斜倚在贵妃榻上,指尖绕着缕青丝:"公子可知,这宅子为何总有冤魂?"
我摸着后颈的肿块,瞥见她身后博古架上摆着个青铜鼎,鼎纹竟与玉牌上的偈语如出一辙。正要开口,她突然起身,水袖拂过案头,露出半截泛黄的书卷——正是昨夜梦中的《推背图》。
我冲出门,正撞见王少爷踉跄跑来,裤脚沾满泥浆。他肥脸煞白,指着柴房方向直哆嗦:"鬼!那丫鬟变成鬼了!"
此时柴房方向火光冲天,浓烟中隐约可见个白衣身影在屋顶起舞。我掏出玉牌,月光下"缘定三生"四个字突然渗出血珠,顺着纹路往下淌。
"举人的功名,皇商的富贵。"女子不知何时出现在身后,发间金步摇在火光中闪烁,"都是拿人命换的。"她忽然抓住我的手,冰凉的指尖刺入皮肉:"公子若想破局……"
话音未落,王老爷带着家丁举着火把冲来。他看见女子的瞬间,手中烛台"哐当"坠地:"翠……翠云?"
女子回眸一笑,百媚千娇。王老爷却像见了鬼,跌跌撞撞往后退:"你……你不是二十年前就……"话音未落,女子水袖轻扬,满园湘妃竹突然齐刷刷折断,露出底下森森白骨。
我举着火把凑近,白骨手腕上套着个银镯,镯内刻着"王门李氏"四个字。王老爷突然跪倒在地,肥硕的身躯抖如筛糠:"造孽啊!造孽啊!"
原来二十年前,王老爷为夺祖产,毒杀发妻李氏。李氏咽气前死死攥着银镯,诅咒王家世代不得安宁。自那以后,宅子里每夜都有女子哭声,下人们都说看见穿月白襦裙的鬼魂。

"张公子,您想要的功名。"女子忽然将《推背图》塞进我怀中,"就在这书里。"她转身望向火光冲天的柴房,"至于那舍利子……"话音未落,王少爷突然发出非人惨叫,众人回头时,只见他七窍流血,手里攥着半块玉佩。
雪越下越大,覆盖了满园白骨。女子站在火场中央,月白襦裙被燎出焦痕却毫发无伤。她忽然转头对我嫣然一笑:"缘分已尽。"话音未落,整个人突然化作漫天流萤,那枚羊脂玉牌"啪"地摔碎在青石板上。
次日清晨,我背着书箱离开王家大宅。城门处贴着通缉告示,画着王老爷父子的画像。卖油饼的老汉嘬着牙花子:"作孽哟,听说王家宅子底下挖出上百具尸骨,都是当年修宅子时埋的。"
我摸了摸怀中的《推背图》,书页间夹着片焦黑的湘妃竹叶。忽然,背后传来车马声,回头却见个穿茜素红比甲的女子坐在轿帘后,腕间银镯碰出清脆响动。她对我眨了眨眼,轿帘便放下了。
雪地上,昨夜捡的玉牌碎片突然发烫。我摊开掌心,碎片竟自行拼成个完整的圆,中间多出个"缘"字。远处传来晨钟暮鼓,混着卖花郎的吆喝:"杏花咧——新鲜的杏花咧——"
"这位公子,您的书箱硌着奴家的轿子了。"轿帘忽然掀起,露出半张涂着胭脂的脸。卖花郎的铜铃铛"叮当"一声,惊得我后退半步,怀中的《推背图》差点掉在地上。
轿夫们吆喝着让路,轿子却稳稳停在我跟前。女子伸手拈走我肩头的杏花瓣:"张公子,可知京城往西三十里有个破庙?"她指尖带着梅香,说话间轿帘上绣的并蒂莲突然活过来似的,花瓣簌簌颤动。
我咽了口唾沫,想起昨夜玉牌上的"缘"字。正待开口,城门处忽然传来快马嘶鸣。官差举着"刑部"灯笼纵马而来,马背上驮着的正是王老爷父子,两人被麻绳捆成粽子,嘴里塞着破布。

"让让!刑部办案!"官差鞭子甩得噼啪响。我贴着墙根,看见王少爷裤裆湿了一片,黄汤顺着马鞍往下淌。轿中女子忽然轻笑:"公子瞧这报应,可比唱戏的还热闹。"
轿子重新起行时,她丢出个油纸包:"杏花糕,吃了能清心。"我接住时,轿帘已放下,只听得银铃般的笑声混着马蹄声往西去了。
破庙里供着尊无头菩萨,香案上积着半尺厚的灰。我按照女子所说,用玉牌碎片在菩萨座下挖了三尺深,果然挖出个铜匣。匣中除了《推背图》残卷,还有本泛黄的《金刚经》,经书扉页写着"李氏翠云"四个字,墨迹被泪痕晕成黑蝴蝶。
"张公子,可算找着您了。"庙门外忽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我慌忙合上匣子,却见个穿灰布袄的老汉拄着拐杖进来,正是王家柴房烧火的老王头。
他脸上带着新结的痂,作揖时露出手腕上的青紫勒痕——与昨夜丫鬟颈间痕迹一模一样。"公子快逃吧!"老汉压低声音,"王家在刑部有人,老爷少爷被抓前,早派人去请五台山的高僧了。"
我摸着怀中的《金刚经》,忽然想起女子说的"舍利子":"老人家可知,这宅子底下埋的……"话未说完,破庙外突然传来木鱼声。三个穿袈裟的僧人走进庙门,为首的老僧须眉皆白,手中禅杖竟用玄铁打成,杖头嵌着九颗骷髅珠。
"施主,把东西交出来吧。"老僧双目紧闭,木鱼却敲得震天响,"那妖女用邪术惑人,王施主已请贫僧用'大日如来咒'超度她。"
我退到香案旁,手指触到《推背图》残卷。忽然想起书中"金乌西坠,玉兔东升"的卦象,对应卦辞竟是"阴盛阳衰,邪不压正"。外头木鱼声越来越急,老僧的袈裟无风自动,骷髅珠发出鬼哭般的呜咽。
"施主莫怕,老衲来助你。"老王头突然抄起火钳,将香案上的残烛戳进老僧后颈。另外两个僧人刚要上前,破庙梁柱突然齐刷刷折断,露出房梁上贴着的黄符——正是昨夜女子水袖上的佛经偈语。

"快走!"老王头拉着我就往密道钻。地道里阴风阵阵,墙壁渗着血水,越往里走越听见女子哭泣声。转过三个弯,眼前突然出现口古井,井沿刻着"李氏冤魂,永镇于此"。
井底传来铁链晃动声,接着是女子凄厉的尖叫:"王家害我全家八十三口,我要他们血债血偿!"我举着火折子往井下照,只见密密麻麻的骷髅叠成小山,最上头那具骷髅手腕套着银镯,镯内"王门李氏"四个字闪着幽光。
"公子,把玉牌扔下来。"老王头忽然跪地磕头,"老奴就是这镯子的主人,当年被王老爷毒杀后,魂魄被困在宅子里二十年。那妖女……不,那仙子,是菩萨派来点化您的。"
我掏出玉牌,碎片突然合成整块,井底骷髅竟发出叹息:"多谢公子。这往生井能通阴阳,王家父子已被投入井中,公子快带着证据去衙门……"
话音未落,井口突然垂下条金丝绳。我拽着绳子往上爬,手心被勒出血痕。待到井口,却见老王头已化作青烟,只剩下火钳插在井沿。
三日后,京城菜市口围满百姓。王老爷父子戴着木枷,身后跟着八口棺材,里头装着从往生井捞出的尸骨。刽子手鬼头刀落下的刹那,我忽然看见人群里的茜素红比甲闪过。
"张公子,可悟了?"女子声音在耳畔响起。我转头时,她已坐在茶楼栏杆上,晃着腿吃杏花糕。楼下说书人正拍到惊堂木:"列位看官,这善恶到头终有报,举头三尺有神明……"
女子忽然纵身跃下,众人惊呼声中,她却稳稳落在我跟前。发间金步摇撞出脆响:"公子可知,那《推背图》最后一象说的什么?"她指尖在我掌心画圈,"'阴阳混沌,缘起缘灭'。这缘分啊……"

我握紧掌心的《金刚经》,经书扉页突然显现出新写的偈语:"功名如粪土,仁义值千金。莫道鬼神远,举头有神明。"抬头再看女子,她已化作漫天流萤,绕着刑部衙门的鸣冤鼓盘旋。
"举人啊举人,你可知这故事最妙在何处?"说书人扇子"刷"地展开,"那妖女不是妖,是菩萨化身;那玉牌不是宝,是照妖镜。王家的罪孽,早被刻在《推背图》里,就等个心怀正气的人来破局!"
茶楼外飘起杏花雨,我摸着怀中的玉牌,忽然想起破庙里无头菩萨座下的泥土——那泥土里,分明混着舍利子的金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