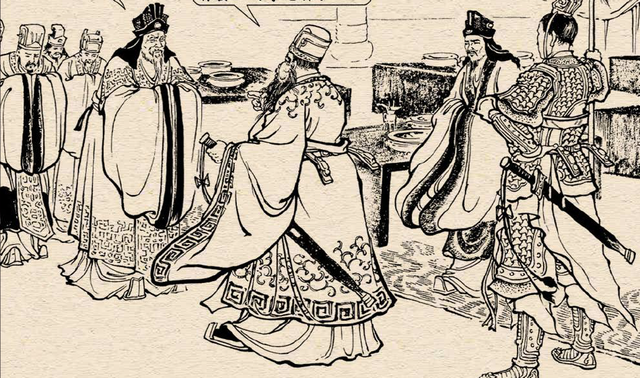“泾原兵变”堪称历史上最滑稽的一起事件,唐德宗好心请士兵们搓一顿,却不料兵哥哥们因为吃得不爽,一怒之下这群人竟然攻克长安、占领皇宫,把皇帝打成了流浪狗。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一场浩大的“盛宴”在长安北郊举行,京兆尹王栩奉唐德宗的命令,在这里设宴招待即将奔赴淮西战场的泾原节度使五千将士。
原来是“壮行酒”,既然如此,咋就喝急眼了呢?一群酒蒙子呀?
这事儿要怪就得怪王栩不上心,酒宴的档次弄得太低,甚至都不能算酒席,就一些粗茶淡饭,外加几碗“断头酒”。
士兵们心凉了,也怒了,有人抱怨说:我们即将为国赴死,朝廷本该有所犒赏。可如今朝廷一毛不拔,还弄这种猪食糊弄我们。我们抛弃父母妻儿,慷慨捐躯,朝廷却让我们饿着肚子上战场,有这个道理吗?既然朝廷不把我们当人,听说皇宫里宝物堆积如山,咱为什么不自取?

这句话如同往油库里扔了一团火,顿时烈焰冲天。于是兵哥哥们集体调转枪口,杀奔长安。
得到报信,唐德宗懵了:连叛军的面都没见着,负责平叛的“国军”又反了,朕这脸被打得啪啪响啊。赶紧送去二十车金银布帛,只求泾源兵大爷们别闹了……
大臣们一脸慌张:陛下,来不及了,泾原乱兵已经攻破长安,杀奔皇宫来了。
唐德宗大惊失色:什么?城池丢了?神策军呢?干嘛不抵抗?吃干饭的呀?
大臣们一噘嘴:神策军?唉,早就烂啦,天下恐怕就您不知道,神策军长期吃空饷,充斥着一群无赖子弟。集合号令响起,您猜来了多少人?二百人不到,抵抗个球?
天哪,好几万的神策军,等到用人之际就来了二百人!唐德宗差点哭了,朕养着你们还不如养一条狗管用呢。

说什么都晚了,唐德宗被大臣们拥着,仓皇逃离长安,成了继唐玄宗、唐代宗之后的第三位大唐失国皇帝。
泾源兵不费吹灰之力就占领了大唐帝国的心脏,一顿狂风暴雨般的劫掠,塞得脑满肠肥,集中了帝国财富的琼林、大盈两大库被洗劫一空。
如果到此为止,这事儿也就是一粒小芝麻,不值一提。钱嘛,身外之物,威胁不到江山社稷。问题就在士兵们冷静下来后,也学会了“思考天下”。
等兵哥哥们实现了“小目标”后竟然有点不知所措了:就为这点钱咱就成了叛军,国家的罪人,值吗?下一步咋弄呢?毕竟打跑皇帝这个罪可不是闹着玩的。

兵哥哥们天真,但老政客们很成熟,有个叫源休的御史中丞没来得及逃离长安,这伙计正因为朝廷对他“赏赐不丰”恨得咬牙切齿呢,这会儿终于逮这机会了。于是源休联合泾原节度使姚令言,导演一出惊天大戏,并将“泾原兵变”推向了高潮。
他们的大戏就是推举中书令、太尉朱泚为帝,建立新王朝!
朱泚这个人原本是幽州节度使,在河朔藩镇拿捏皇帝的那个年代,他却带头忠于朝廷,被世人奉为“感动大唐”的忠义代表。
后来朱泚的弟弟幽州节度使朱涛谋反,并联络朱泚企图里应外合。朱泚虽然不知情,但唐德宗为防万一,将朱泚明升暗降,罢免了兵权。
朱泚“一腔热血”被浇了粪水,把唐德宗恨了大窟窿。“泾原兵变”时,朱泚本想跟着唐德宗一起逃跑,却不料晚了一步,没跑了,被堵在家里了。

朱泚还有一个经历,他曾经短暂担任过泾原节度使,是这群“孙猴子”的老领导。
有老交情,又有源休的撺掇,再加上原本就对唐德宗一肚子怨气,以及皇位的诱惑力,于是曾经的忠义楷模变了脸:既然天意如此,洒家就不客气了,从此天下就不叫“唐”了,也不姓“李”了,改做“秦”,老子称帝了,哈哈……
一顿酒闹出的风波,竟然演变为重大的政治事件,大唐帝国被推向破产的边缘。
这事儿怎么看都有点滑稽,有点不可思议。军队是最讲纪律性的一个团队,怎么可能因为招待不周而捅破天?这里面有没有隐藏的玄机呢?
还真有,下面咱就说一说“泾原兵变”幕后的一些故事。
首先,我们要剔除阴谋论,“泾原兵变”绝不是某个人精心策划的结果,而是一个偶发事件。

从“谁得利谁就是凶手”的逻辑来看,似乎朱泚、姚令言、源休这些人是幕后的黑手,不过这个推论有点站不住脚。
事件发生时,姚令言因为阻止士兵,差点遇害。
朱泚是在逃跑过程中被拦截的,当姚令言等人提出拥戴朱泚时,朱泚也经历了一个心理变化过程,而不是一上来就要称帝。这个过程很符合一个“被彩票砸中,从不相信到慢慢接受,进而疯狂”的过程。
源休出身名门,跟朱泚、姚令言是两个生活圈,他们之间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交集。后来,源休抛弃遮羞布,主动投靠,靠不要脸的精神才挤进了朱泚的“核心圈”。
三个核心人物没有交集,也没有利益共同点,怎么可能策划这么大的一件事?

事实上,“泾原兵变”中如果不是神策军“现大眼”,长安很难被攻破,精心策划的事件怎么可能将希望寄托在偶然事件上?
可问题是,如果说这是一件偶发事件,实在有点匪夷所思,就算朝廷抠门,也不至于群殴皇帝吧?
这就要涉及“泾原兵变”背后的第二个话题:泾原兵马的特殊经历表明,这支被命运歧视的虎狼之师需要一个出气口,泾原兵变就是那个口子。
“泾原”是指“泾州和原州的合称”,可是泾原兵马的班底却不是这两州的人,而是安西、北庭都护府的兵马,第一任节度使就是威名赫赫的“大唐第一先锋”李嗣业。
“安史之乱”爆发后,李嗣业奉命率领这支队伍勤王,由此拉开了他们可歌可泣的奋斗史。他们先后追随郭子仪、李光弼、仆固怀恩,参加了全部平叛战争,并在收复长安、洛阳的战斗中屡立奇功。

李嗣业为人质朴,作战勇猛,忠贞爱国,并给这支队伍注入了骁勇的军魂。遗憾的是,在“相州会战”中李嗣业壮烈牺牲,丢下了与他同甘共苦的兄弟们。
与其他的藩镇兵马不同,这支队伍是“行营节度使”,他们的根大西北,由此他们就像浮萍一样漂泊,四处征战,四海为家。
我们都知道,藩镇的威力就在于有“根据地”,像土皇帝一样治民治病,而安西、北庭兵马却吃了大亏。每次作战他们都承担最艰辛的任务,可是却不能像其他藩镇一样享受成果。
唐朝藩镇为什么难以根除?很简单,藩镇多香啊,天高皇帝远,并逐渐形成以藩镇将领为核心的地方豪族势力。但这一切都跟这支队伍无关,因此士兵们不可能没有积怨。

当怨气逐渐积压在一支彪悍的队伍中时,您肯定猜得出来会发生什么。没错,兵变!于是他们成了一支经常爆发“火山喷发”事件的刺头部队,节度使遇害也屡见不鲜。
后来,唐代宗将这支队伍安置在泾州、原州,从那以后他们才有了固定的治所和名称,但“兵变”的老传统也被延续下来。
藩镇本来就跟朝廷若即若离,泾原兵马又是一个火药桶,朝廷长期对待他们不公,随时爆发一点都不意外。
“泾原兵变”深层次的原因,跟朝廷与藩镇实力此消彼长有很大关系,用通俗的话来讲就是“落魄的凤凰不如鸡”。
安史之乱虽然平定了,但唐代宗却按下葫芦起了瓢,一个安禄山倒下,无数个安禄山又起来了。唐德宗即位后决定改变局面,于是拉开了削藩之战。

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本来是奉命平叛的,却不料这家伙竟然比河朔藩镇还要嚣张,人家是“五国相王”,他干脆称帝了。
朝廷集中火力攻打李希烈,却不料一败再败,无奈之下只好祭出“钢刀”泾原兵马。
唐代宗当初放任藩镇,唐德宗受挫于藩镇,其实都是一个原因,那就是大唐的中央军废了,打不过藩镇了。
泾原兵马为什么敢因为一顿饭作乱?还不是神策军太面嘛。他们为什么能轻松攻入皇宫?还不是神策军太渣嘛。

事实上,大唐之所以能跟藩镇“和平共处”百余年,就是因为后来唐德宗痛定思痛,又将兵权交给了宦官,重建了神策军,腰杆子又硬起来了。后来大唐为什么亡了?原因也很简单,唐昭宗意气用事,非要跟李克用、杨复恭、李茂贞火并,拼光了神策军,于是朱温晃着膀子来打包。
总之,“泾原兵变”看似偶发,其实是有深层原因的,所谓没病不死人,大唐重病缠身,兵哥哥们吃得不如意就掀桌子,一点也不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