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里是专栏“写在理论边上”的第二篇更新。顾名思义,“写在理论边上”注目理论边上的体验,也看到理论之外的困惑。而在它们之间,我们还有更多思考。
今天的文章关于动物伦理。身边的养宠人群越来越多,将动物圈养在狭小的公寓房里,穿上人类喜爱的衣服,吃着工业生产的粮食,这真的是爱护动物吗?但如此质疑又显得不合时宜,在现代化的都市中,除了成为宠物,动物们已没有更多容身之地。大多数人其实既不饲养宠物,也不关心动物议题——漠不关心,已经是人类最大的仁慈。
但动物议题不可能消失。归根结底,它们与我们共享同一个地球。如果留心,生活中其实充满动物伦理:你有怎样的饮食习惯?你是肉食者还是素食者?你如何看待“吃狗肉”问题?你使用皮包皮具制品吗?你使用经动物测试的护肤品、药品吗?你喜欢逛动物园吗?……
这些问题错综复杂, 难以给出简单的答案。每个人身处的立场,体验的历史,生长的环境,关注的重点等等不同,都会导向不同的观点。每次讨论相关议题,总是引发多方争论。但在给“对方辩友”贴上“圣母”或“野蛮”的标签之前,我们有更多话可以说。
在本文作者看来,对待动物伦理的立场,也往往与女性与环保等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个女性,她感到与动物、自然的相似处境,这些思考在理论研究中有诸多回响。但还有更多缝隙,我们只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填补。
对“写在理论边上”此前文章或对此专栏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阅读。
(海报设计:刘晓斐)
 撰文|张婷
撰文|张婷  从“动物”到“宠物”
从“动物”到“宠物” 大概每个人都有一段属于自己跟动物的“微观史”。
小时候我在农村,村民对待动物相当粗放,并没有“宠物”概念。上世纪90年代,隐约记得村子里有耕地的牛,拉磨的驴,随着农业机械化,牛、驴在华北农村很少再见到。猫狗倒是常见,养狗为了看门护院,养猫为了抓老鼠。也有村民喜欢饲猪养鸡,鸡满院子溜达,厉害的还能扑腾到墙头晒太阳,等到年节就宰杀成了年菜。乡村的动物像是土地上长出来的,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它们跟人类共享一片土地。小时候总觉得在农村,人可怜,动物也可怜。动物很少得到细致照料,更谈不上关爱,它们的一生劳碌而受限——跟乡野的人一样,我们都活得如同草莽。
长大一些,我进入城市生活,惊讶于城里人对待“宠物”的方式。猫狗会被取一个“洋气”的名字,穿上漂亮衣服,被圈养在钢筋水泥的楼房里,饲养宠物的人会以“爸妈”自称。这些宠物们往往有着不同于乡野动物的昂贵血统,它们由人工选择、定向繁育。城里人对待动物很精细,它们能吃上昂贵的粮食,拥有丰富的玩具。

《一条狗的使命》电影剧照。
但在城市生活日久,才发现这里对待动物的方式隐藏着种类繁多的残酷。人工培育的品种常带有基因病:比如法斗犬可能罹患退行性脊髓病导致瘫痪;折耳猫容易骨骼发育异常,苏格兰折耳猫的基因缺陷率甚至高达90%;无毛猫面临更高的皮肤病风险......但对人类来说,折耳更可爱,无毛不掉毛,法斗很呆萌,它们受到养宠人群的追捧,被不断地定向繁殖、基因改造。而养宠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弃养:搬家、结婚、怀孕、生病、过敏、不喜欢……弃养时能为宠物们寻找一个靠谱下家,已实属大发慈悲。依靠萌、可爱博得人类青睐,与人类共同生活的宠物们,赤裸裸地面临“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的困境。它们的命运,无非倚赖人类的“良心”。
如果说使用动物是人类的需要,那么乐观地讲,亲近动物可能也是人类的本能。如同看到河流渴望用手去触碰,面对高山渴望用脚去攀登,人也是如此渴望其他物种。被贩卖和定制的“都市生活方式”层出不穷,但总有人饲养动物,照料植物。如今我也成了养宠的“城里人”。7年以前,我领养了一只流浪的狸花猫,唤作咖喱。咖喱调皮好动,所到之处窗帘、沙发遍体鳞伤,杯子粉身碎骨。它喜欢在洒满阳光的午后昏睡,毛茸茸的脑袋靠着我的胳膊,爪子搭着我的腿。看着它沉睡的侧脸,的确让人忍不住感慨“这跟亲生的有什么区别”。

熟睡的咖喱,作者供图。
咖喱不是我拥有的第一只“宠物”,我也不是一直如此“有爱”。我当然是人类征用动物,杀害动物,奴役动物,使用动物,食用动物的漫长而残酷历史中的一分子。
大约是10岁的暑假,我跟妈妈要求想养一只小狗。我妈带我去了当地的狗市场,买回来一只白色的小狗。它对人类有着无条件的信任,任何时候你将目光投向它,它都以一副“我准备好了”的姿势奔跑过来。记忆中,我跟它相处甚欢,度过了一段蜜月期。但后来课业负担加重,与班上朋友的爱恨纠葛,爸妈的争吵......一切属于人类的琐事轮番上演,我与小狗的相处时间变少了很多。那只小狗习惯在家里随地拉尿,我和家里人似乎也没想办法去训练它,至少没穷尽一切办法。在它又一次尿在我妈的枕头上之后,它被转手送给了一个亲戚。自那之后,我就忘记了曾有过这样一只天真活泼的小狗。直到很多年后,我来到亲戚家,发现它一直被拴在院里的柱子上,活动半径只有方圆半米,光亮的白色毛发变成了灰黄色,打结纠缠,旁边是它的排泄物。它就那样度过了余生,没有再自由走动过一天。就算它去田野流浪,可能都有更快乐的一生。而我对此无知无觉。
更小的时候,我已记不清那是谁的狗,它被一根粗粗的铁链拴在路旁的窝棚边,窝棚里是左邻右舍堆积的杂物。人们经过扔点剩菜剩饭,它就那么长大了。来来往往,没有人正眼看过它。多年后,我妈去给它喂饭,才发现它的脖子已皮开肉绽,血肉模糊地露在外面。它从小狗变成大狗,脖子在变粗,却没有人去松一松它脖子上的铁圈。它该有多疼,但它从没有因为疼痛叫过。它一直恪守看门狗的职责,只有外来人靠近时会汪汪叫着发出警报,危险解除就悄无声息地趴下去。这只狗最终去了哪里,项圈有没有被打开,我已没什么记忆。只记得它是一只黄黑色的狗,耳朵很大,眼睛黑亮。
一个安静的午后,看着咖喱四脚朝天地沉睡,我终于想到了它们。我想起了那只黄狗曾经用黑亮的眼睛注视着我,想起它们曾经怎样信任人类,而又是怎样被人类辱没。眼泪一下子涌出来,家人从厨房走出来,诧异地问我怎么回事。我说就是想到自己的残忍,人类的残忍。说完,又觉得羞耻。这是一个怎样根深蒂固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现实,人竟会因为对动物产生了悲悯而感到羞耻。
 肉食者的动物伦理
肉食者的动物伦理 或许那羞耻里也掺杂着内疚。对于生命中出现的这些动物,我或者家人、邻居,并没有人蓄意虐待它们,人只是无知无觉地忙于自己的生活,就足以给它们带来致命伤害。以如今的标准看待,不论是否故意,让动物受伤或者不人道地养育,也是虐待。回看过去二三十年间人类对待动物的态度,是有“进步的”,以往村落间常有狗肉饭馆,如今已很少见到。小时喂养猫狗只是管饱,如今有供给宠物的各种保健品,还有弥补圈养限制的丰容玩具(丰富动物生活趣味,模拟野外需求的玩具)。但觉察得越多,也越容易发现还远远不够。
我曾经在清晨的马路上看到被碾碎在路边的猫,清洁工把它扫起跟落叶放在一起。我问阿姨要回那只残破的小猫,想着至少把它埋葬。阿姨说像这样被撞死在路边的动物太多太多,根本埋不过来啊,更不用说还有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我还是把它埋在了小区里的一棵树下,之后的很多年,每次经过那棵树,我都感到无法呼吸,只能快步低头走过。
城市化孕育了繁荣的工业化养殖场、药物实验、产品测试、皮包皮具、动物表演,更不用说还有单纯为了取乐而进行的虐杀。他们蓄意虐待、殴打、杀害动物:被扭断了四肢在地上抽搐的狸花猫,被人用箭射入眼睛的黑猫,被开水烫、被扔进嘴里的鞭炮炸开的流浪狗,在街头被活剥皮的橘猫,因为不肯求饶被虐待致死还被调侃“有点骨气”的奶牛猫......
人类对待动物,真可谓是剥皮噬骨。那一点从伴侣动物身上生发出的善意与共情,常常因为更残酷的一切显得微不足道,甚至颇为可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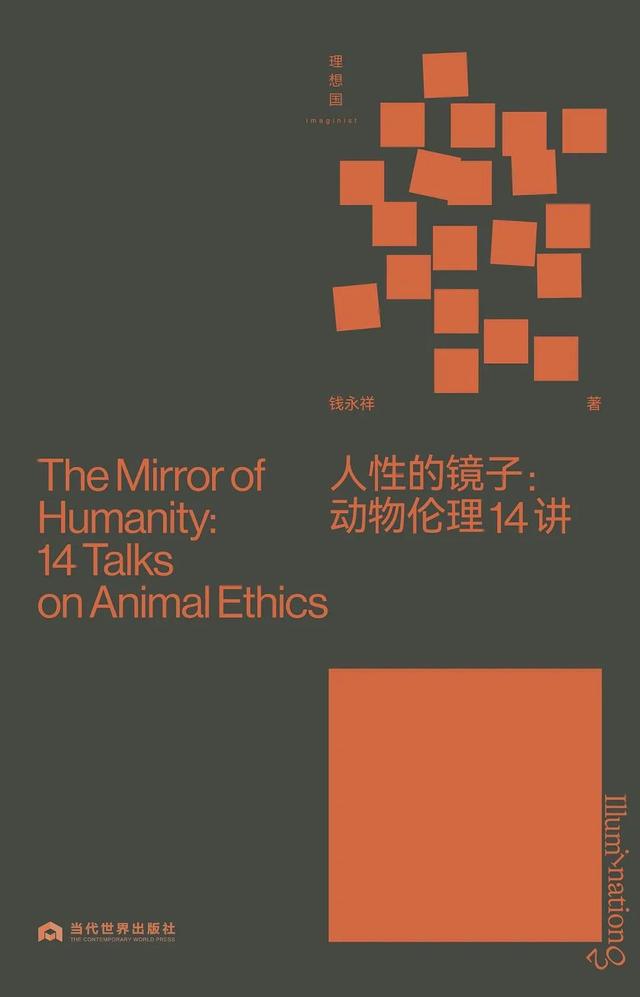
《人性的镜子》,作者: 钱永祥,版本:理想国|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4年4月
人是杂食动物,几乎所有人都在吃动物。据统计,2020年中国大约宰杀了7亿只猪、0.4亿只牛、1.77亿只羊,以及92.9亿只鸡;美国在2020年则大约宰杀了1.3亿只猪、0.33亿只牛,以及93.5亿只鸡。这些数字,还不包括上亿上兆的鱼类以及其他水生动物。(钱永祥,《人性的镜子》,数据由Faunalytics网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数据库整理)
而我也是一个肉食者。对于从小到大吃肉的人来说,这个饮食习惯似乎是自然的事。整个肉食生产链条也有意识地让消费者与屠宰场的血腥场面隔离开来,以至于我们很少意识到背后的残酷。很多年里,我甚至未曾思考过饮食习惯这件事。我目前也无法做到完全成为素食主义者。但这不代表肉食者不能思考、不能参与推进动物权益的行动。
我刚工作不久时的一次聚餐上,大家聊起“吃狗肉”的话题,彼时“狗肉节”正风靡。一位长辈说,吃狗肉没什么问题。他质问:你们谁是素食者吗?那谁也没资格指责吃狗肉的人。他指指我笑着说,你们这些小姑娘,不能因为喜欢猫猫狗狗,就觉得猫狗的命比猪牛羊宝贵。猫狗不该吃,猪牛羊就该吃?更进一步说,蔬菜就该吃?你们干脆啥也别吃了。这不就是生物链。
他使用一连串的因果推论,却夸大了每个环节的因果强度,将可能转化为必然。彼得·辛格在他的经典著作《动物解放》中提出了一种衡量标准,用感知痛苦的能力来判断动物的处境。这一说法不乏挑战者,有更多的学者提出不同的衡量路径。但我们得承认,蔬菜并没有中枢神经,它濒死时感到的痛苦的确小于动物濒死时的痛苦。如果要将不可知论推到极致,说我们并不知道蔬菜是否真的没有神经系统,那人类真要陷入不可说也不可行动的境地了——虽然如此对其他物种未必是坏事。
 《动物解放》, 作者: [澳] 彼得·辛格 , 译者: 祖述宪 , 版本: 湖岸|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动物解放》, 作者: [澳] 彼得·辛格 , 译者: 祖述宪 , 版本: 湖岸|中信出版集团 2018年8月 曾有网友询问佛教徒(定弘法师):烧水杀菌是杀生吗?听来颇为好笑,堪称电车难题烧水版。
大师开解说,严格来讲是杀生,但这是迫不得已的选择。如果不杀菌,生病去看医生更是劳民伤财,吃药还是得杀死体内的细菌。那如果不去看病也不喝水呢?饿死得了。大师又说,还是不行,这等于杀死了自己,还是杀生。我想,没有人会认为烧水杀菌跟杀死一个人是同样的罪过。毕竟,细菌跟人在面临死亡时的想象力与感知到的痛苦是不同的。
以前我无肉不欢,几乎每顿饭都会吃肉,喜欢囤大量的肉类冻在冰箱,那让我感觉安全。但现在我吃肉的数量减少了很多,不再囤积肉制品。这当然远远不够,但至少它是一个开始。在人类的饮食选择上,一直有着巨大争议。也许未来的某一天,大部分人类可以改变饮食习惯,或者我们会找到更好的替代选择。
“食物链”可以被接受,但无节制地杀生是另一件事。
 在“全部”和“绝不”之间
在“全部”和“绝不”之间 有时我疑心自己患上了“厌人症”。我感到无法再为人类的权利摇旗呐喊更多了。有无数的生命承受着比人类千倍百倍的苦,而人类永远觉得不足够,想索要更多。想到黄永玉那句感叹:人真不是个东西。也许人类是这个星球并不美好的意外。疫情期间的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展示了当人类的行动和存在收缩,地球将会如何生机勃勃。但黄永玉那句感叹还有后半句:我也是一个人。所以怎么办?如何爱上作为人类的一生?如何作为一个人,去攫取去施展去信奉意志去完成至高无上的人类理想?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剧照。
作为一个女性,有时性别与物种这两者会带来困惑。当走向女性主义理论,我发现了生态女性主义,相见恨晚。它内部有着众多分野,但大体来说,都强调人类剥削自然与性别制度剥削女性的权力结构是同构的。其中,女性与自然同样是被压迫的一方。这种权力结构共享着同样的逻辑:弱肉强食,胜者为王。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上野千鹤子指出“女性主义绝不是弱者试图变为强者的思想,而是追求弱者也能得到尊重的思想”是多么切中要害。
但我困惑于一个敏感问题:在自然与动物面前,女性扮演何种角色。得承认,女性不只是与它们站在一起的天然同盟,她既是受害者又是加害者。甚至可以说,在人类征用自然的历史中,女性更像是男性的共谋者,而非反抗者。相关著作似乎很少提及女性如何处理这一双重身份,当然我的阅读范围是相当受限的。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强调去中心化,打破二元对立,尤其是自然与人类、男性与女性这样的二元对立。对于生态环境/动物伦理问题,女性在压迫结构中被裹挟,在漫长的历史中很难参与决策,这更多是结构问题,而非个体责任。打破二元对立,重申主体性,但在面临责任时强调结构与个体的区分(这当然有一个历史/未来、理论/现实的问题),我恐惧这样“原谅”自己太过轻巧。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剧照。
但如此追根究底,的确太过严苛了。我又疑心这是一种厌女症。我们首先刻薄地审视自己,继而苛刻地审视女性。当我们“不原谅自己”的时候,世界其实既不在乎女性问题,也不关心动物问题,更不在意自然问题。
没有答案。但如同不要从吃肉滑向吃狗肉,我警惕自己不要从“保护动物”滑向“厌恶人类”。
从对伴侣动物的善意与不忍出发,逐渐共情更多动物的处境,我不认为这需要反对。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很自然的道理。但它曾长久被打上“圣母”的标签。
很久之后,我读到更多相关著作,才发现这样朴素的理解有着诸多回响。台湾学者钱永祥在《人性的镜子》中谈到不同动物伦理思想的来源与路径,他提及女性主义处理动物伦理的一大优势正是从“关系”视角切入:“用强调逻辑、理性的方式构建动物伦理学,在辩论的时候也许铿锵有力,但大多数人并不是基于这类抽象的理想才关心动物的。换言之,强调理性,排斥情感,其实并不符合人性的实际情况。”多数人是因为对动物的喜爱,或者看到动物的遭遇,产生愤怒、同情、不忍等情绪,从而意识到我们对动物负有一些道德责任。动物伦理真的只需要逻辑理性吗?钱永祥建议肉食者可以每周或每月挑选一天吃素,可以关注养殖动物的处境,可以推进人性化的养殖与屠宰——我们还有很多办法,减少动物的痛苦。
到了这里,人类也许还是只能回到最朴素的出发点:尽力而为。
如果我们做不到不吃肉,那可以先做到不要浪费动物的血肉。如果我们做不到杜绝动物实验,至少我们可以不滥用动物实验。如果我们做不到不生产垃圾,那我们可以先做到少生产垃圾。在这些议题上,纵欲与节欲仍然有很大不同。
做这样的努力,比不加节制地滑向“既然你吃猪肉,也别管我吃狗肉”要好得多。毕竟,在全部和绝不之间,还有一段又一段漫长的路。

纪录片《地球改变之年》剧照。
本文系独家原创内容。作者:张婷;编辑:走走;校对:付春愔。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最近微信公众号又改版啦 大家记得将「新京报书评周刊」设置为星标

2024书评周刊合订本上市!
点击书封可即刻下单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了解《新京报·书评周刊》2024合订本详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