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马寅初在《新人口论》中,留下了一个带有强烈警示意味的数字:“如果按1953年的增长率计算,到2023年中国人口应有26亿人。”
这个预测,一度引来了无数质疑甚至批判。

然而当我们对比2025年实际约14.1亿的人口规模,会惊觉:
在那漫长七十年的人口与政策演化中,三代人的生活轨迹,国家的粮食安全、就业竞争和养老结构,早已在计划生育的轨道里被彻底改变。
假使当初历史在某个瞬间走向了另一面,今天的中国是否会与印度一样,面对难以承载的人口压力?
一、突破承载极限的推演走进假设,如果没有马寅初的呼吁和后续的计划生育政策,中国人口将会依旧沿着高生育率惯性一路狂飙。

据1950—1970年平均5.8的总和生育率推算,2025年前后的人口或许会轻松冲破23亿甚至25亿,远超当前14亿多的实际规模。
那些年我们痴迷于“人多力量大”,却常常忽略资源与环境的可承载能力。
粮食预警随之而来。
本就耕地有限的国土,若真让超过20亿以上的人口大军涌入,按照人均400公斤的粮食需求来测算,至少需要9亿多吨粮食来维持温饱,而2025年实际产量预测在6.8亿吨左右,少于需求的缺口极可能造成大面积进口依赖。

更可怕的是,粮食进口量一旦过高,就意味着对国际市场波动的脆弱度随之上升,价格控制与社会稳定都将面临巨大隐患。
而教育和医疗系统,也会在这种人口洪流中难堪重负。
假设高校毛入学率维持在60%的水平,庞大的适龄大学生数量将达到1.38亿,超过了当今现实近五倍的在校大学生规模。
彼时若没有强力的政策疏导,高校或许会出现“万头攒动”的场景,教育资源极端匮乏,师资无法跟进,无法保证教学质量。

再看医疗体系,每千人需要至少配备5.2名医师才能勉强维持当下的服务水平,但是现实中却很难在短时间内培养出这么多医疗人才。
若没有政策干预,医院“挂个号排三天队”恐怕会变成常态。
 二、经济困局夸张
二、经济困局夸张人口是经济的内生动力,但过度的人口爆炸却会蚕食经济升级的土壤。
在马寅初当年的预测中,他认为每降低1‰的人口增速,就能显著提高国民收入的积累率。
如果人口增速一路维持在30‰的高位,到2025年全国的储蓄率很可能会低于20%,与现实中超过45%的储蓄率形成鲜明反差。
换言之,若资金都被庞大的消费需求“吃”掉,哪来的余力发展高端制造业、投入研发和技术升级呢?

就业市场也会变得异常脆弱。
到2025年,若劳动年龄人口突破15亿,不仅城市就业岗位供不应求,农村人口进城打工的规模也将再度激增。
在最极端的情况下,大批年轻劳动力没能及时转向高技术产业,或许会挤占原本有限的工厂岗位,反过来导致失业率超过15%的“警戒线”,催生更多社会矛盾。

另外,技术升级之路也会遭遇更艰难的迟滞。
如果大量企业可以依赖廉价劳力,就很可能放缓自动化、智能化的技术改造。
回看上世纪90年代到处是“民工潮”,不少工厂宁可招千把人,也不愿意投入高额成本去升级生产线。
这样的路径依赖,短期或许能解决劳动力就业,但长远而言却会耗损国家的核心竞争力。
中国的工业化或将在低端产能的红海里,苦苦挣扎更久。
 三、这么多人,打底能承受住吗?
三、这么多人,打底能承受住吗?当人口规模以几何级数猛增,大地能否承受如此大的压力?
在假设情境中,人均耕地可能跌至0.7亩,远低于联合国0.8亩的警戒线。
历来就缺水的北方平原,地下水的超采量可能飙升至每年400亿立方米,几近形成难以逆转的生态黑洞。

污染问题也会愈演愈烈。
如今一些指标尚且能够控制在警戒范围之内,但若人口超负荷,参照印度密集区域的经验,PM2.5年均浓度或将突破150微克/立方米,几倍于我国目前平均水平。
更重要的是,环境破坏往往难以逆转,一旦土地盐碱化、地下水枯竭、空气污染加剧,就像抽走了下一代的生存希望。

能源安全同样令人担心。
如果经济规模和人口同时高速增长,到2025年原油对外依存度或许会冲破85%,煤炭年消耗量可能突破60亿吨。
进口外汇消耗剧增,国际原材料市场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在国内激起层层震荡。
如同站在生态环境与能源供应的临界点上,人口失控正是火上加油的一把火。
 四、被压缩的现代化进程
四、被压缩的现代化进程在这种高人口压力下,教育代际传递的断层效应会被放大。
由于资源分配不足,文盲率可能居高不下,甚至保持在15%以上,再度形成“多生育-低教育”的恶性循环。
个体能力被限制,社会整体素质难见飞跃。

性别比例,也会失控更久。
如果没有后来的一系列政策纠偏,中国社会传统的“重男轻女”观念在部分地区会固化延续。
出生性别比或持续高于115,一代又一代的女孩被埋没,社会结构和婚姻观念更加失衡。
假如流动人口达到5亿,所谓的“城中村”面积有可能占到城市建成区的40%甚至更多。与之相随的是住房、医疗、社保等公共服务的缺口越发明显。
城市发展就像一只被吹涨的气球,看似庞大,却随时可能被来自资源或就业的尖锐压力戳破。
 五、另一种发展路径评估
五、另一种发展路径评估从国际视角审视,中国若失去人口控制,可能就会以另一种方式被“锁定”。
粮食进口依赖度过高,年进口量或突破3亿吨,对全球粮价的波动和话语权都带来负面冲击。
洪水般的劳动力供应,固然能够延续低端制造的生命线,却也会限制高端技术的比重发展,制造业升级道路被更长时间地拖住。
比照目前我国高科技产业约占比41%的数据,那时或许难以突破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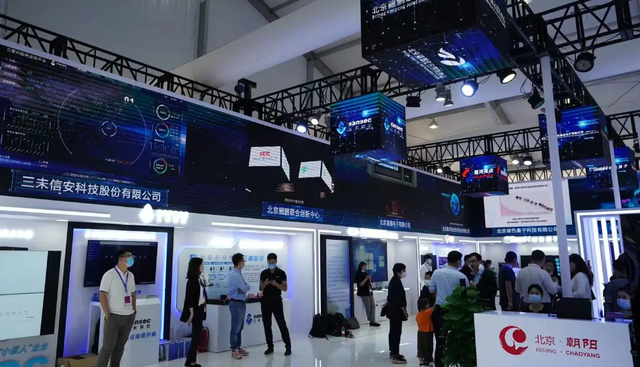
对于气候与碳排放的博弈也会十分被动。
人口基数大意味着更高的总排放量,即便人均还能与其他大国接近,但绝对量过于庞大,国际气候谈判中,原本力争上的小空间都被净削弱。
人均排放上升到8.5吨甚至更高,一旦遭到贸易壁垒或碳关税的打击,转型成本急剧攀升。

或许有人会问:多个人口换来更强的消费市场,难道不是大国红利?
高速扩张的人口更易陷入资源紧缺,以及社会发展失衡的泥淖,反倒难以真正形成可持续的内需体系。
在全球化竞争中,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和滞后的产业结构,会使中国在国际坐标上失语寒颤。
 结语
结语每一个时代都有属于它的考题,而我们在马寅初提出《新人口论》的那一刻,等于提前拿到了参考答案。
当2025年的生育政策已步入“三孩时代”,当用于托育和养老的举措更加完善,或许我们应该感念当年那场关于人口控制的“危言”。
回望这七十年,中国的命运在三代人的集体选择里找到了相对平衡,也为全球快速发展的人口社会提供了另一面审慎的镜子。
倘若换了另一个平行时空,或许您正忙着同时操心三个孩子的升学压力!
参考资料:1.经济学动态:中国人口政策与人口结构及其未来发展趋势

2.人口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

3.中国自然资源部:为什么要珍惜每一寸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