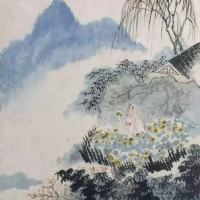汉赋圈中的“惊天互撕”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张衡的《二京赋》和班固的《两都赋》都是汉代辞赋的经典之作,下面就两赋的具体内容,举例说明张衡《二京赋》对班固《两都赋》的潜在回应,以及其中暗藏的“彩蛋”。

一、结构模仿与主题颠覆
班固《两都赋》采用“西都客夸长安→东都主人驳斥→颂洛阳”的框架,而张衡《二京赋》虽沿用“凭虚公子夸西京→安处先生驳斥→颂东京”的结构,但内容上暗含对班固的“修正”。
例如:对长安的态度
班固《西都赋》:
借“西都宾”之口极写长安宫殿之奢靡(如“九真之麟,大宛之马,黄支之犀,条支之鸟”),实为铺垫后文对洛阳的赞美,但客观上让长安的繁华跃然纸上。
张衡《西京赋》:
虽同样描写长安的奢华,却加入大量讽谏细节,如写帝王狩猎“白日未及移其晷,已狝其十七八”,暗讽统治者沉迷享乐;甚至直接批评“取乐今日,遑恤我后”,点明奢靡误国。
彩蛋:班固笔下的长安是“被批评的靶子”,而张衡的长安更像“被解剖的标本”——他并未完全否定班固的描写,却通过更夸张的铺陈和突然的议论,暗示班固的批评不够彻底。

二、对“天命”与“礼制”的解构
班固在《东都赋》中强调东汉定都洛阳的“天命”与礼制完备(如“建章甘泉,馆御列仙”),而张衡在《东京赋》中刻意淡化神话色彩,转向务实。
例如:对“巨灵擘山”神话的改写
班固《西都赋》:
用“巨灵赑屃,高掌远跖,以流河曲”的神话渲染长安地理的“天命所归”。
张衡《西京赋》:
将同一神话改写为“巨灵赑屃,厥迹犹存”,仅客观提及传说,随后立刻转向现实水利工程“通沟大漕”,暗示“人力胜于天命”。
彩蛋:张衡用班固的典故,却抽离其神话光环,暗讽班固过度依赖“天命”叙事。

三、对“节俭”的定义之争
班固《东都赋》赞美洛阳“宫室光明,阙庭神丽”,但重点在礼制;张衡则直指“节俭”的核心是爱民。
例如:对帝王出行的描写
班固《东都赋》:
写天子出行“乘銮舆,备法驾”,强调仪仗合乎礼制(“清道案列,天行星陈”)。
张衡《东京赋》:
写同一场景时,先赞“礼官整仪,乘舆乃出”,却突然插入“民忘其劳,乐输其财”,暗示礼制背后是百姓的负担,结尾更直言“今公子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也”。
彩蛋:张衡表面上模仿班固的“礼制赞美”,实则暗藏刀刃——他揭露了班固笔下“完美礼制”可能掩盖的民生问题。

四、对历史典故的“反向使用”
两人皆引周代故事,但用意迥异。
例如:周成王营洛邑的典故
班固《东都赋》:
引周公营洛邑证明洛阳的合法性(“周公初基,其绳则直”)。
张衡《东京赋》:
同样引用周公,却强调“虑玄武以无成,意百堵之皆兴”——即“不追求宏大,只求实用”,暗中批评班固以“合法性”掩盖现实问题。

五、终极彩蛋:赋的结尾
两赋结尾的议论最能体现立场差异:
班固《两都赋》:
以“昭节俭,示太素”作结,仍归于对东汉政权的颂扬。
张衡《二京赋》:
结尾突然跳出叙事,直斥“今舍纯懿而论爽德,以春秋所讳而为美谈”,甚至发出“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的警告(比唐太宗早数百年!),将矛头直指当下。

总结:是“diss”还是超越?
张衡看似在模仿班固的结构,实则处处“解构”其逻辑:
1. 班固的“二元对立”:长安(奢)vs 洛阳(俭)→ 张衡的“一体两面”:两京皆可奢可俭,关键在执政者。
2. 班固的“天命叙事”→ 张衡的“民本思想”。
3. 班固为政权辩护→ 张衡为社会敲警钟。
与其说张衡在“diss”班固,不如说他借《两都赋》的框架,完成了一次对汉赋传统的升级——从“政治颂歌”转向“社会批判”。这种暗流涌动的“互文性”,正是文学史最精彩的“彩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