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655年,齐桓公在首止(卫邑,近于郑,今河南省雎县东南)召集了鲁僖公、宋桓公、陈宣公、卫文公、郑文公、许僖公、曹昭公等诸侯举行了一次八国峰会,周惠王之太子郑列席会议。这也就是齐桓公九合诸侯的第六合,首止之盟。
为什么太子爷也赏脸来了?原来,齐桓公发现周惠王在老婆惠后的枕边风吹拂之下,想废长立幼,废掉太子郑,改立小儿子王子带为储君,这可不好,齐桓公觉得自己有必要去管一管。
这算不算多管闲事儿呢?齐桓公可不这么认为,从辈分上算,齐桓公是当年周庄王的女婿,而周惠王是周庄王的孙子,所以齐桓公乃是周惠王的舅舅,舅舅管外甥,有何不可?再说了,他还是霸主呢?霸主就是负责维持天下秩序的,包括他名义上的主子周天子在内。其实说到底,齐桓公的“尊王”只是扯了虎皮做大旗,借这个幌子为自己的霸业服务而已。要他真的唯周天子马首是瞻,那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现实的。何况,传承制度是权力秩序的基石,如果周天子带头破坏游戏规则,各国诸侯必然纷起效尤,从而增加中原政局的不稳定因素,牵扯齐国的精力,齐桓公老了,不想再到处奔波了,大家安生一点儿不行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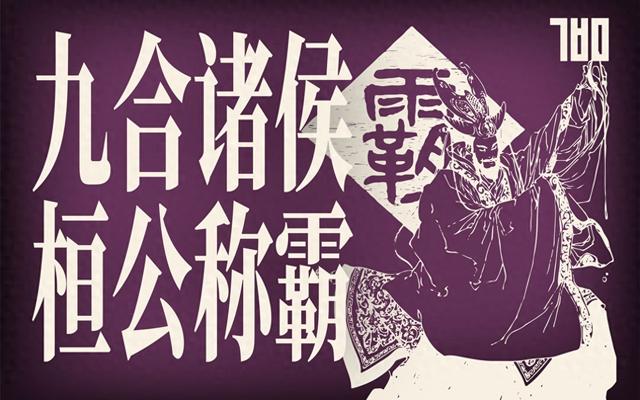
当然,若因此和周天子直接对抗也是不合适的,当年郑庄公就因此而失去霸业,所以齐桓公决定绕个弯子举行盟会,让诸侯们一起和太子郑定下君臣名分,这样周惠王就无从废储了。而齐国也可以通过拥立天子,进一步控制周王室并抬高自己的霸主地位。而周惠王在接到消息后虽然相当郁闷,但却没有理由阻止,毕竟齐桓公此举正大光明,且为尊王之举,他根本无法拒绝,那怎么办呢?他抱着头想了半天,终于给他想到了一条妙计。
数日后,周王室的上卿宰孔也来到了首止之会,正好碰上齐桓公在开会:“天子想要废长立幼,这可是违背了老祖宗礼制的!天子带头不遵礼,我这个霸主很难做啊,所以寡人提议,咱们八国诸侯就在此签订盟约,立誓共同支持太子日后即位,如何?”
太子郑带头鼓掌,宰孔和其他诸侯也跟着鼓掌,心里头却在嘀咕:“好像你齐小白也不是嫡长子吧!”
诸侯中间的郑文公尤其犯嘀咕,当年,他的父亲郑厉公有拥立周惠王之功,两家关系密切,他非常看不惯齐桓公多管周惠王家闲事儿。再加上去年伐楚的时候,齐桓公强迫自己将重镇虎牢封赏给郑国大夫申侯,这也让他非常不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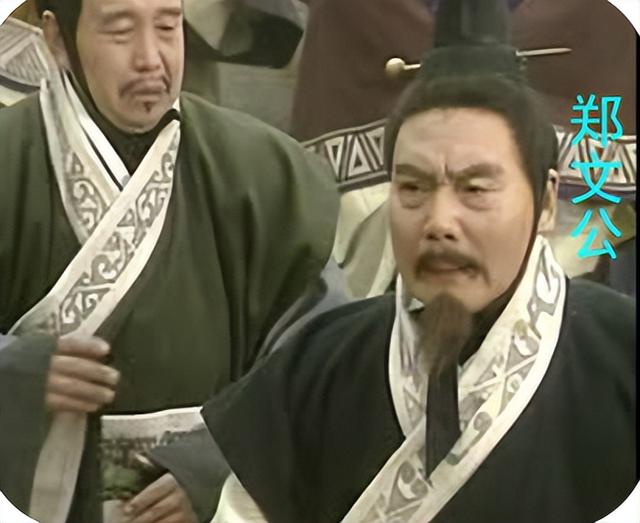
多少年来,郑文公从来就没有彻底服过齐桓公,其它诸侯动不动就去齐国朝见,郑文公一次也没去过。齐桓公还为此拘留过郑国的使臣郑詹,但郑文公也相当拗,不去不去就不去,你能咋地。
而就在这时,开会间隙,郑文公突然被一个人叫去密谈了,谁?周天子的太宰与上卿、周公旦的后裔宰孔。
原来,宰孔正是周惠王派来的,他的任务就是策动郑文公背叛齐国归附楚国,并联合晋国,共同对付齐桓公。《左传·僖公五年》载,周惠王向郑文公表示:“吾抚汝以从楚,辅之以晋,可以少安。”
傻子都看出来了,齐桓公所谓尊王,其实只是尊他自己而已。周惠王不甘受制于人,所以决意反击,为此他竟不惜拉拢蛮夷,反正这江山他也控制不了了,不如把水搅浑。
郑文公这会本来就开的很郁闷,又见周天子也讨厌齐桓公,顿时被阳光给灿烂了,于是他半途开溜,来了个不辞而别。
继陈国叛齐后,郑国也反水了,他们都加入了南蛮楚国的阵营,后者竟还是华夏领袖周天子授意的,真是荒天下之大谬!
史书记载,在这一年秋九月,很多地方发生了日食,连老天爷都觉得荒谬。
齐桓公于是愤怒了,他不敢得罪周天子,只好去打郑国,打了好几次,终于把郑国给打服了。
公元前653年秋,齐桓公召集鲁、宋、陈、郑四国在宁母(鲁邑,位于今山东省鱼台县境)举行盟会,商量如何处置郑国。这也就是齐桓公“九合诸侯”的第七合,宁母之盟。
经过郑文公这件事儿后,齐桓公也觉得自己的霸位有些不稳了,于是他接受了管仲“礼待诸侯”的建议,向与会诸国送上一些会议纪念品,当然,大方的齐桓公不可能送些地摊货,而是“虎豹之皮、文锦”这些奢侈品(《管子·霸形》),胡萝卜政策果然奏效,在它的感召下,大家伙又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了齐桓公周围。
楚成王以刀服人以力服人,齐桓公以德服人以礼服人,还有后来宋襄公的以仁服人以义服人,其实都失之片面,只有三管齐下,才是春秋称霸之大道,所以后来的晋文公与楚庄王总结前辈经验,终于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晋楚长期而稳定的霸权。
这一年的十二月份,阴谋破产、羞恼交加的周惠王总算是在失意中悄然驾崩了。太子郑害怕王子带一党趁机造反,遂秘不发丧,而使人密告齐桓公为他做主。
很好笑,天子居然还要诸侯为他做主。可见周室朝廷里,已经全是惠王纵容王子带培植的势力。
次年春,齐桓公召集鲁、宋、卫、许、曹、郑六国在成周附近的曹国洮地(今山东甄城县西南)举行盟会,共同拥立太子郑为周天子,是为周襄王。这也就是齐桓公“九合诸侯”的第八合,洮之盟。这次盟会本来没请郑国,但郑文公却一改常态主动乞盟,因为他的大靠山周惠王和楚平王都靠不住了,所以,身为一个识趣的政客,他非常明白跟着风向走。
有了齐桓公出面,周襄王这才松了一口气,宣布正式即位,并为父亲周惠王发丧。
“尊王”尊到这种境界,全天下都明白,齐桓功业之盛,以臻登峰造极了。
齐桓公也是这么认为的,所以他决定举行一次规模最大的盟会,以彰其名。另外,正好这一年齐国的坚实盟友宋桓公病逝,宋桓公也算是个老实人,齐桓公每次盟会他都来参加,相当捧场,现在他死了,齐桓公也不免有些伤感,所以决定在宋地举行盟会,也好给宋国嗣君定位,而这位宋国嗣君,正是大名鼎鼎的宋襄公。
于是,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夏,春秋史上最重要的盟会,葵丘之盟,在齐桓公的组织下胜利召开了。葵丘乃宋国重镇,在今河南兰考。

这是一次天下之盛会,不仅中原诸侯全部跑来捧场,就连周天子也派了“钦差大臣”宰孔前来祝贺。
新即位的宋襄公对此次盟会相当期待,因为齐桓公是他的学习榜样,也是他的超级偶像。哪怕自己身在孝中,也一定要参加。
其实诸侯们多来一个少来一个都没有太大的关系,关键的关键,是周天子的“天使”宰孔来了,他的任务就是代表周天子,感谢齐桓公的拥立大恩,并赐予齐桓公无上的荣耀:一块肉、一些弓箭、还有一辆马车。
有人要说了,这算啥无上的荣耀啊,比起齐桓公上次援卫时差点拉了一个动物园过去,周天子实在太小气了。
这样想就错了,其实齐桓公有的是钱,啥都不缺,只要面子和排场就足够,所以周天子投其所好,给他的都是面子,而且是大面子。
首先,那块肉并不是普通的肉,而是“文武胙”。所谓“胙”,就是祭肉,古人认为,祭祀完毕后的供品之肉,食用之人会得到祖先的福佑,所以大家都抢着要。而且按照周礼,天子的祭肉只能送给同姓诸侯,现在齐桓公以异性诸侯的身份获赐祭肉,得以同享周的先祖们赐给的福佑,这可是祖坟上冒青烟的大荣耀,忒有面子了。
如果只是赐胙,其实也没啥,自齐桓公始,很多霸主都得过,不稀奇。但是“文武胙”又不一般了,那可是周天子祭祀周文王与周武王所用之供品,是大圣人大贤王在天之灵享用过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方好了,如果说“胙”是开过光的佛珠,“文武胙”就是开过释迦牟尼如来佛的佛珠,是极品中的极品,是“唐僧之肉”,是肉王中王!历春秋一世,也只有齐桓公得过,即便在加上战国,也只有齐桓公、秦孝公、秦惠文王三人得过。齐桓公这面子可大了。

其次,那些箭也不是普通的弓箭,而是“彤弓矢”,也就是以丹彩涂饰的弓与矢。这玩意儿相当于后世的尚方宝剑,有了它诸侯就有了代天子讨伐叛逆的大权,这就不仅仅是面子工程了,它还代表着实际的权力。历春秋战国一世,也只有齐桓公与晋文公得到过。
最后那车也不是普通的车,而是“大路”。这是一种黄金装饰的木制马车,据《史记·乐书》:“所谓大路者,天子之舆也。”可见大路便是天子所乘坐的专用豪华马车,由六马牵引。在严格的礼制中,诸侯只能用四马牵引的“路车”,大夫用三马“轩车”,士用二马“饰车”,不能僭越。所以,“大路”通常只赐予特别有功的诸侯,以示如天子亲临,并可享受一些与天子等同的礼遇,比如随同此车还有一幅配套的九旒龙旗(旒音流,飘带流苏之意。按照周礼,天子之旗为十二旒,公侯之旗为九旒)。而这等礼遇历春秋一世也只有齐桓公与晋文公得过。
真是太给面子啦!
还有更给面子的。
原来齐桓公正准备下阶拜谢,宰孔忙阻止他道:“且有后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注1)耋老(注2),加劳,赐一级,无下拜。’”意思是说齐桓公年纪大了,又劳苦功高,就免礼别跪了,真要闪了老腰,那可不是吃两块祭肉能补回来的。

一听不用下跪磕头,齐桓公松了口气,他也七十多岁的人了,老胳膊老腿可受不了这通折腾。周天子也是我给扶上去的呢,既然他这么识相,那寡人就勉为其难答应他,不跪拜了吧!
见齐桓公竟想偷懒耍奸,管仲赶紧劝他说:“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
齐桓公这才罢休,出来跟宰孔说:“天威不违颜咫尺,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曰‘尔无下拜’,恐陨越于下,以遗天子羞。敢不下拜?”
意思是:天子的威严的面容好像就在眼前,小白我哪敢放肆?我还不下拜?不下拜就折福摔死了!到时候又给天子丢人,我不敢这么做。
说完,齐桓公颤巍巍的小步倒退着降阶而下,再面向北匍匐于地,叩头稽首,然后再次起立,立正,再缓步走上台阶,登堂,再拜,然后才郑重接受天子的赏赐,好一通折腾。

天下诸侯见齐侯如此谦逊知礼,皆为之赞服,更觉齐侯谦逊之中透着一股傲视天下的霸气,令人折服。
至此,齐桓公所有手续办理齐全,正式当选为天下最具影响力男人,他的人生达到巅峰。
接下来,宰孔打道回府,齐桓公与天下诸侯正式开始盟会,看着台下一帮旧小弟新小弟,他心中除了激动还是激动,差点就想引吭高歌一曲。
葵丘之盟,规格高、意义大、与会诸侯众多,它是齐桓公“九合诸侯”中最重要的一合,也是最后一合,齐桓公他终于功德圆满,成为了天子正式册封的诸侯总管,春秋第一霸主。汉高祖刘邦因此而赞曰:“盖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也!”(《汉书·高帝纪》载其《求贤诏》)

和后来的霸主夸耀并维持自己的势力不同,齐桓公身为五霸之首,他的目的与功绩还是维持华夏整体的秩序,据《孟子》一书记载:齐桓公在葵丘之盟上,一共提出了五条盟约。
第一条:诛不孝,无障穀,无曲防,无贮粟,无遏籴,同恤灾危,备救凶患;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
所谓障穀、曲防,就是当初楚成王对宋国干的缺德事儿。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为了自身安全,或是为了加害邻国,经常在流经本国的黄河、淮河、济水等大河筑起堤防,堵塞河流,这超损人的!因为如果上游国家筑堤,下游国家便会断水爆发旱灾;反之如果下游国家筑堤,上游国家便会积水淹没良田。
所以齐桓公提议,大家以后不要再这么干了,驱水为害,损人利己,非君子所为也。我们要通力合作,共同治水,以经济合作带动政治团结,加强各国的凝聚力。
“反对障穀,黄河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河!”齐桓公带着诸侯们一起高喊,气氛很热烈。
口号谁都会喊,但问题是当时诸侯国各自为政,都有自身的利益,齐桓公能管的了一时,却管不了一世啊。春秋尚好,到了战国时代,“障穀”问题越演越烈,几至不可收拾。
比如《战国策·东周》就曾记载:“东周欲为稻,西周不下水,东周患之。”
再看《史记》的记载,公元前332年,赵与齐魏作战,竟将黄河河堤决溃以浸淹对方。
另外的证据,还有《孟子》一书中孟子责备魏相白圭的话:“禹以四海为壑,今吾子以邻国为壑……吾子过矣!”
最后是谁解决了这个大问题呢?秦始皇。他一统天下之后,就“决通川防”,从此治水一事,终于由中央政府集中管理了。
这说明对于以大河贯穿天下的中国来说,中央集权远比邦国联盟制度要好。最后还是秦始皇实现了齐桓公的理想。
而所谓贮粟、遏籴,就是积储粮食、不对外出口。由于春秋时国家普遍较小,一有自然灾害则往往是全国性的,而且当时农业生产技术与仓储技术都比较落后,所以很容易爆发饥荒,这样就得求助于邻国,若邻国不救,便会有举国无炊的危险。这样就难免会爆发纠纷与战争。
关于这一点,十余年后的秦晋风波很能说明问题。晋国发生饥荒,秦国以渭水运粮,大举援晋;而由于仓储技术落后,秦国把余粮都给了晋国,自己就没了战略储备,而恰巧第二年轮到秦国饥荒,晋国却见死不救,借机搞封锁,于是秦晋之间爆发大战,秦国大胜,晋国割地赔款。

显然,这个问题,同样只有天下一统后才能得到彻底解决,而齐桓公却寄此希望于盟约与邦交,只能说是一种美好的愿望吧。最后也得是秦始皇才能实现齐桓公的理想。
另外“无易树子,无以妾为妻,毋使妇人与国事。”简单来讲就是要维护宗法秩序,禁止“废嫡立庶”与“改立夫人”,不要让庶子做国君,不要让小老婆变成大老婆,不要让后宫干涉君位继承;这些都是春秋时代之最大乱源,数十年来已引起无数诸侯内乱与国际纠纷,就连上任周天子周惠王都差点犯下此等错误(注3)。所以齐桓公才想要摆脱周天子与诸侯另立盟约,在中原重建起统一的政治秩序,确保各国不因内斗和纠纷牵扯精力,大家都文明一点,规矩一点,紧密团结在齐国周围,共同对付北狄南蛮,不好吗?
葵丘之盟约第二条:尊贤育才,以彰有德。
这条简单,无非就是培养人才。但从齐国的情况来看,自管仲鲍叔牙隰朋这代老一辈贤臣之后,齐国年轻一辈中几乎没有贤才,可以说是青黄不接,后继无人。显然齐桓公这些年虽霸业鼎盛,但在人才问题上有所忽视,所以管仲特意将这一条加入盟约之中,希望引起齐桓公与其他诸侯的重视。
葵丘之盟第三条:敬老慈幼,无忘宾旅。
尊老爱幼,还有善待各国来使,这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需多言。
葵丘之盟第四条:士无世官,官事无摄,取士必得,无专杀大夫。
意思是:士人的官职不得世袭,官员不能身兼多职,要录用有才之士,国君不得擅自诛杀大夫。

春秋时期的政治体制主要还是贵族共和制与世卿世禄制,但在这条公约中我们可以看到,齐桓公与管仲希望对其弊端进行部分改革,以改善官僚系统的流动性与专业性;比如规定只有大夫的官职可以世袭,低一级的士则不能世袭;另外春秋以后国家政治开始变得复杂,并出现了将相分离的官制,而将事权分开、专人专职,这对政局的稳定与避免专权是有积极作用的。此外春秋时代礼崩乐坏,而明文法又未建立,导致各国都有很多臣子任意弑君、君主随意杀臣的情况,这也是齐桓公坚决反对的。
当然,要完全解决世卿世禄的诸多弊端与礼崩乐坏的政治混乱,实现完备的专业官僚体系、明文法制度与中央集权制度,还是得靠四百多年后的秦始皇了。
葵丘之盟第五条:无有封而不告。
封赏大夫采邑必须公告天下,让天下诸侯来监督你——或者也可以解释成要报告霸主齐桓公,得到齐桓公批准才行。如果是这样,那么齐桓公就等于变相获取了中原各国的人事权,在制度上建立起了齐国主导的权力秩序。
五条盟约之后,依照惯例还有一句套话:“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注4)完了再歃血为盟,这会就算开完了。不过据《孟子》:“葵丘之会,诸侯束牲载书而不歃血。”以及《谷梁传》:“陈牲而不杀,读书加于牲上。”看来诸侯们并没有按照规矩举行宰牲与歃血仪式,只是把盟书放在牛身上宣读一遍即罢。为什么?因为春秋时代耕牛非常贵重,就这样杀掉太可惜了,而且也显得相当野蛮、不文明,齐桓公这也是对会盟制度的一种人性化改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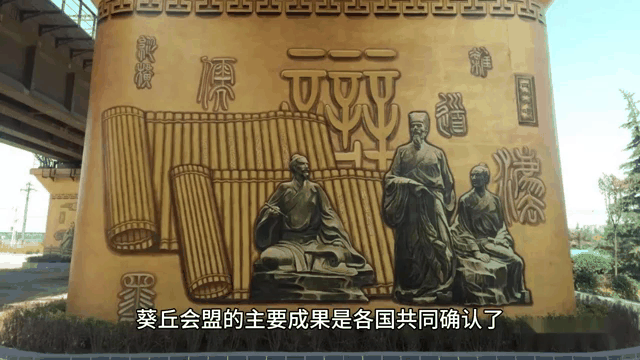
不过说实话,歃血也就一形式而已,真正有心歃不歃都无所谓,若是无意遵守盟约,就算宰一万头畜牲、把嘴巴涂再红红成鸡屁股都没用。
总之呢,齐桓公想要通过葵丘盟会维护政治秩序,加强诸侯联盟关系,改善经济合作环境的政治理想,注定只能成为一大堆不切实际的空口号,纯粹面子工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很难实现,诸侯们也都对此不以为然,只有齐桓公自己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如今“诸侯莫违寡人,昔三代受命,有何以异于此乎”?所以想着更上一层楼,仿效传说中夏、商、周三代承受天命的圣王,率诸侯去泰山搞什么封禅大典(注5),这让管仲很头痛。管仲是商人出身,在他看来,有名无实,有害无利的事,都不值得去做。

所谓封禅,其实应该分开来讲,叫做封泰山、禅梁父。五岳之中,泰山为首。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或云云等小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这是古代帝王的最高大典,而且只有改朝换代、江山易主,或者在久乱之后,致使天下太平,才可封禅天地,向天地报告重整乾坤的伟大功业,同时表示接受天命而治理人世。从上古到春秋,历代封禅者有无怀氏、伏羲、神农氏、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汤、周成王,每一位都是大名鼎鼎的上古圣王,而齐桓公身为一个周室诸侯,却认为自己和这些受命圣王没啥区别,而欲行封禅之礼,这就等于是想放弃从前的尊王大业,转而废黜周室、僭越称王了。
当然,齐桓公这种僭越的想法,也是两周之交的一种普遍思潮所致。如前所述,西周末年,周幽王试图废黜申后母子以铲除周室中的姜姓势力,却被申姜反扑杀死,从此,中原诸侯集团的高层中就弥漫着这样一种论调:强大的姬姓周王室被姜姓西申国一举击败,绝不仅仅是由于周幽王个人的失误,而是天命已经抛弃了姬姓周族,转而开始眷顾姜姓族群(注6)。甚至就连春秋初期姬姓小霸郑庄公都悲哀的表示:“天而既厌周德矣,吾其能与许(姜姓国)争乎?”(《左传·隐公十一年》)
所以,当齐桓公取得了巨大的功业之后,自然会受此思潮影响,认为天命将抛弃姬周而转向姜齐。但是管仲却很清醒,齐桓公的功业虽大,但只是霸道,而非王道。所谓王道,即以超凡入圣的仁义道德感动天下,最终感动得天下人鼻涕一把泪一把地来归附,最终成为天下共主,这才是真正天命所归的受命者。
但这是不可能的,齐桓公还远没有那样的威望、德行与实力。硬要实施只会自毁大业,将好不容易初建的天下秩序彻底打破,到时候诸侯离心、群起而叛齐,齐桓公和管仲就是千古罪人。

孔子曾责管仲“器小”,只能辅佐齐桓成就霸业,而不能使之实行王道,殊不知春秋社会形式与三代之时大有不同。以当时之局势,谁都不可能王天下,只有四百年多后秦始皇雄才伟略,累秦百年之功,兼并天下,不行王道而成帝业,才能封禅泰山,成千古一帝。
总之不管怎么说,齐桓公虽然霸业卓著,离“王天下”还远的很,至少,南边的楚,西边的秦,北边的晋,都不会让齐国得逞。所以管仲苦口婆心,劝齐桓公收手:“封禅不是那么简单的,需要黄土高坡产的优质黍禾(注7)做供神的祭品,江淮地区产的三脊菁茅做拜神的席子。还得事先有祥瑞之兆,什么东海的比目鱼啊,西海的比翼鸟啊,还有什么凤凰啊麒麟啊嘉谷啊,林林总总共要出现十五种祥瑞才行。现在什么征兆还都没有,荒草乌鸦倒是一大堆,这样就去封禅,得被皇天后土笑掉大牙的。”
齐桓公一听原来封禅这么麻烦,顿时傻眼,无奈之下只好作罢。
其实管仲所言,虽然看起来像是推托,但句句都是大实话,古之封禅,的确需要祥瑞降世才能令天下信服。比如说黄帝属于土德,所以有黄龙和大蚯蚓出现。夏朝得木德,就有青龙降落在都城郊外,且草木长得格外茁壮茂盛。商得金德,所以山中竟流出银子来。周得火德,便有红鸟之符瑞。现在齐桓公啥德啥祥瑞都没有,即便自己声称承受了天命,难道不会失去它吗(无乃失诸乎)?
不过齐桓公还算是挺淳朴的,没祥瑞就收手了。后世帝王想封禅没祥瑞怎么办?好办,自己造,随便抓头鹿化装一下说是麒麟,在地里随便埋个鼎挖出来说是上古宝鼎,随便挖几个坑说是仙人足印,左右糊弄一堆屁民而已,这还不简单!
注1:天子一般尊称同姓诸侯为伯父或叔父,而尊称异性诸侯为伯舅。
注2:齐桓公当时年纪多大史书无载,但“耋”乃七老八十之意。而齐桓公此时已在位35年,其年纪在七十岁以上当不令人意外。
注3:故《吕氏春秋·慎势》曰:“先王之法,立天子不使诸侯疑焉,立诸侯不使大夫疑焉,立嫡子不使庶孽疑焉。疑生争,争生乱,是故诸侯失位则天下乱,大夫无等则朝廷乱,妻妾不分则家室乱,嫡孽无别则宗族乱。”
注4:成语“言归于好”源出于此。
注5:关于《史记》中所载齐桓公欲封禅之事,雷海宗《皇帝制度之成立》一文认为此乃战国末年齐国阴阳家邹衍一派编出来的传闻,事实上,就连“封禅泰山”这种提法,都可能是邹衍一派搞出来的,目的是宣传齐国必将王天下,达成齐桓公未竟的事业。不过,齐国公族出自姜姓羌人,而羌人原先生活在西北山地,崇拜山岳之神,泰山山神(天齐神)自然成为了齐国最重要宗教崇拜。其实泰山也不是很高,但黄淮地区乃平原,只在山东省中部与东部有一些丘陵,其大多数山体的海拔在几百米,只有泰山的主峰突然增长到1500多米,真可谓“一览众山小”了。

注6:参阅刘勋:《春秋十日谈》,四川人民出版社,2023年,第91页。
注7:黍乃五谷中最珍贵的一种。其籽粒大于粟,多呈金黄色,故俗称黄米。但历史上还曾有白、黑、赤、褐诸色(孙思邈《千金食治》),黑黍所酿成的酒是酒中极品,专用于祭神。因其珍贵,一般人平常食粟,丰年时才食黍,就算贵族阶层,也不见得能够天天食黍。故其亦是待客的主食,《论语·微子》中那位荷蓧丈人热情款待子路,“杀鸡为黍而食之”,唐代也见“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孟浩然《过故人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