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话语趋向于合流,道德话语趋向于分流。”波斯纳如是说。
 国内的研究
国内的研究国内对波斯纳的法律与道德理论的研究,可分为三类:

一类为直接研究此理论的成果。
李龙教授主编的《法理学》教科书从三个方面介绍了波斯纳的法律与道德理论:
其一,道德是地方性的;

其二,道德理论家提供统一的道德理论,从而无法为道德疑难的解决提供指导;
其三,波斯纳所推崇的是科学理论及“司法实用主义理论”。
高其才教授撰写的《法理学》教科书着重强调了波斯纳利用社会科学理论解决道德疑难的途径,他认为波斯纳的意见值得我们认真对待。

张芝梅教授介绍了波斯纳的道德是相对性、区分公共道德和私人道德的两个命题,阐述了波斯纳在解决道德疑难中求助于科学而非哲学的原因;
焦宝乾教授主要论述了波斯纳的道德立场,强调了波斯纳“道德理论与法律无关”的观点以及波斯纳对法律与道德关系研究的贡献。
苗金春教授详细地分析了波斯纳的实用主义道德怀疑论,介绍了波斯纳对强势命题的批判和对弱势命题的批判;

张金花从波斯纳的道德立场出发,总结了波斯纳的强命题和弱命题,并对波斯纳的实用主义道德怀疑论进行了批判;
刘韩静将波斯纳的法律与道德理论分为:波斯纳对道德理论、法律理论的批判以及波斯纳的出路是求助科学与实用主义。
她还论及波斯纳的法律与道德理论对中国的启示。

其核心启示可总结为:实用主义进路有助于开阔我们的事业,有助于中国法官了解外国法官的专业和学术素养,培养思辨精神。
另外一类为间接研究此理论的成果,其主要特点为,在论述波斯纳其他观点和其他学者观点的同时引出波斯纳的法律与道德理论。
其主要成果如下:
张芝梅教授通过论述波斯纳对道德疑难的描述来说明波斯纳的“没有基础的法理学”、疑难案件并不存在唯一答案的理论;

李霞教授讨论了德沃金对“芝加哥学派”缺少理论的批判,以及波斯纳对德沃金的回应,认为二人的根本差别在于法律思维路径之不同。
蔡宏伟博士从波斯纳和德沃金之争来分析法律的确定性问题。
他详细地介绍了波斯纳和德沃金在强命题和弱命题的往返回应,并认为,两人争论的焦点是司法的确定性问题。

即,在面对疑难案件的司法活动中,法官利用道德理论能否得到一个正确答案。
杨国庆博士在论述德沃金法律理论的同时,谈到了波斯纳对道德理论家的批判,并认为波斯纳的此种批判是自由主义范围内的批判;
徐品飞从基本的道德价值理念之争研究了波斯纳和德沃金关于道德理论的论战,结论是波斯纳和德沃金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都是“自由主义者”。

价值理念的分歧很细微,就像“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分歧”,真正的区别在于用以实现共同理想的手段。
同样,江兴景也细致地研究了波斯纳和德沃金的论战。
他认为,两人之争乃是法的道路之争,即法律应受科学引导还是哲学引导。

最后一类是对波斯纳实用主义的研究成果,并且笔者的主要关注点是对波斯纳实用主义方法的剖析。
通过搜寻研究波斯纳实用主义的书籍和以“波斯纳实用主义”为主题在知网、维普、万方等学术网站上进行检索,笔者主要得到以下文献:
张芝梅教授分析了美国法律实用主义产生的背景、历史沿革以及实用主义的家族类似。

而且她认为波斯纳的实用主义的立场有两个鲜明的特征:第一,强调实用主义注重对问题的解决;第二,吸收其他学科的知识。
成凡教授将实用主义的方法总结为工具论的知识论和结果论的证明论,认为波斯纳的法理学方法可以用科学和功利进行概括。
苗金春教授认为波斯纳的实用主义法理学进路是工具主义和语境论。

郑鹏程和聂长建教授详细地分析了波斯纳实用主义法理学“三位一体”的思想体系。
黄培云教授从实用主义与法律经济学的关系、法官的职业活动和法律和道德的关系的范畴,论述了实用主义的结构和演进。
伊卫风博士反思了波斯纳的司法实用主义存在的两个问题:结果主义与反理论。

张志文博士从法律发现的角度出发,认为实用主义司法观可以概括为:以逻辑传递着对发现的尊重,以经验护佑着对创造的追求。
高红将波斯纳的实用主义审判观总结为不以先例为义务、注重政策分析、向前看、结果主义导向和将裁判视为组织社会秩序的实践性工具等特点。
李天余将波斯纳实用主义法律推理的特点总结为注重后果,具有主观性、客观性、开放性,并且以合乎情理作为法律推理结论的标准。

 无法对道德进行客观性研究
无法对道德进行客观性研究波斯纳认为,每个人的道德直觉都是私隐的,这就意味着每个人都会得出不同的“道德知识”。
对于研究者来说,就不可能拿出充足的实验数据去证明一个人的道德直觉是错误的,也没有统计学的恒常,来证明某个道德论点的正误。
并且,道德是相对的,并不存在一个可供研究的道德实体,无从下手是每一个研究者需要直面的问题。

总之,我们生产不出一个清晰的、客观的道德知识。
那么,共识性知识我们能够做到吗?波斯纳对此也是否定的。
在波斯纳看来,是“共识创造了真理,而不是真理迫使人们形成共识”。

这也就意味着,在共识消退的美国社会,对于道德争议根本达不成道德共识。
更为重要的是,如果确实存在一个关于道德疑难的正确答案,道德理论家也没有一致的同意程序去决定哪种道德知识是正确。
如果没有办法获知的话,那么“确实存在”的道德公理对于人们来说,也是不存在的。

而且,道德理论家之间的道德真理也是互相矛盾的,形成不了像科学共同体那样的哲学共同体。
波斯纳质问:为什么世界上有如此之多的道德疑难?原因即在于“没有这样的技术,无法对道德探讨的前提以及对推理和检验具体道德命题的手段形成共识。”
正如麦金太尔所言:“在概念上的不可公度性,每一个论证在逻辑上都是有效的,或者,很容易通过推理达到这一点;

所有结论的确都源于各自的前提,但是,对于这些对立的前提,我们没有任何合理的方式可以衡量其各个不同的主张。
因为每个前提都使用了与其他前提截然不同的标准或评价性概念,从而给与我们的诸多主张也就迥然有别”。
简言之,在道德问题上,我们既无共享的语言,亦无相近的前提。

在此,波斯纳还列举了德沃金论证毕加索比巴尔图斯更伟大的例子。
在德沃金看来,美学是存在一个伟大目标的。
虽然我们每个人的偏好不同,但是我们却可以通过论证找到这个目标。

或者说我们最好相信有一个客观的目标,如此我们才能去追寻,得到更好的答案。
但波斯纳关注的不是这个问题,他关注的是“谁是更好的画家”这一现实问题,关注的是我们究竟有没有手段找到何为伟大画家的定义。
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说“我觉得巴尔图斯比毕加索更好”是犯了错误。

因此,以德沃金为代表的道德理论家更关注道德的目标,他们相信在各个道德疑难中是存在唯一的正确答案的。
他们告诫我们不能持外部怀疑论,因为过多地怀疑会让我们停止不前,只要我们不断论证并不断修正我们的观点,我们总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解释。
但波斯纳却不关心道德的目标,他只关心道德疑难的解决,只关心我们究竟有没有手段达致共同的道德目标。

如果波斯纳如此实用地看待道德,他就更倾向于把道德看成一种偏好。
这与美国当时的社会现实也是相关的,美国众多的道德争执其实已经演变成一种选择的问题。
比如在堕胎问题上,选择派和生命派便选择了不同的偏好——自由和生命。

而偏好是根本不存在对错问题的,也不能经过推理去验证对错的。
就像一个人不喜欢吃香蕉,你不可能通过论证香蕉是好吃的,来论证他的偏好是错的。
所以,所谓的“正确答案”也只是异想天开。

总之,在波斯纳看来,除非我们的社会存在共识,否则我们不可能通过推理得到某种共识。
这也就意味着,共识是扎根于文化的、个人情感的、生物本能的,却永远不会是论证出来的。
不仅如此,越是讨论,我们的分歧就会越大,因为我们本来就如此不同,因为我们每个人的偏好“神圣不可侵犯”。

那么科学呢?由于不同价值之间的不可通约性,科学也无法处理真正的道德冲突,但它可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解决“目的与手段”之间的合理性,从而解决一些道德问题。
波斯纳认为,当一个道德主张基于一个可检验的经验假设时,或者当这些道德主张的理由是一个功能性的理由时,我们就可以用经验证据来检验道德知识。
“如果把少女投入火山的唯一理由就是为了使作物生长,经验性研究就会消除这种做法”并且。

在波斯纳看来,尽管人们在道德理论上经常不一致,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在处理具体的道德疑难时同样如此。
换言之,每个人的道德理论不同,具体的结论却可能相同。
正如孙斯坦所言,尽管人们对是非善恶存在不同的理论,但对于如何解决具体案件却往往可以达成一致的。

这就为科学提供了用武之地。
另外,正如上文所言,波斯纳更看重经验性地研究道德背后的故事,人类学、心理学、经济学、生物学、数据建模等学科的研究,会给我们带来了众多有趣的知识。
或许它们得出的结论并不完全正确,也有可能无法得到验证。

但相较于道德理论,它们已经得出了更多关于道德的知识。
道德理论工具的匮乏,也就决定了它在“关于道德的知识”的生产上,难望科学之项背。
可以看到,波斯纳之所以求助于科学并不在于科学完全能够解决道德疑难,而只在于科学能够提供一些背景知识并且科学是比道德理论更有前途的学问。

在知识欠缺的情况下,道德疑难根本无药可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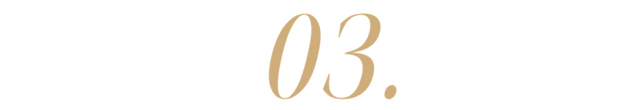 道德统一具有危险性
道德统一具有危险性在《道德的谱系》一书中,尼采指出,好与坏相对主义的起源乃是:“某个上等的统治阶级在与低贱阶层、下等人发生关系时所具有的持续的、主导型的总体感觉与基本感觉”。
换言之,流行的道德价值都是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群体的权力意志的表现。

显然,波斯纳追随了这一思路。
在《性与理性》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斯纳笔下的天主教会为满足教义的告诫,认为肉体是可耻的,将一切非生育的性活动都扫地出门。
在维多利亚时代,1806年,“因肛交而被处死的人超过了因谋杀被处死的人”;对于维多利亚人来说,自慰是一种精神无序的严重症状之一。

同样,同性恋也是邪恶选择的结果,并被归为某种意志堕落的犯罪。
因此,在波斯纳看来,文明的另一面是压迫,我们应该时刻对此保持警醒。
波斯纳认为,我们的社会需要的是道德多样化,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善良”。

他指出,“尽管没有这样说,但每个校园道德家都认为自己的进路是正确的,每个人都应当遵循他的进路”,温情脉脉的道德理论背后是对不同道德观念打压、指责与同化。
不仅如此,在波斯纳眼中,道德理论家的观点是与个人生活相连的。
就像康德的道德观点,他认为自慰、肛交以及其他非阴道性活动都是非道德的。

他对该观点的论证基于其对自然的两个假定:一是,动物并不进行这些行为;二是,性的自然目的即是生育。
波斯纳对此观点的评价是,康德的观点建立在虚假的事实之上,并且作为一个单身汉,康德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他所在社会对性的官方观点。
在前面的论点中,波斯纳就曾指出,道德理论家对于道德问题并无令人信服的答案,这个世界并不存在完满的道德观念,那么为何不让众多道德观念任意发展、恣意竞争呢?

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出,波斯纳更情愿把道德当成一种偏好来看待。
作为密尔式自由主义的信奉者,他自然主张宽容这些偏好,而不是去说服或者利用权威“改进”他人的道德。
此外,波斯纳还认为,道德统一的社会是令人烦倦的、是缺乏弹性的、是没有创新性的。

在他看来,“道德的近亲繁殖也许与生物的近亲繁殖同样危险”。
如果把视角转化到法官,另一种道德统一的危险就会被揭示出来。
在《法官如何思考》中,波斯纳曾提到法官们具有“异议厌恶”的倾向,所以,道德多数会轻松掌握住法院的话语权,法官道德同一也就在所难免了。

道德统一的法院,在波斯纳眼中,对道德观念异质的美国无疑是弊大于利的。
因此,波斯纳认为,“如果我们还想对法官制定法的茁壮保持信心的话,那么,我们真正需要的则是不同类型的法官”。
最后,波斯纳指出,我们应该看到悲剧的价值、我们应该欣赏冲突的意义。

在他看来,生命中的悲剧因素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悲剧的境况亦是法律经常要处理的。
可以看出,波斯纳欣赏的是尼采式的审美——酒神悲剧的背后孕育着幸福和超越。
从另一个隐含的层面讲,波斯纳在分析性态时就表现出了对福柯的部分赞同,即众多关于恶的概念是社会构建出的,而非自然的。

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时刻警惕的社会现实。
笔者认为,波斯纳对道德统一的反思是深刻的。
他看到了自由主义同样存在集权主义的风险,并且常常以善良的面目展示于人。

他提醒我们尊重恶、尊重多样性,他提示我们压迫无处不在,规训从未远离。
或许我们应该谨记尼采曾对我们的劝诫:“假如人类永远无法企及那原本可以达到的强大与卓越的顶点的话,那么,是否恰恰就是因为道德的罪过呢?
那么,是否恰恰说明道德才是危险中的危险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