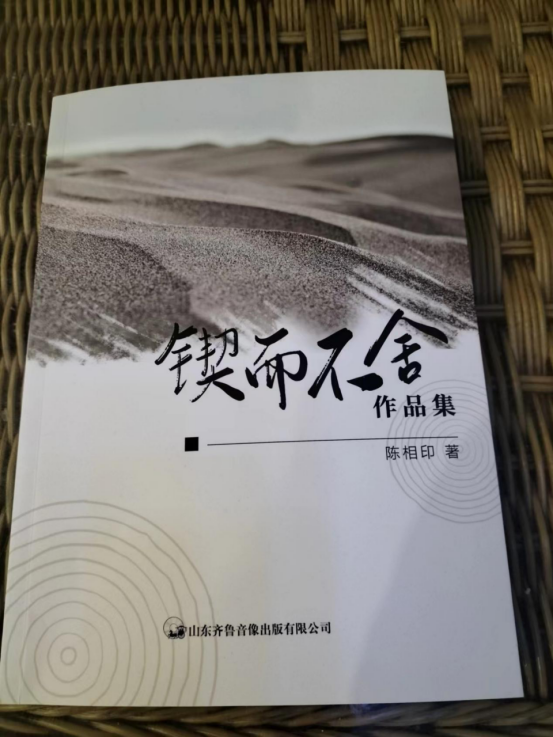稿痴
锲而不舍
高敬轩就是个普通的农村老头,一辈子笔耕不缀,每年在报刊杂志和公众号都有发稿,最多的时候有上百篇,少的有几十篇。就是生命的最后几年发表的作品很少。他一直没有出过书,他儿子为他出过书,但他没能亲眼目睹。据他说:“心疼几万元的出书款。”
他发表过的文章都贴在一个厚厚的大笔记本上,逢人便拿出来炫耀。他还会摄影,时不时有图片在报刊、杂志发表,也当做稿件一样粘贴。他的大笔记本我看过,后面还有厚厚的空页。他自信的说:“预备粘贴新发表的作品的。不够了在补。”
当有人夸赞时,不管是不是真心话,他都激动不已,脸上甚至绽出块块红云,恨不得留人在家吃饭。真要有亲戚朋友在家吃饭,话不到三句,高敬轩就拿出自己的大笔记本,叙说笔耕的辉煌过往。时间一长,村里人给他起个外号“稿痴”。
这个外号还颇有文学味,据说是村里出来的一名大学生起的。但高敬轩没有觉得不好,反而认为对自己“恰如其分”,甚至是对自己辛勤笔耕的夸赞。因此,这个外号就越传越广,在当地,三里五庄都知道了“稿痴”。
1
我与高敬轩相识,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当记者的时候。到他们村里采访过,有过一面之缘。当时是采访“三夏”丰收,我还是见习记者,特别是摄影刚学,还是弱项。高敬轩就自报奋勇,拍了几张图片,有两张图片随文一块发表。我没想到,他家里还有个小暗室,高敬轩自己还会冲洗。他告诉我:“当兵时在部队学的摄影和冲洗。”
那时,我们记者也有编辑通讯员稿件的任务。一天下午,高敬轩拿着一篇总编室已经退回的稿子找到我:“响应国家节约的号召,我们乡政府开个食堂,不在外面吃饭了。我听说后写了篇短消息,乡长看后还夸我呢。没想到,退稿了,这回去我怎么交代。”我拿过稿子仔细看,发现他还是有一定文字功力的,事实叙述的很详尽,但太长了,有接近1000字,当时记者的消息一般控制在800字以内。并且标题起的太平淡。我拿起笔,“刷刷”的删得剩下500字,并加了个引题“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丝一缕,恒念物力维艰”。我删字的时候,就看到高敬轩脸上“敝帚自珍”的惋惜之情,当看到添加的标题,他又喜笑颜开,大声叫好。重新投稿,这篇短消息竟然在二版头条发表。
高敬轩高兴坏了:“这是我第一次发头条!”喜滋滋骑了几十里地的自行车,到报社请我吃饭。看他一身尘土和汗水,我开始坚持不吃。高敬轩急了:“我们乡长叫请你吃饭的。”我明白,他一个普通农民,不一定能和乡长搭上话,但看他着急,就答应吃饭。就在路边一个小摊上吃饭,花了不到50元。我也是农村考上大学的孩子,知道农民的辛苦,偷偷地结了账。但饭后高敬轩拉着我,死活把50元钱塞到我手里。
从此,我们就熟悉了。我们的市级党报成了他主要的发稿园地,他经常骑着自行车送稿件。我劝他:“几十里地,不用那么辛苦,邮寄过来也可以。”高敬说:“新闻稿件有时效性,不能耽误了。”我说:“那也不用骑自行车啊,那么远,也有公共汽车。”高敬“嘿嘿”笑笑,不做声。后来,我知道,他家里比较困难,舍不得经常买车票。他也送一些散文、诗歌、图片等,还是一如既往的骑自行车。“稿痴”的名字也传遍了报社。
一年后,我奉命创办“农村园地”,每周一出版,高敬轩成了发稿最多的通讯员。版面也确实需要来自最基层农村的声音,高敬轩的稿子和图片为版面增色不少。有一次,刊发记者采写的“交公粮”(当时还没有取消农业税)的综合消息。高敬轩根据自己交公粮的实际,也写了一篇交公粮的现场短通讯,还配发了两张图片。至今我还记得精彩的一段:“粮库有两层楼高,一块窄窄的木板斜斜地架在地面和粮库口。交公粮的农民背着百十斤重的粮袋,一步一步攀上去,木板还晃晃悠悠的。木板上撒有小麦,防滑还得脱掉鞋。每上一趟就出一身汗——”年底,高敬轩荣获了报社最佳通讯员称号,还在表彰大会上发言。我记得那是他最高兴地时刻。
有人说他赚了不少稿费,我也负责通讯员的稿费签发。当时稿费低廉,千字20元。高敬轩的每篇稿子或图片就是10元、8元的,靠这生活,只有喝“西北风”了。但高敬轩不在乎稿费:“文章或者图片能发出就是最高兴的事,我从来没有指望稿费赚钱。”
不为名,不为利,写稿干什么?我们交往中,我也逐步了解了他的写作动机。他高中学习成绩优异,但高考发挥失常,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就立志写作,有和考上大学的同学“试比高”的劲头。他给我看过一个发黄的小本子:“你看,我高中作文就特别优秀。这是我根据白居易的长诗《琵琶行》改写的散文《琵琶行》,老师认为很优秀,把我的作文本在几个班里传阅。我平生第一次获得这么大的荣耀。这个本子我一直保存着,死了也得放棺材里。”
我也了解到,高敬轩还被乡里临时聘用过。那时,养猪还是散养,各户自己杀猪。村里一户人家杀猪卖肉,到集市上发现猪肉的颜色不很正常,怀疑是瘟猪肉,就果断地拉回来不卖了。高敬轩听说后,写了篇短通讯《卖猪记》,称赞这家农户为大众健康考虑的高风亮节。没想到,《河南日报》竟采用了。但乡里因为编制问题,最终也没正式聘用。但能在省级党报发文,绝非轻易而举的事,所以,他的写作热情越来越高。
高敬轩还有机会离开黄土地的。乡里聘用不成,又到村小学当了半年的民办教师,熬几年也能转正,但教育资源整合,村小学和乡小学合并了。他不得不放弃了教鞭。在部队,他仍然是优秀的通讯员,还学会了摄影和冲洗。高敬轩惋惜地说过:“本来要转文字干事的,可百万大载军,一声令下就回来了。”
2
进入新世纪,高敬轩和儿子一起出去打工了。他给我来信,自豪地告诉我他打工的地方是北京,具体是承建“鸟巢”。当时,“鸟巢”没有北京奥运会后出名。
繁忙的打工之余,他还不忘笔耕,新闻稿没有了,但不时有散文、诗歌发表,但数量少多了。我也离开了记者岗位,但他仍然经常和我联系,那家报纸、杂志发表了他的文章,都一一告诉我。每次我拿着他发表的文章让同事阅读时,不少人赞赏后嘀咕:“一个打工农民,写什么稿啊。”我也写信劝他打工辛苦,注意休息,少写稿吧。他回信说:“就喜欢写稿,几天不摸笔,手就痒痒。”
最让我最惊奇是,一天,我在办公室翻阅《人民日报》,突然发现六版上有四张“鸟巢”建筑工人辛勤劳作的图片,摄影者赫然写着“高敬轩”三个字。我准备发信祝贺他。第二天就接到了他的来信,说是他在一家小照相馆冲洗的,施工队还特别奖励了1000元。我想,这可能是是高敬轩最“高光”的时刻。
“鸟巢”工程完成后,高敬轩又带着儿子去了天津新港。一次,我在报纸上看到举办农民诗歌大赛的消息,正好到天津公务出差,就约他见面。他带着儿子请我吃“狗不理”包子,看到消息很兴奋:“还有半年的时间投稿,我一定好好写,写好后你给我修改一下。”饭后吩咐儿子结账,告诉我儿子已经大小是个包工头了。
不久,我接到他的稿子,写的是农民工的辛苦和贡献,很有激情。年底,大赛公布奖项,一位农民模仿“鹅,鹅,鹅,曲颈向天歌”的短诗荣获了18万元的奖金。我写信安慰高敬轩。谁知他很看得开:“几十万篇作品参赛,那能那么容易获奖。我能参与就很幸运、很满足了。”
3
10年后,我下到高敬轩所在的县担任局长,不想,我们又凑到一起了,还成了“邻居”。
高敬轩快60了,也不打工,回乡了。他的儿子在县城开办了一家建筑公司。我局的院子面积大,用不完,又是黄金地段,招标建起了两栋商品楼,一半供我局干部职工住,一半面向社会销售。他儿子的公司中标,还购置了一大套,高敬轩就搬了过来。
远亲不如近邻。我们更是经常互相走动。高敬轩还是笔耕不断。但活动的范围小了,在加上年纪越来越大,稿子也越来越少,但更珍惜发稿的机会。一天晚上,下着小雨,他举着雨伞来到我家,兴奋地举着一家老年杂志:“老弟,这杂志一期就发我两篇,一篇散文,谈老人养生的;一篇诗歌,歌颂老当益壮的。还聘我为特约通讯员。”
我也为他高兴,根据他的写作经历和执着精神,写了一篇散文《稿痴》,在这家老年杂志发表。但他却有些不好意思:“写的不少,但水平有限,成绩不大。”
但类似的机会越来越少,不久,这家老年杂志停刊了。特别是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网文逐渐成了文坛主流,“穿越文”、“同人文”、“耽美”、“剑仙”等新文体大行其道,“打卡”、“沙雕”、“内卷”等网络词汇遍地开花,公众号层出不穷,高敬轩还是纯文学作品,被采用的机会越来越少。特别是绝大部分报纸、杂志和公众号都废弃了纸质稿件,都要求通过邮箱或者微信投稿,高敬轩根本不熟悉电脑,打字都不会,别说写稿、投稿了。照片更没有了,都用手机摄影了,他玩不转,干脆放弃了。
但稿痴就是痴,一天我去串门,发现他在孙子“指导”下,学习打字,一个一个字母的按下去,显得拙笨,甚至滑稽。他说:“写好稿子总不能光让别人打字。不行,我一定得学会,还要写稿、投稿。”
一年后,高敬轩真的学会打字、投稿了。虽然不是很熟练,但总算有模有样。但稿件还是没有被采用多少。他纳闷地问我:“那么多公众号,很多都说急着用稿,但投稿都石落大海,有的还回复一下,鼓励两句,有的干脆屁都不放。”我说:“公众号都有自己的调性和风格,你多看看以往的发文,尽量适应。”但我心里知道,以高敬轩的年龄和创作,要想适应很难,便鼓励他多给报纸、杂志投稿。他也照做了,但稿子被采用的仍然很少。
网络、博客等自媒体发展迅速,我劝他多在自媒体上发表,但高敬轩不熟练,用的也不多。
他常常翻着贴满自己文章的厚厚记录本慨叹:“完了,老了,跟不上时代了。”但他儿子告诉我:“父亲还是经常写,多数时间电视都不看,趴在自己屋里写。有时竟写到夜里一两点。我们家人劝他休息,他说,不行,写作灵感来了,刹不住车。”我也劝他多休息,他说:“这辈子就这点爱好,改不了了,发不出去,自己欣赏吧。”我还听说,他经常拿着稿子给一起健身的老头、老太太念。我局一位退休的老局长就很欣赏,两人很快成为“莫逆之交”。
高敬轩的儿子的公司越做越大,儿子成了一个远近知名的“大户”,所以,高敬轩的70岁大寿还是很排场的。寿宴上,我对他儿子说:“要想让老头子更高兴,你拿钱给他出本书吧。”儿子爽快地答应了,高敬轩高兴地连喝了几杯酒:“今天晚上我就开始整理自己的作品。书名就叫《稿痴作品选》吧。”
不过,很遗憾,高敬轩没有看到那本书。一天午后,刚午睡起床的高敬轩突发脑溢血身亡,但出版社赠送的20本《稿痴作品选》第二天才到。在我的提议下,这本书和他厚厚的笔记本,还有写散文《琵琶行》的作文本,包括保存的发他文章的报纸、杂志等都整齐地放在了棺材里。
作者简介:陈相印,大学中文系毕业,喜欢创作,以散文、小说、书评、剧本和影视评为主,“锲而不舍”是笔名,出版有《锲而不舍作品集》等。邮件联系13839997000@163.com,微信号wxid-p803wdjiamhl1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