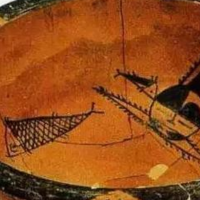当代艺术界纷繁喧嚣,作曲家武玮却像株独伫的松竹。她并非刻意标新立异,却因骨子里那份近乎执拗的“封闭”,让她在众声喧哗中显得格外清寂。恩师张广天曾在一棵青松下瞥见她的背影,惊觉这具纤细身躯中竟藏着一副“龙骨”——那是深潭下不灭的坚毅,是山野间呼啸的元气。这种气质,既非学院派的雕琢,亦非先锋派的锐意叛逆,而是某种更原始的生命力:一个拒绝被规训的灵魂,在艺术的旷野中自筑精神城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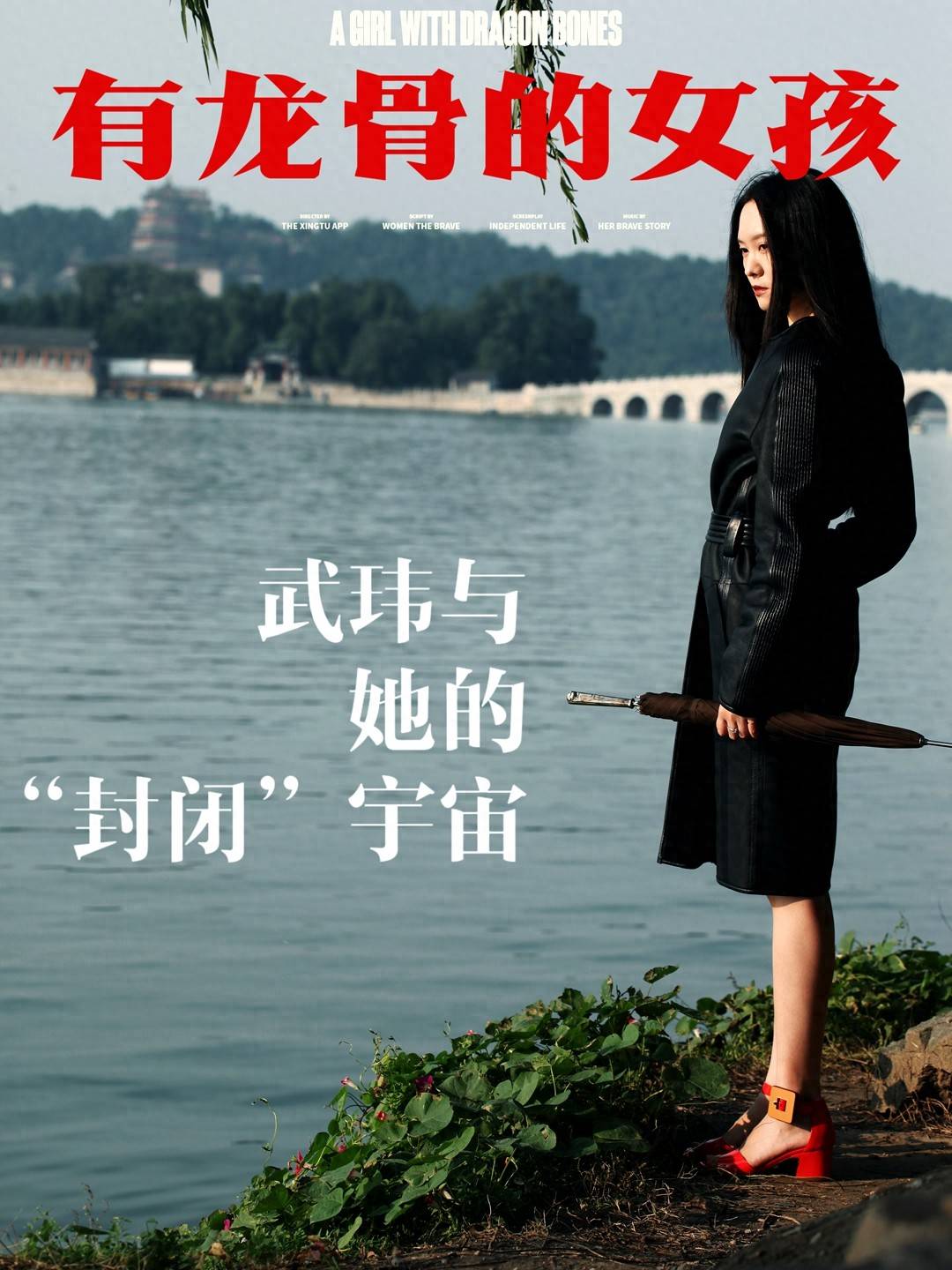
逃难的起点
武玮的艺术之旅,始于一场被动的逃离。少女时期,因出众容貌屡遭骚扰,母亲将她送往北京习舞。但舞蹈并非终点,毕业后的迷茫,让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踏入北京电影学院的考场。当主考官问及报考理由,她直愣愣答道:“因为没地方去了。”这份笨拙的诚实和她天生的灵性,意外叩开艺术之门。多年后回望,她形容这段经历为“逃难”,却也在颠簸中淬炼出对表达的渴求。

家族的戏剧血脉,早在她生命里埋下伏笔。作为民间艺术家的祖父,吹拉弹唱样样精通,因而家中常响着弦索叮咚。但那些锣鼓喧天的舞台,终究不是属于她的天地。年少羞怯的她,曾躲在床底躲避电视剧导演邀约,却在命运的推搡下,一步步走向更广阔的表达场域。
语法与龙骨
张广天初见武玮时,惊叹于她的“无知”——这份未被知识腌渍过的空白,恰成为最珍贵的画布。他教她“语法”:不是模仿的套路,而是将内在才情转化为语言的秩序。她近乎较劲地“啃食”着吉他、钢琴、和声学、作词、写文章的知识要义。明明打小不擅文辞与乐器,却在日日勤勉地练琴写作中,凭借这股子倔劲催生出专辑《真核》的惊艳。在她日益成熟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矛盾的武玮:她以古典的典雅守护交响乐的神圣,又以孩童般的天真打破形式的枷锁。她从不将创作视为东西方的拼贴缝合,只认作是“自性化”的自然流露——就像龙骨深藏于血肉之中,她的声音,皆从内心的封闭宇宙中喷薄而出,带着生命最初的炽热与真诚。
藏宝人的傲慢与谦卑
上海弄堂深处的元龙书店,曾是武玮心中的圣殿。那日,她看见自己的总谱与德彪西、马勒的著作并列于蒙尘的书架,她忽然领悟:真正的殿堂不在云端,而在市井烟火深处。这种认知折射出她独特的生存哲学:以知识为甲,却不沦为“知道主义”的囚徒;渴望作品被世人看见,却又坚信“贵重之物应如空气阳光般自然存在”。疫情封锁期间,别人焦虑于隔绝,她却如鱼得水——这个自称“内学之人”的作曲家,在闭关中让创作的根系扎得更深。正如她揶揄道:“守旧需要多大的财富?”这份守旧的奢侈,恰恰是她艺术创作中独特的珍宝。
不为注解而生的歌者
面对赞誉与批评,武玮表现出超乎年龄的漠然;“我的歌只为心跳共振,像一场恋爱。”她的创作拒绝被任何潮流裹挟。就像她笔下交响曲中那些交织的声部:不刻意解构,亦不锐意颠覆,只遵循内心灵性的指引。在张广天笔下,这个曾经“连手机都不会用”的弟子,总在完成不可能的命题。从为角色即兴创作《薄荷》,到用交响曲书写《日出地》的人类学史诗和《玉》的千年精魄,她以龙骨般的倔强将老师口中的“窄门”越拓越宽。

当年 20 岁的她,曾稚气宣言 “要让唱片放进所有书店显著位置”。如今的她,早已不再执着于此(她也早已做到),可她的声音,却在不经意间传得更远——因为真正的龙骨,从来无须宣告自己的存在。它沉默地支撑起整座山川,让每道溪流都奔向自己的海域。(编辑/王蕾 爱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