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14年秋,刘文彩的孙子刘小飞站在“收租院”门口合影,一脸平静。
但这画面却让无数人炸锅——这不是普通合影,这是恶霸后人站在“受害者控诉墙”前笑着摆拍!你说这像不像孙悟空在压他五百年的石头前自拍发朋友圈?

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2014年深秋,四川大邑县的天有些阴沉,空气里混着潮气和薄薄的霜雾。正值一个普通周末,大邑县安仁古镇迎来了一位特殊访客。
此人叫刘小飞,年纪五十上下,神情平和,衣着整洁,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站在“收租院”雕塑前的那张合影。这一幕,迅速引爆了网络。
“收租院”所在的位置不一般,它原是刘文彩老宅的一部分,坐落于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安仁镇,是一座典型的西式庄园与中式园林结合的大宅,建于民国时期,面积超过两万平方米,公馆共计27座。
这宅子后来被改造成博物馆,命名为“收租院”,自1978年正式对公众开放,主要展陈封建社会地主对农民的盘剥实录。

在这个博物馆里,最核心的展项是一组大型真人比例雕塑群,名叫《收租》。这组雕塑用27个农民形象再现旧中国农民缴租情景:一个背脊弯曲的佃户捧着沉甸甸的稻谷,旁边是佝偻着腰的老农、抱着孩子的妇人、低头叩拜的短工。
雕塑中神态各异,痛苦与压迫直观表达于脸部细节上,不仅传神,而且令人窒息。这不是艺术品,而是历史的“铁证”。

而站在这组雕塑前拍照的人,正是雕塑中“收租者”原型刘文彩的亲孙子。这张照片一经流出,立刻引发轩然大波。不少人觉得,这一幕太有戏剧性了,“祖上剥削,孙子参观”,仿佛历史跟现实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公众愤怒不是无缘无故的。刘文彩,这个名字在川南一带,可谓“谈虎色变”。他不仅是个经济大鳄,更是政治上的多面手。
从1921年开始,他借着弟弟刘文辉在川军中的地位,短短六年内,从一个地方烟酒局的小官一路爬升,兼任川南捐税总局总办、川南护商处处长等多个实权岗位。

这不是夸张。他在乐山、宜宾、叙府等地,强制开征的税种多达44项。
这些税收并非用于地方建设,而是直接进入了他的私库。据当时四川省统计,叙府一地平均每户农民每年被摊派的杂税在16项以上,且多以实物和银元计,负担极重。

到了1931年,他的财富已可与省府匹敌,仅在大邑安仁一地,他就控制了20余家银行、典当行、布庄与烟行。他的私人保镖团超过800人,还自组情报网与武装力量。
他的庄园中设有私刑室、拘押所、账房、烟库,每年从民间搜刮的粮食高达数百万斤。地方农民曾多次上书控诉,然而由于刘家与地方权力深度绑定,所有控诉无一回应。

而今天的“收租院”正是建立在这段沉重历史之上。雕塑、账本、租契、器物……这些展陈不是艺术加工,而是原物复制、史料支撑,是人民群众血与泪的见证。
可当年那位作威作福、霸占田地的“刘老虎”,在这天,被他的孙子以“观众”的身份再次拉回公众视野。
刘小飞的照片背后,是舆论的洪流。他既未公开说明此行缘由,也未对家族历史发表态度。这种沉默,被很多人视作默认,甚至是对那段历史的淡化和模糊。

历史的伤口并不会因为时间而自动愈合。尤其当“加害方”的后人站在“受害者”的回忆场景中时,这种画面往往会激起新的伤痕与不安。这不是一张合影那么简单,它承载着千百农民一生的苦难,也凝固着大众对于公正历史叙述的期待。
照片定格在深秋的清晨,雕塑面无表情,祖屋沉默不语。历史被按下快门,但那一刻,仿佛有人在心里响起一声叹息——不是我不明白,是这世界变化快。
刘老虎,真不是个外号
在四川人心中,能让一县百姓提起名字就心头发毛的,除了瘟神,恐怕就数刘文彩。人称“刘老虎”,不是外号唬人,而是真真切切用鲜血和尸体换来的“称号”。
时间推回到1927年,那年秋天,四川屏山县城南门外的农民聚集了一场数千人规模的抗议。他们不是什么流氓地痞,也不是造反贼,而是实打实的农民——种地的、挑担的、打短工的,喊出的口号却异常清晰:“反对烟厘捐,退还懒人税!”
他们的核心诉求只有一个:不要再强迫我们种罂粟了。

可刘文彩不干。他要收烟苗税、收烟土税、收加工税,这一整条黑色产业链,全是他私人的“提款机”。
农民的反抗,在刘文彩眼里,那是“动摇根本”的大逆行为。于是他一声令下,调来叙府驻军百余人,夜里突袭农会驻地,枪口对准人头,尸体扔在通江河口示众。
这还不算完。
1928年3月,叙府城区的农民自发在城区召开反苛捐大会。谁知会议还没开完,刘文彩便带兵冲进现场,开枪扫射,血染街巷。那一日,死者多为老幼妇孺。当天被抓者超百人,随后多被秘密杀害,剩下的戴枷游街三日,最后发配苦役营。
而1931年春天发生的“五人堆”事件,更是令全川震惊。那年3月,四川省委特派员梁戈、宜宾中心县委书记孔方新等5人在传达上级文件途中被捕。刘文彩命令将他们五人绑至宜宾南门旷地,白昼行刑。五人跪在地上,不发一言,被一枪一个打死。随后,五具尸体堆在一起,不准掩埋三日,用以“警示乡民”。

在刘文彩的治理下,川南地区“口不能言,民不聊生”成为常态。哪怕是地方官也得给他三分面子。原因很简单——有钱,有枪,有人,谁敢惹?
根据1940年民间统计,刘文彩在川西拥有良田3.6万亩、商号128家、地下库房存银逾百万两。他的财富规模,甚至一度超过当时四川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对这样的地头蛇,地方官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这照片,不该只是合影那么简单
2014年的那张合影里,刘小飞面色平静,身后是农民雕塑跪地求租的痛苦模样。这一张对比,不是一张“回忆”合影,而是历史的“锥心剪影”。
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一张照片能引起这么大反应?理由只有一个:中国老百姓吃过太多苦,尤其是被地主阶级盘剥的那段岁月,不该被忘,更不该被轻描淡写。
回顾刘文彩的“发家史”,从不是靠祖产,而是靠政治勾结。
1920年代,刘家搭上了军阀刘文辉这条线,开始疯狂扩张。刘文辉在四川军政两界如鱼得水,刘文彩便以“护商总局”的名义将税务、仓储、贷款一条龙搞起,从此脱离农耕,走上掠夺之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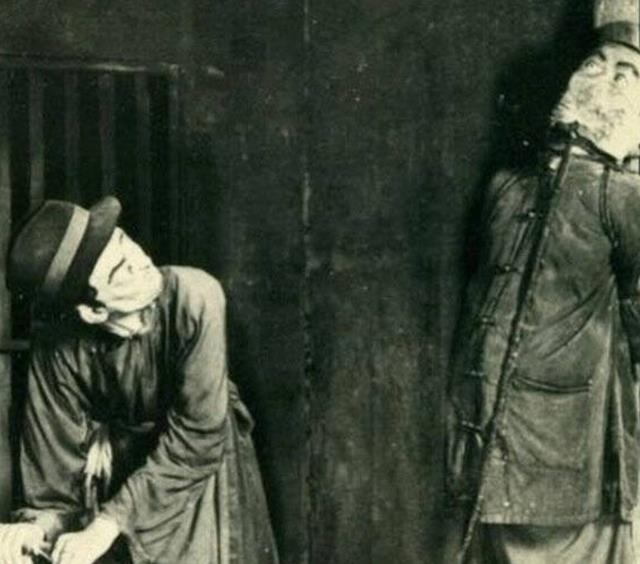
到了抗战时期,刘文彩又摇身一变,以“支持抗日”为名,在大邑一带强征“抗战捐”,实则搜刮民间存银。他从不参与战场,却频繁为军政要员“接风洗尘”,用金银珠宝巴结各路军阀。他在安仁开设刘氏当铺,用高利贷控制地方百姓,失地者只需三日,即被赶出祖宅。
正因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邑县数千农民主动上交材料、证词、租契,仅1950年两月内就形成超过4000页的“刘氏剥削档案”,成为后续博物馆布展的重要资料来源。
那张2014年的照片之所以引发公愤,不是刘小飞“来参观”惹了众怒,而是因为人们在这张照片里,看到了一个家族的“无言翻篇”,而这恰恰是百姓最怕看到的东西。
人们害怕的不是历史沉默,而是历史“被沉默”。

“收租院”依然矗立,但照片里的那个人,是否真正“看见”了那段历史,谁也不知道。他或许只是站在自家祖宅前,拍了张照,走了。但对更多人来说,这不是归来,而是提醒。
有些记忆,不能抹;有些罪行,不能轻;有些照片,不能只当作纪念——那是一张历史对照图,一边是旧世界的压迫,一边是新时代的觉醒。
参考文献:
刘文彩.百度百科.2025
所谓“善举”改变不了刘文彩的恶霸本质.历史评论,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