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出生率的下降,生育正从所谓的个人行为成为备受关注的社会话题。生育政策的变化更是从宏观角度折射出生育低迷的现状。而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她们为何选择“生”?又为何选择“不生”?阻碍女性生育的因素究竟是她们自己,还是整个社会环境?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社会学学者沈洋与蒋莱的新作——《新生育时代》,聚焦于中国都市女性的生育抉择与母职困境,填补了国内相关话题的空白,是一部立足于本土的性别著作。书中以细腻的笔触记录了不同代际女性的真实故事,涵盖了从70后到90后的女性群体。她们在生育、家庭与职业发展中的纠结与成长,展现了女性在社会转型期所面临的多重角色和挑战。
10月26日,沈洋与蒋莱两位作者携新作《新生育时代》在北京进行新书分享,与随机波动主播傅适野、婚姻家庭研究专家杨菊华共同探讨当代中国女性的婚姻与生育问题。四位女性从书中内容出发,展开了一场关于生育选择与母职挑战的深入对话,既有个人在时代下的婚育体悟,又不失理性的分析。现场的对谈活动也引起了大家的热议与共鸣,或女或男,都加入了关于生育行为与社会性别环境的讨论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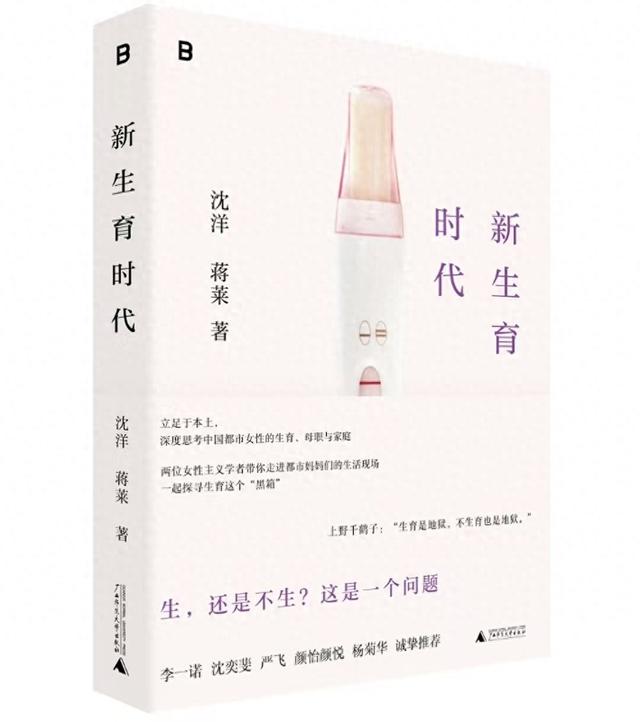
新生育时代“新”在哪里?
在对谈之初,傅适野对《新生育时代》的书名产生了好奇,想知道新生育时代究竟“新”在哪里? 作者蒋莱谈到,书名中的“新”字反映了自2013年以来,从单独二孩到全面二孩,再到全面三孩的政策转变,这些变化对人们的生育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育龄女性也发生了代际上的变化。70后、80后女性是非常期待政策变化的,甚至有很多人是在等着政策的。但是到了今天,这个育龄人口已经面向85后、90后了——人变了,所以新一代育龄女性是书中关注的对象。
作者沈洋补充说,新一代女性的生育理由也呈现出新的特点,她们更倾向于深思熟虑后做出生育决策。例如,书中受访者选择生二孩的理由是为了让孩子有个伴,而不是出于传统的男孩偏好或养儿防老的观念。
杨菊华从社会学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对书中的分析表示赞赏。她补充道,书中不仅展示了代际间的差异,还深刻洞察了婚姻生育现象。今天我们会想着我生不生?我要生几个?我什么时候生?这些在过去可能从来不是“问题”的问题,变成了问题。在现代社会中,生育和婚姻已不再是理所当然的人生阶段,而是成为需要慎重考虑的选择。另外,两位作者在研究的过程中也把自己作为方法,用自己的亲身经历与研究并行,跟受访者、读者产生共情。
傅适野也认为对于现在的年轻女性来说,生育以及生育选择甚至是走进婚姻这件事可能已经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现象了。关于父母辈的生育选择,他们会认为其实没有别的选择。但是到了现在,生育成了一个需要慎重考虑的事情,仿佛生孩子和不生孩子的人生是两种人生。
“母职惩罚”下的生育观变化
在《新生育时代》一书中,作者蒋莱、沈洋和杨菊华深入探讨了母职惩罚和性别税对现代女性生育选择的影响。母职惩罚这一概念在西方早已存在,而性别税则是杨菊华针对中国国情提出的概念。这些概念揭示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因生育而面临的额外挑战。
杨菊华谈到,性别税的影响不仅限于母亲,所有女性在求职时都会面临性别带来的困境。她通过研究发现,多生育一个孩子会导致收入降低,这种影响不分性别,男性同样会因参与育儿而遭遇职场困境。蒋莱补充说,父职惩罚同样存在,但社会往往忽视了这一点。沈洋观察到,随着二孩甚至三孩政策的开放,性别税对女性似乎有所加重,女性在招聘时受到的歧视似乎有所增加。
当成为母亲变成一种职场的“惩罚”时,女性的婚育观念也会受到影响。
蒋莱通过自己的教学经验,发现女大学生不少存在不婚不育的想法,而女博士生则表现出较大的婚育焦虑。她认为,这种焦虑可能源于年龄增长和家庭压力,以及完成婚育对求职的潜在好处。完成婚育的女博士在求职时可能会得到加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她们的婚育焦虑感。傅适野认为,这种现象恰恰反映出女性选择的有限性。尽管年轻女性可能在互联网上宣称坚决不要孩子,但她们内心知道总有一天可能会有孩子。这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实际上揭示了女性在生育选择上的困境。
同时,沈洋通过自己的观察,发现更年轻一代的女性对婚恋的需求有所降低,一些女学生甚至考虑非婚生育,并得到了家庭的支持。这也反映出中国结婚年龄有可能会进一步推迟。
单身生育还是丧偶式育儿?
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对于婚姻的失望情绪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现象,这种情绪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如《再见爱人》等探讨婚姻关系的节目的火爆。节目中,观众不仅仅是在观察夫妻间的矛盾,更是在寻找一种情感的共鸣和宣泄的出口。正如沈洋所指出的,现代女性在婚姻中的困境和对传统家庭角色的反思,使得她们开始寻求新的满足情感需求的方式,比如投身于乙女游戏,在游戏中寻找真实的情感体验。
杨菊华提到,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家庭传统,但晚婚晚育、少生不育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一个全球性的趋势。韩国的初婚年龄和生育率都是全世界垫底的,这正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中国,随着社会的发展,女性在教育和职业上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她们对于婚姻的期待和要求也随之提高。当现实与期待不符时,失望便随之而来。
在这种背景下,单身生育逐渐成为一些女性考虑的选项。虽然目前政策和实际情况还未将其作为主流趋势,但社会对单身生育的讨论和接受度正在逐渐提高。一些地区已经放开了对单身生育的限制,尽管在制度上仍有限制,但实际操作中已经有了一些灵活性。
傅适野认为,尽管单身生育还不是一个主流趋势,但这是女性可能会考虑的选项。这种想法也反映了近几年热议的“丧偶式育儿”的话题。大家可能会觉得有一个异性配偶仿佛等于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社会支持,那是不是可以凭自己的力量和一些女性照护者一起来养育孩子。这种想法和讨论反映了父职的缺失。

在绝望与失望之间摇摆的女性
在探讨现代家庭中父职的新形态以及如何协调家庭角色时,书中发现了一系列值得关注的变化。蒋莱指出,尽管父职参与度在传统上一直较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观念和家庭动态正在发生变化。虽然制度上的支持可能不足(如996的工作制),但人们的观念在进步,父亲的参与度在逐渐增加。她通过书中的例子——两位全职爸爸的出现,说明了这一点。他们在家庭中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这在几年前是难以想象的。爱意和育儿的投入程度是相关联的,让男性带娃带得越多,他在某种程度上也会越来越爱小孩子。
沈洋分享了书中的一个案例——一位父亲从沉迷于游戏到部分参与家务和育儿,展现了父职参与的转变。她强调,父亲的角色不仅仅是经济支柱,还包括情感支持和家庭责任。另外,家庭是权力斗争的场所,对男性提出要求和推动他们改变是必要的,即使这可能伴随着冲突和斗争。杨菊华也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了这一现象。她认为,尽管中国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仍然存在,但随着女性在教育和职业上的成就,男性的角色也在逐渐转变。虽然男性完全进入家庭还需要时间,但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男性开始参与育儿,这是一个积极的趋势。
傅适野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即社会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预期存在差异。她通过一个博主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这位博主的丈夫在成为全职爸爸后,家庭内部和外部的反应截然不同(丈母娘难以接受男性在家)。这反映了社会对男性和女性角色的不同期待。另外,傅适野强调,家庭作为一个持续的战场,需要不断地斗争和协商,才能带来实质性的改变。
沈洋也以幽默的方式提到了《再见爱人》节目对婚姻关系的维稳作用——好像给我们展示一些奇怪的男性,让我们会觉得自己身边的这个男性还不错。傅适野觉得这很诡异,它好像是利用了女性心态,因为和女性同步进步的男性确实变得很稀缺。尽管她认同两位作者所说的“男性是可以被教育好的”,但是每一个具体的女性可能会想为什么我要来教育他呢?为什么男女在婚姻中相遇之后,教育的责任反而在女性身上?当结构性不平等被分摊到每一个人身上的时候,女性要做的还是比男性多很多。沈洋同意并补充道,就算公司想要一个现成能用的员工,还需要花费成本用来培训。
蒋莱认为,我们首先应该追求人与人之间的基本平等。如果我们能够做到不物化对方,那么在更深层次的关系上,我们还是有希望的,我们应该保持信心。在该话题上,傅适野最后补充:“今天的主题似乎是在绝望和失望之间摇摆,我们都处于这个中间地带。”
冠姓权的争取与妇女友好型社会的构建
在分享会中,四位女性也深入探讨了冠姓权的问题,这是一个涉及家庭协商和性别平等的复杂议题。作者把“孩子随母姓”的动因分为四种:父权制的延续、孝顺型动因、性别平等型动因、一时冲动型动因。冠母姓通常由妻子家庭或者妻子提出,因为很少有男性会主动让渡自身利益,哪怕只是象征性利益。这些情况也涉及到女方家庭对小家庭的照护和经济投入,体现了一种反传统家庭的过度补偿现象。
蒋莱坦言,在沈洋提出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她没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她也认为这正是社会科学研究的价值所在,问题往往是被发掘出来的,而冠姓权就是这样一个被忽视的问题。过去这个问题并不被看作问题,但现在社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进展。
傅适野提到了《再见爱人》节目中的一个片段,其中男嘉宾杨子因女摄影师的一些言论而以威胁的口吻询问她的姓氏。互联网上的许多人解读,他实际上是在提醒女孩,她仍然隶属于父权制,暗示她不应以“越界”的方式与他交谈。书中讨论的随母姓的争取问题在这一刻就变得十分有价值。
此前的分享会中,蒋莱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对冠姓权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现在人们可以更开放地讨论这个问题。同时应该尊重个体的选择,让冠姓权成为一个自由选择的问题,而不是被传统观念所束缚;并且随着代际变化,未来对于冠姓权的看法可能会更加自由和多元。
几位嘉宾除了讨论冠姓权的争取,还探讨了生育和养育赋予女性的独特权利,并呼吁妇女友好型社会的建立。
傅适野提到,养育的过程,其实要求大人从孩子的视角来看待世界的。因为相对于大人来说,孩子其实教会我们从弱者的角度去看待世界。而大部分情况下,女性比男性有更好的共情能力。也许是因为在照料过程中,女性总是需要从弱者的角度出发,去理解他人的处境和困难,这让她们获得了更多的共情。而男性由于在生与育过程中参与较少,往往缺乏理解弱者的视角。
蒋莱说,她原本研究女性领导力,发现女性作为领导者时,往往能减少冲突和战争,更注重协商和寻求共识。这可能与女性数千年来的基因内在的照料者角色和站在弱者角度的视角有关。因此,她不认为女性是一个弱势标签,相反,它带给我们的是权利、独特的体验,甚至可能是更强的能力。同时,当社会提倡生育友好、儿童友好等标签时,我们也应该提倡妇女友好。在人造子宫尚未实现的今天,生育仍然需要通过女性来完成。我们需要将生育友好型社会提升到妇女友好型社会的高度,这样女性才能更敢于生育,没有后顾之忧,并且能够平衡生育者角色和职场角色。这是性别平等的文化诉求,也是鼓励生育和促进社会更加平等和谐的追求。
在提问环节,观众也用真实经历真诚发问。其中,有男性观众提问如何履行父职?沈洋以书中的例子(河南妈妈随夫流动到上海)回应道:“如果说给丈夫或者男性什么建议的话,你们能不能在考虑自己工作调动升迁的时候,也要考虑到妻子,双方协商能有一个最优结果,而不是以牺牲女方的工作为代价。”蒋莱认为,在亲密关系中,共同维护和提升关系、增强意识和学习是非常重要的。这不仅关系到你与配偶的相处,还关系到你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好父亲,理解孩子的情绪。在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中,男性可能需要放下一些旧观念,经常反思自己是否带有过时的“爹味”或普遍存在的自负倾向。杨菊华补充说,在夫妻关系中,无论是育儿还是家务,都不应被视为一种单方面的帮助。这不是“我帮你”的问题,而是分担。我们不是说一方在帮助另一方时给予了什么,而是要认识到这些都是两个人共同的责任。
也有人关心育儿的物质代价与尊重孩子主体性之间的关系。沈洋认为,尊重孩子的主体性并不一定需要高物质投入,认为“富养”是一个主观的概念,并强调尊重孩子的主体性并不一定要与金钱挂钩,例如让孩子自由玩耍就是一种低成本但尊重主体性的方式。蒋莱指出,如果不在孩子小时候提供兴趣班等教育资源,他们长大后可能需要补课,这同样需要投入。她强调社会应该尊重多元化的家庭形态和教育方式,并需要有相应的支持机制。傅适野认为富养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富足,更涉及精神层面;情感上的富足同样重要,家长应该让孩子感受到被爱和支持。
记者:钱欢青 编辑:徐敏 校对:杨荷放 通讯员:丁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