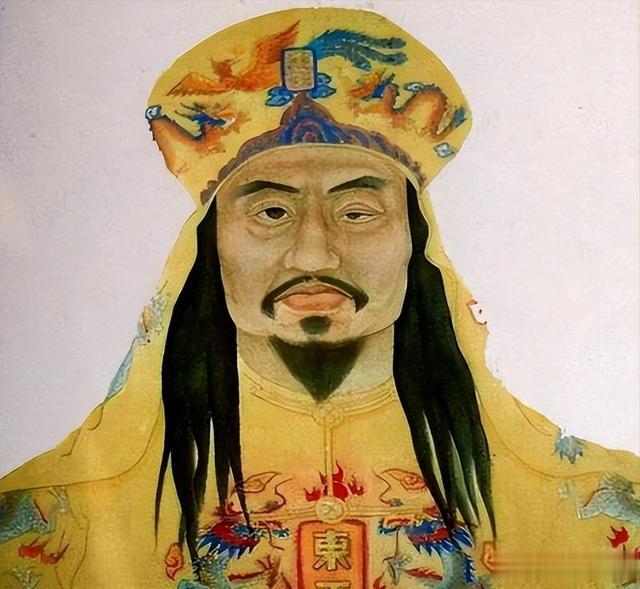《氓》《孔雀东南飞》,别轻易扯到男尊女卑、封建礼教上去

我们的语文教学似乎已经陷入一种固有的套路上去,一学外国小说,那就是揭露了资本主义的腐朽;一学山水散文,那就是歌咏祖国的大好河川;一学古代诗歌,那就是怀才不遇、壮志难酬……
一说到《氓》《孔雀东南飞》,两首弃妇诗,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男尊女卑,吃人的封建礼教……
定势思维,管它什么文本,主题先行,直接往上套。
文本讲什么无所谓,主题肯定就是这个,跑不了。
这种思维还是要不得,我们的语文教学亟需改变这一点,阅读理解,一定是对具体文本的理解,一定是对作者彼时彼刻思想情感的理解,不会也不应该套路化。
以《氓》和《孔雀东南飞》为例。
说这两首是弃妇诗,宽泛意义上是可以的,但如果较真,可能本身就算不上。
先说《氓》,准确地来说是婚恋悲剧诗或婚变诗,男子虽然“士也罔极,二三其德”,三心二意,用情不专,甚至“言既遂矣,至于暴矣”,还有家暴行为,但公允地来说,男子并没有“弃”的行为,女子刚强果敢,看到男子“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果断分手,及时止损,做了“出走的娜拉”。
这个女子是可怜的,也是可敬的,但若将其定性为“弃妇”,不仅不合乎实际情况,也是对其决绝果断精神的削弱和否定。
记住,我是“出走的娜拉”,不是被甩的白月光,要说“弃”,“弃夫”还差不多。
阅读,应忠实于文本,应基于具体的文章,哪怕文章传达出来的意思和我们头脑之中已有的模型不合甚至冲突,也应该忠实于文本。因为生活是具体的纷繁的事件场景,而不是固有的几个模型。就《氓》的文本而言,就不宜往男尊女卑、封建礼教上去扯。
首先两个人的结合算是自由恋爱,没有父母之命,也没有媒妁之言,“氓之蚩蚩,抱布贸丝。匪来贸丝,来即我谋”“匪我愆期,子无良媒。将子无怒,秋以为期”,不仅是自由恋爱,还是闪婚。
女孩子没有被强迫,而是全身心的投入,“不见复关,泣涕涟涟。既见复关,载笑载言”,用情至深,甚至恋爱脑了。
后来婚变,男子“二三其德”,女子“三岁为妇,靡室劳矣。夙兴夜寐,靡有朝矣”,任劳任怨,却换不回男子的浪子回头,于是“反是不思,亦已焉哉”,那就算了吧,一别两宽。
整个过程就是我们今天闪婚的翻车现场,似乎与封建礼教没有太多的关系。
再说《孔雀东南飞》,刘兰芝的被弃不是被丈夫焦仲卿抛弃,而是被婆婆抛弃,原因呢?文章并没有明说,只有几句“大人故嫌迟”“女行无偏斜,何意致不厚?”,大概是出于婆媳矛盾,婆媳矛盾自古有之,这就更不好往男尊女卑、封建礼教上去扯了。
今天的语境下,婆媳矛盾仍然存在,总不能再说什么封建礼教了吧。
刘兰芝被遣送回家后,她的母亲和哥哥立马为她张罗新的婚姻,虽然这种“热心”成了压垮痴情的刘兰芝的最后一根稻草,好心办了坏事,但正说明那时候女子离婚再嫁都还属于正常的现象,没有后来太多封建礼教的束缚,如果非要扯封建礼教,那可能就是焦母这位婆婆的大家长作风了。
婆婆太霸道,儿子儿媳妇一对恩爱夫妻成了最终的牺牲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与其说是弃妇诗,不如说是家庭伦理诗。
无论是婚变诗《氓》,还是家庭伦理诗《孔雀东南飞》,这样的场景虽在两千年前,但直到今天还依然不断发生着,这正是这两首诗的生命力所在,跨越时间,横亘古今。
无关封建礼教,只是历史的不断重演。
《孔雀东南飞》里有一句话,“多谢后世人,戒之慎勿忘”,后世人啊,那么一定要引以为戒,只可惜人类从历史中吸取的唯一教训就是从来不吸取教训。
《氓》里的女子和《孔雀东南飞》里的刘兰芝,一个遭遇婚姻不幸,决绝果断,及时止损;一个无端被婆婆棒打鸳鸯,最后夫妻双双殉情。
她们是可怜的,也是可敬的,千百年后我们再读这两首诗,我们应真诚地献上我们的同情和敬意,但若强行往男尊女卑、封建礼教上去扯,那就是对事实的不尊重,对两位女子遭遇的不尊重。
尊重事实,理性分析,就是对她们最大的敬意。
这是语文课应该有的理性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