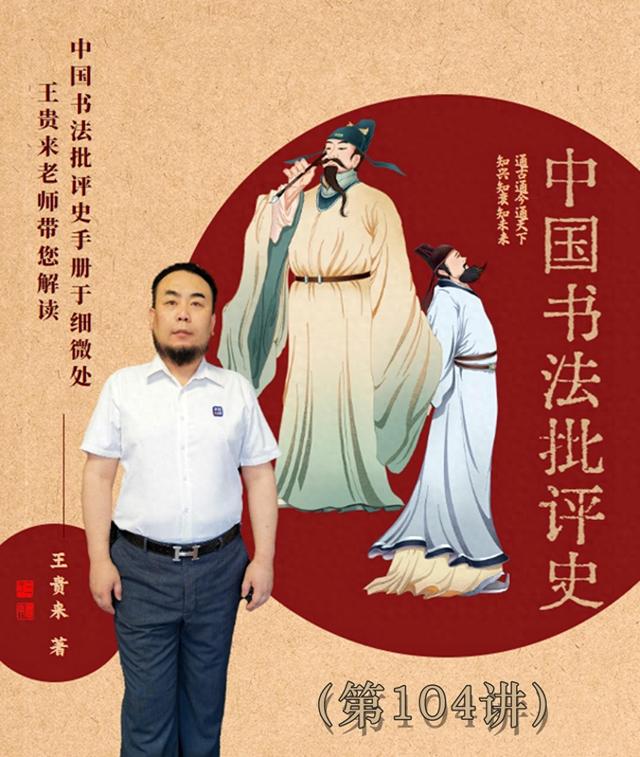
王贵来老师带您解读《中国书法批评史》第一百零四讲
第二册 宋朝、金朝书法批评
第二章 "探析苏轼与黄庭坚:文人书法中的艺术意蕴与美学追求"
第八节 黄庭坚论创新
三、书法的“意韵”“意象”
他们注重书法的“意韵”,有别于唐人所关注的“意象”,进而催生了全新的书法艺术思维。唐人通常聚焦于“意象”,呈现出强烈的情感宣泄和生动的字势,着重向自然学习。苏轼、黄庭坚则着眼于“意韵”,展现出细腻的思绪、优雅的韵律以及引人深思的效果。
书法艺术的创作动力也由激情转变为意兴。他们并不主张书法家向自然学习,苏轼觉得张旭从公孙大娘的剑器舞蹈中领悟到的只是用笔动作,而非形象,并且对雷简夫从嘉陵江水的暴涨声中体悟到书法的意象、文与可从蛇斗中悟出草书妙理表示难以理解。这种趋势造就了此后中国书法艺术创作的一种倾向,即更多地从前人作品里探寻变化的依据,而忽视师法自然。
作为一种以文字作为塑造对象的造型艺术,书法生命力的源头主要在于向自然学习,宋朝书法相较于唐人,总是略显欠缺生气与活力。追根溯源,也不得不从苏轼、黄庭坚这一代人的思维中找寻原因。苏轼、黄庭坚侧重“意韵”也营造出另一种境界。苏轼所说的“远韵”、黄庭坚所讲的“韵胜”,常常指作品的整体成效,与其他文艺形式中提及的“意境”颇为接近。
唐以前的理论所关注的“象”属于某些孤立、有限的物象,而“境”则包含“象”之外的虚空。就书法作品而言,不是突出某些笔画、字形的成效,而是更为注重整篇作品中每个元素之间的关联,包括空白处的韵律,这也是他们更倾向于魏晋书风的缘由之一。
苏轼和黄庭坚为书法设定了全新的标准。此标准依据变化、清新且契合文人的审美意趣而定,着重强调创作者的胸怀、抱负、学识修养等精神层面的价值,而不涉及“肥瘦”“工巧”。这一新标准无疑对古代书法审美价值体系进行了一次大革新,凡不符合文人趣味的书法皆遭摒弃。后世所尊崇的“文人气”“书卷气”,以及所排斥的“僧气”“俗气”“酸气”等,皆源于苏轼、黄庭坚的书法观念。
这些均可归结为“雅”这一艺术范畴。文人所理想的“雅”,与后来正统论者所说的“雅”存在差异。不妨看看近代马叙伦的阐释,他讲:“鲜于伯机的书法因雅胜过松雪,张伯雨虽不如伯机,但比松雪更显雅。我所指的雅,主要以山林、书卷为重点。具备山林、书卷的气韵,书法自然可观。”马叙伦对“雅”的诠释最契合北宋文士的理念。
而后来正统派的“雅”,更注重典章法则,更倾向于庙堂的气度。苏轼、黄庭坚虽未将历代书法家划分出三六九等,不过,他们构建了一个宽泛的等级体系,即“雅”与“俗”的差别。其间不再有唐人那种难以企及的书圣,也不再有森严的等级划分,甚至连普通的美丑之分也不复存在。就拿美丑问题来说,在唐朝及其之前是有较为客观的衡量标准的,当时人们的思维中有一个客观的参照,这个参照便是历朝所建立的名家体系,看重的是力量感、形式感等,能让普通人一眼便能感知,这个体系的美相对而言更为直观。
苏轼、黄庭坚则注重人品、学养等方面,不看重形式准则,或者说形式问题逐渐不再占据主导地位,这将书法的价值导向了作品的内在部分,要求欣赏者具备丰富的知识储备才能理解。甚至有些作品乍一看并不美观,却被视作富有内涵、具有水准,只因作品蕴含着创作者的智慧才华、文化品位等等。
苏轼、黄庭坚让书法艺术摆脱了昔日繁琐的教条束缚,恰似禅宗对佛教的变革,由此获得众多人的认可与支持,故而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大量追随者,对后世也造成了深远影响。我们只需审视一下宋徽宗主持编纂的《宣和书谱》,便能清晰地彰显出这一影响的深度。《宣和书谱》成书之际,正值苏轼、黄庭坚的文章字画被封禁之时,自然在这一书法谱系中寻不到苏、黄的名号。
《宣和书谱》中的诸多评书观点皆源自苏轼、黄庭坚,现援引数条,用作佐证。《宣和书谱》“李奚”条称:“其书于楷法之处可见,理应皆具胜韵。大抵饱学儒者,下笔毫无俗气,且暗合书法之道,此乃胸次使然。至于世间之学者,其字并非不够精巧,而气韵俗劣者,正是由于胸次之过,并非缺乏规矩。若奚能饱读万卷之书,那么其字岂能仅以循规蹈矩衡量,应当从气韵获取。”这番言论显然是对黄庭坚论书观点的摘抄。
《宣和书谱》“纽约”条道:“盖其字画虽小,却圆劲有成,不乏精神,令人欣喜。曾考往昔之人论字,认为大字难在结密无间,小字难在宽绰有余。结密无间,《痤鹤铭》接近;宽绰有余,《兰亭叙》接近。大概而言,纽约的小字,虽不足以与古人比肩,但就其字形的顿放而言,颇具意味,亦不局促于边幅而韵胜。”这一关于纽约的评语又是苏轼、黄庭坚论书言论的综合。
苏轼、黄庭坚的创新及个性化的书法批评观念,也受到同时代及后世部分理论家的批判,在后续章节中我们将对这些反对派予以介绍。(全文共计:1943字)

作者:王贵来(天津书画艺术网总编)
2024年10月14日星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