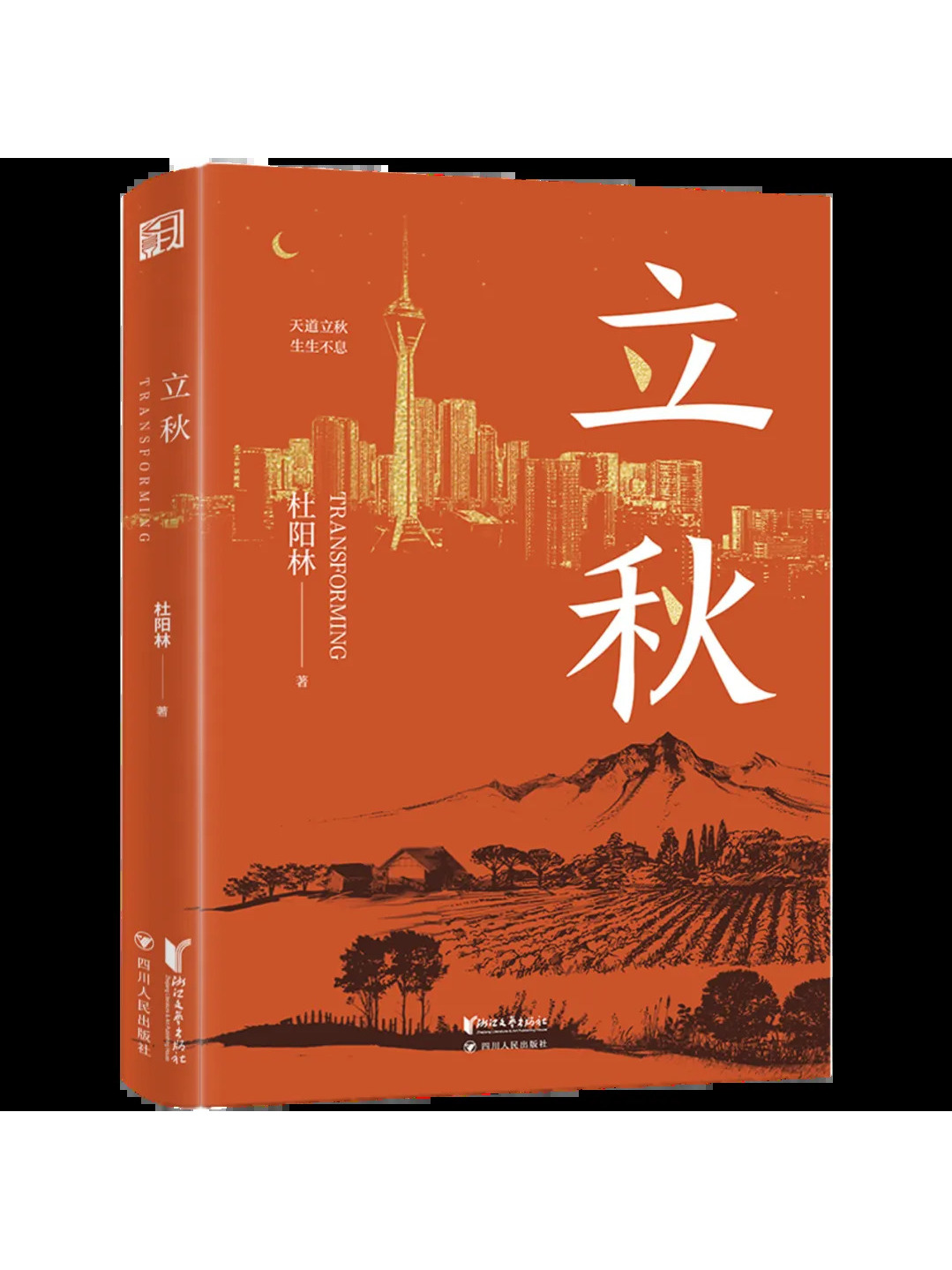
血土酿的酒糟味
这《立秋》里的盐碱地啊,像块浸透高粱酒的粗布,攥一把能拧出三代人的泪和汗。凌云青的脚底板踩着柏油路,鞋缝里却钻出红高粱的根须,夜半三更总听见老坟场的蝈蝈在报社铅字堆里打滚。他辞了铁饭碗下海开餐馆,锅铲翻飞的油烟里飘着观龙村祠堂的纸钱灰——城里人嚼着水煮牛肉,哪晓得辣子里掺了半辈子没还清的人情债。
狗链镀金的年月
创业这坛子酒,刚启封时飘着理想主义的醇香,窖藏三年就发酵成资本市场的酸醋。凌云青教乡民握炒勺的手势,活脱脱像他娘往腌菜缸撒粗盐,只是盐粒早被证券交易所的铜牛嚼成了金粉。那些标榜“扶贫”的餐饮学校,分明是把闰土的钢叉熔成镀银餐具,蘸着人血馒头教打工仔吞咽体面二字。最绝的是马家大院的算盘珠子,拨弄起来叮当作响,细听竟是祠堂梁木上吊死鬼的裹脚布在唱莲花落。
秋蝉驮着招魂幡
要说这书脊里藏着的鬼魂,可比高密东北乡的还热闹。霓虹灯下晃荡的哪里是西装革履的猹?分明是孔乙己换了副电子假牙,举着镀铬钢叉对准自己影子捅。凌云青跪在玻璃幕墙前磕头,水泥地缝钻出他爹的旱烟杆,烟锅里烧的不是烟叶,是证券交易所熔了的银项圈。立秋那天的风一吹,满大街飘着转基因的纸钱——这头印着餐饮学校的招生简章,那头画着王母娘娘的二维码,扫一扫能看见赵老太爷在云端卖茴香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