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避寒
编辑|避寒
《——【·前言·】——》
曾国藩提拔了一个人三次,换来的是三次军饷被截、一次近乎兵败的危局。
对方没有解释,没有退让,反而反手递了奏折,把朝廷拖下水,这个人叫沈葆桢。
他们曾是生死与共的师徒,后来,成了政治对手。
 “提拔三次,反噬三次”:曾国藩的湘军为何栽在沈葆桢手里?
“提拔三次,反噬三次”:曾国藩的湘军为何栽在沈葆桢手里?1862年,湘军围攻金陵,前线兵疲马乏,曾国藩在日记中记:“士卒欠饷,心思不定,贼势反勇。”
问题出在哪?钱没到,原定每月拨付的50万两军饷,只到帐了24万两。

是谁截了钱?沈葆桢。
这一年,他是江西巡抚,他说得明白:“江西自顾不暇。”便直接下令停运部分厘金至前线。
没有报备,没有请示,曾国藩是那一刻才意识到,这位昔日门生,已经不再听他的了。
一年后,1863年,曾国藩换了个办法,避开沈葆桢,从九江关道蔡锦青手中调款3万两,用于前线伤兵医药。
账刚拨出,蔡锦青便半夜被请去沈葆桢衙门“喝茶”。
沈说得直接:“谁让你拨的?”蔡说:“曾大人。”沈冷笑:“我撤你,你信不信?”

第二天早上,款项原数退回,蔡锦青跪在曾国藩门口,说:“巡抚要杀我。”
曾国藩只能忍,他写信给沈葆桢,措辞温和,沈不回信,转头却向朝廷请示,要“厘金由地方自用”。
曾国藩第一次意识到,沈葆桢不仅有胆量抗命,还在争夺财政控制权。
1864年,太平军残余退至江西边境,湘军追击,军饷告急。
曾国藩向朝廷申请将江西厘金直接划拨前线,沈葆桢抢先一步上奏,要求厘金“对半分”。
朝廷批复:“一分为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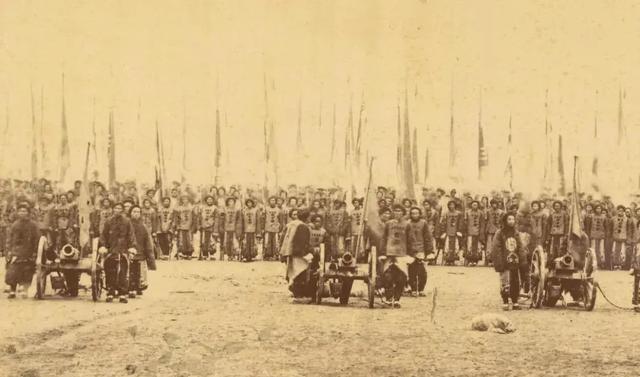
曾国藩震怒,湘军将士欠饷十余月,军心涣散,将领骂沈是“绝无良心科”第一名,这是公然对抗。
他写信斥责沈葆桢“背义忘恩”,沈未回信,仅回复一句:“江西疲敝,不堪拨银。”
他不是在讲理,是在划地盘。
 “我知有国,不知有曾”:沈葆桢的算盘
“我知有国,不知有曾”:沈葆桢的算盘江西不是没有钱,厘金征收制度本就严苛,港口、城镇、关卡都设有征收点。
1862年,江西厘金年收超过400万两,但沈葆桢上奏称“国库空虚,无银可调”,前线只分到24万。

他把其余银两干了什么?三件事:练兵、修厂、搞情报。
团练一扩再扩,原定万人编制被他推到三万,超员者仍给粮饷。
银子下到县,点兵册与实数不符,账面调度三千,实到五百,差额去哪了?衙门、商号、军头三分,朝廷不查,曾国藩不敢查。
沈的理由很硬:“江西腹地,贼患未平,守土有责。”他抓的是“不得罪天子”这个底线。
曾国藩能灭太平军,靠湘军,而湘军,要钱,钱从哪来?厘金,谁握住厘金,谁就握住生杀大权。
沈葆桢的底气来自另一个角度,他是林则徐的女婿,福建人,根基不在湖南,他不想也不能依附湘军系统。

他知道,太平军一亡,曾国藩将成为“异姓王”一般的存在。
他不要被曾国藩一锅端,也不想做其羽翼,他要站到朝廷那一边,站在曾国藩的对面。
他做得极稳:
银子截,但事由充分:江西军需、自保边境、稳定地方。
信件不回,但奏章必快:曾国藩私信来,他不答。朝廷问,他马上回。
团练扩编,但留出余地:不建“军”,只建“练”,一字之差,规避“私兵”之嫌。
他让湘军失血,却让自己合法。
他在赣江修造轮船,学的是西洋技艺,船政的图纸从广州转道送来,江西不是造船省,他偏要造。

为什么?不是为了海防,是为了“眼界”,他要让朝廷看到:“我不是地方守将,我是能开洋务的人。”
军饷不拨是“硬”,船政、练兵、财政整顿是“软”,他不当反叛者,要当改革者。
同治四年,他上奏《江西军务备览》,自述“团练不扰民,船政自筹银,赣南粮价稳定”,朝廷批示六字:“可为诸省范。”
这不是平衡,是翻盘。
从一个被曾国藩三次推荐的门生,到截饷自立的巡抚,沈葆桢用了三年。
从地方军政“独裁者”,到中央信任的改革样板,他用了五年,他不靠曾国藩,靠朝廷,也靠自己造的那张局。

沈不是狠人,他是冷静的手术刀,他砍的是湘军的动脉,救的是自己和江西。
他把“忘恩负义”这四个字,从私德层面,拔高到政治层面,他从不争解释,因为他早就算明白:
“个人的恩义,永远抵不过体制的态度。”
 “忍住不打,是为了不败”:曾国藩的隐忍与困局
“忍住不打,是为了不败”:曾国藩的隐忍与困局曾国藩不是不知道沈葆桢在做什么,他早就察觉了,早在1862年,他在私信中就提到:“江西恐有异心,不可过问。”但他选择不动。
他不是不敢,是不能。

一旦动,前线崩了,朝廷震怒,战局失控,他输得起面子,输不起大局。
沈葆桢也知道,他赌曾国藩不敢翻桌,于是更强硬了。
有人建议曾将沈调职,他没奏请,他知道沈站在皇帝背后。
咬牙吞下,也许,是他一生最屈辱的一口气。
他有个底线:不让湘军自己乱,他安抚将士,自己倒贴银两,一次拨银十万两,他亲笔写:“宁折吾身,不乱吾军。”
他知道,沈葆桢在走朝廷那边的线,他只能做一个“听话的功臣”,给朝廷留下“可控”的印象。
曾国藩忍下的,是功高震主的惩罚。
那年冬天,他写信给李鸿章,说:“功成不居,是为保命之道。”他不是不知道尊严,只是,他更清楚规则。

他曾是权臣,现在,是活着的权臣。
1865年,太平天国灭亡,曾国藩调任两江总督,沈葆桢升为福建船政大臣,继续扩充势力。
有人说机会来了,可以削沈,曾国藩什么也没做,他去金陵拜庙,写诗,写书,他退得很干净。
不是放过沈葆桢,是放过曾国藩自己。
 “不顾恩义,只顾活着”:历史如何看待这场反目?1.湘军视角:沈葆桢是“背信弃义”的代名词
“不顾恩义,只顾活着”:历史如何看待这场反目?1.湘军视角:沈葆桢是“背信弃义”的代名词湘军中流传一句话:“江西沈某,绝无良心。”不是骂,是实录。
将士欠饷,战线拖延,一切都能归因于那个停止拨款的人。
有人骂他是“忘恩者”,也有人说他是“自保者”,曾国藩没再提他,他选择性失忆,历史没忘。
 2.朝廷视角:沈葆桢是那根“拴住湘军的绳子”
2.朝廷视角:沈葆桢是那根“拴住湘军的绳子”沈葆桢截饷、独断,是不是越权?是,有没有被治罪?没有。
反而仕途平步青云,福建、台湾、两江,越走越高,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一件朝廷不敢明说但必须有人去做的事:卡湘军脖子。
太平天国覆灭后,湘军坐大,朝廷最怕的不是敌军,是自己人,沈葆桢截饷,就是敲山震虎。
他不只是在护江西,他在做一件更大的事:把曾国藩拉回体制里。
 3.沈葆桢的辩词:一句话,堵死恩义争议
3.沈葆桢的辩词:一句话,堵死恩义争议“予知有国,不知有曾。”
沈晚年写给弟子的信中,就这八个字,没解释,不辩解,摆明态度:我不认私恩,只认朝廷。
这句话不是在否定曾国藩,是在告诉后人:我站的是体制,不是人情。
现代学者评价沈葆桢时,用的词不是“忠臣”,是“政治动物”,懂局势,敢博弈,能站稳。
他没有输,他在走钢丝,但始终没有掉下去。
 4.曾国藩最后的写照:功臣,但不自由
4.曾国藩最后的写照:功臣,但不自由他一手建湘军,一手灭太平天国,封侯加爵,万人敬仰。
但最后十年,沉默、清谈、写信、退隐,他不再主动插手政务,也不再提沈葆桢。

他的成功,不是赢了谁,而是没有输给体制。
他曾试图建立一支忠于大义的军队,最后却发现,最先叛变的,是他最信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