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嘉二年(308年),刘渊于左国城(今山西离石)称帝,国号为汉,史称汉赵,又名前赵——这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建立于中原内地的外族政权,更在八年后灭掉西晋,把司马家的残渣余孽撵到东南半壁苟且偷生,是为五胡之乱肇始。

此后千多年,无数仁人志士为之痛心疾首,愤懑之余为这件事发明了一大堆触目惊心的警语,比如华夏陆沉,比如铜驼荆棘,比如百年丘墟等等,试图警醒后人,避免悲剧重演。
然而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五胡之乱折腾了135年,又南北朝并立了170年,终于重归一统了,取而代之的竟是“胡”得一塌糊涂的隋唐两朝。反正在巍巍盛唐,除非你长得眼珠五颜六色、发须花里胡哨,否则真的很难分清一个人是汉是胡。
于是又有一大堆后人继续痛心疾首,念念叨叨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什么的。而拿出来的最常见的证据,就是安史之乱——若无此劫,盛唐岂能中道崩殂,又焉能出现宋元的四百年国耻?

其实吧,在洋毛拿坚船利炮轰开“我大清”的国门之前,谈什么汉胡之别、民族之分不能说都是瞎扯淡,但也差不离。孰不见明朝开国二祖的北伐大军里边,蒙古人都快比汉人多了?孰不见晚明压制蒙古、后金的两大利器——辽东铁骑和关宁铁骑中打起仗来最玩命的恰恰是一堆蒙古人和女真人?孰不见朱由榔被汉人吴三桂抓起来后,最积极的跑去营救的居然帮正蓝旗的满洲兵……
说回到安史之乱。叛军这边,除了领头的安禄山(粟特人)、史思明(突厥人)外,高邈、许叔冀、吉温等核心幕僚、张通儒、高尚、严庄等高级文官、李归仁、崔乾祐、田承嗣等重要将领哪个不是如假包换的汉人?
反倒算是正统的唐朝这边,保皇保得最忠心耿耿的“中兴三杰”中除了郭子仪,剩下俩都是胡人(契丹人李光弼和铁勒人仆固怀恩);剩下如高仙芝、王思礼(高句丽)、哥舒翰(突厥)、安思顺(粟特)、慕容溢(吐谷浑)、荔非元礼(羌)、尉迟胜(于阗)、白孝德(龟兹)、浑释之(铁勒)等贤臣猛将,在某些人的判定标准中只能算“精神唐人”;至于朝廷的各路平叛大军,来源就更复杂了——东北的契丹、奚、室韦(即后来的蒙古),塞北的突厥、回纥、铁勒,西北的于阗、龟兹、吐谷浑,西南的僚蛮诸部均是丁壮齐聚、猛男尽出。甚至在今天的阿富汗等中亚诸国以及远天边的阿拉伯人,都高呼着“赴国难,共讨国zei”的口号慨然赴死,打起安史叛军来比正牌的大唐官兵还卖力气。

这场面,就问你抽象不?到底谁更像胡、谁更像汉?
所以就本质而言,安史之乱跟汉不汉、胡不胡的不能说一毛钱的关系没有,但也谈不上多大。其实这就是场因利益、立场以及阶层而起的内战,只不过造反的头头恰好是个胡人罢了。
甚至可以这么说,如果不是安禄山而是张禄山、王禄山之类的汉人节度使坐在那个位置上,这场叛乱可能提前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就引爆了。而且大唐朝廷想要平叛,肯定要花更大的成本、更多的时间,要是因此提前150年就噶了,也一点都不奇怪。
所以你以为李隆基为啥会让安禄山在河北当了十多年的节度使,甚至一度一肩挑三镇?因为他很清楚,安大胖就算最终也要反,但也是所有人中反得最晚、威胁最小的。

正如力主重用安禄山的李林甫所说的那样:
“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旧唐书·卷一百六·列传第五十六》)
老李虽奸,但眼光确实老辣,一语命中的“党援”二字,才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真正的精髓所在。
换句非常ZZ不正确的话来讲,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唐朝乃至前溯至秦汉,都没真正大一统过。因为只要朝廷立在关西,那么山东、尤其河北老乡就是不服,就要跟你干,还是不死不休的那种。
那一千多年里的东西之争,可比后来的南北激烈得多,更血腥得多。很多看似云山雾绕的历史谜团,唯有放在这一大背景下,才能拨开云雾见月明。
01本文所说的关西,指的是潼关、大散关以西的地区;山东则指崤山以东,河北则指黄河以北,与如今我们熟悉的地理概念并不相同。

尤其是河北。据史料记载,从周定王五年(前602年)到1938年黄河共发生1590次决口,其中大的改道就有26次。不过除了在夺淮入海的近700年时间里(南宋到清末),黄河河道与今天并无太大的不同。因此历史上所谓的河北,实际上包括了今天河北省的全部以及山东省的大部,还有山西、河南两省的部分地区,反正山河四省谁都跑不了。
而这个河北,更是从秦汉到隋唐的一千多年里,历朝历代里最特殊的存在。
有多特殊?其一是富庶甲天下。唐天宝年间,河北以不足全国五分之一的人口,给朝廷贡献了超过四成的税赋,这是个什么概念?一个河北的经济规模,就相当于今天的粤、苏、鲁、浙、川这前五经济强省的合体,简直是离谱,堪称富可敌国。哪怕经过安史之乱的摧残,河北照样富得流油——德宗朝时以富庶著称的淮南、江南、岭南这南方三道使出洪荒之力,每年也只能给朝廷供应40万石漕米。而河北一个最穷的幽州镇,被打老实后就能轻轻松松的“施舍”出50万石粮食。
简而言之,就是打南北朝起至隋唐,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心就已经从关中转移到了河北。河北人口之稠密,物产之丰富,经济之繁荣,能把关中甩出二里地。至于尚未得到全面开发的淮南、江南更是瞠目其后,只有河南能勉强比比,但也不在一个水平线上。

经济发达了,文化教育、科学技术、商贸手工等各方面的水平都差不到哪儿去。就拿科举来说,宋明时以擅长考试傲视全国的江南士子在唐朝时压根就排不上号,就算李家皇帝拼命作弊和公开打压,河北仍是众所公认的文化荟萃之地,进士和宰相的数量毫无疑义的全国第一;而在最能体现当时的“科技与工业”水平的丝织业上,河北更是独一档的存在。尤其是贝州(今河北邢台)出产的清河绢直接被《隋图经》奉为“天下第一”,在唐朝时更是作为流通范围最广、价值最高、接受度最强的货币存在——就算有人不认金银铜,也没人不要清河绢。
甚至直到北宋,河北绢帛仍以高产量、高品质备受追捧,成为贡品的首选。赵家皇帝给辽金送岁币时,一度打算拿质量差、价格便宜的南方绢糊弄事,结果被人家一眼看穿并惨遭退货,指名就要河北货,否则就削你。
因为北宋防御契丹人的需要大搞“回河”,弄得黄河数度决口,吞噬了大量的土地人口,才让河北逐渐衰落。靖康之变后河北更是直接沦入野蛮人之手长达300年,才彻底没落。大量的富户、士人以及工匠纷纷南逃,间接促进了江南地区的繁荣。

史上大多数富庶太平之地,都免不了纸醉金迷、士骄民堕,武风不振,偏偏河北是个异类。为啥?除了东临大海外,河北堪称是三面皆敌,连睡觉都得睁只眼,否则别说富贵太平了,没准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河北的北边是东北。东北那疙瘩在史上就是个胡窝子——除了匈奴、突厥和吐蕃,历朝历代最为头疼的“北患”均发源于此。作为挨得最近的邻居,河北保持警惕进行备战并不奇怪。可西边、南边呢?那可是中原内地,大多数时候与河北都是“自家人”,为啥还要如临大敌?
其实在北宋之前,无论是古早的匈奴、鲜卑,还是突厥、契丹,对河北来说都不是啥大事。就拿赵家皇帝死活摆不平的契丹来说,晚唐时河北单拿出个幽州镇,就能屡屡打得耶律阿保机的所谓“开国精兵”鼻青脸肿,牧马不敢南窥。
当然前提是没人扯后腿。而这个扯后腿的,往往还就是那个“自家人”。比如燕云十六州,若非石敬瑭主动送货上门,你以为凭契丹人那个熊样能拿到手?
所以在那个千年里,河北的敌人从来不是来自北方,大多数都是那个理论上管着他的朝廷。因此前文才会说,从唐朝前溯至秦汉只有字面意义上的大一统,皆源于此。
02太和三年(829年)、也就是著名的虎牢关之战已经过去了200多年以后,魏州(今河北大名)小吏殷侔有次下乡公干,发现沿途修有多处窦建德庙,而且香火旺盛,往来祭祀的乡民络绎不绝。殷侔心有感触,遂挥毫泼墨写下一篇流传千古的雄文《窦建德碑》。

在这个长安六破、天子九迁的年头,昭陵的香火怕是都有些年头没冒起过青烟了吧?可窦建德这个与“国朝”唯一那尊神为敌的大反派,在河北大地上依然被祭拜得毫无顾忌。
为啥?《窦建德碑》中的一段话解释得明明白白:
“自建德亡,距今已久远。山东、河北之人,或尚谈其事,且为之祀,知其名不可灭,而及人者存也。”
翻译成白话的中心思想就俩字——不服。
当然除了窦建德庙,当时的河北大地上更常见的是“二圣庙”。哪二圣?安禄山、史思明是也。这俩货无论在官方还是民间、正史还是野史都是臭名昭著的大反派,还人人喊打的那种。唯独在从中唐到五代的河北,是有口皆碑的“圣人”。何为“圣”?在两宋之前,唯有皇帝可称圣。也就是说在河北人的心里,朝廷正统就从没姓过李。

要是有人敢对河北人心目中的正统不敬,后果如何?
长庆元年(821年),幽州节度使刘总被淮西平叛吓到,遂归顺朝廷,唐穆宗李恒以宰相张弘靖代之。结果作为正宗“老西儿”的张弘靖刚到任,就发现幽州遍地都是二圣庙,被吓得不轻。于是他下令毁庙禁祀,又开安禄山之棺戮尸,结果怎么样?幽州兵乱遂起,老张从关西带来的佐吏、亲信、奴仆被杀了个精光。若非李恒赶紧妥协,让本地人朱克融接任节度使,估计老张的小命也保不住。
所以庙就庙吧祭就祭吧,没人管了,也没人敢管。
而如此叛逆的河北,也不是一个唐朝就能炼成的。
早在一千多年前,始皇帝以一国灭六国横扫天下,纯粹是以力服人。说什么大势所趋、天命如此就太扯了。所以当武力不再,自然是六国皆反,秦只好二世而亡。

当时反秦反得最起劲的,当然是“亡秦必楚”的那个楚,刘项都算是楚人嘛。河北作为燕赵故地,虽然反得也挺卖力气,但充其量的角色就是个小跟班,没啥太过亮眼的作为。
变化始自两汉。
刘邦虽然起家于楚地,却第一个打进了关中。而且一来就看好了这个地方,就想赖着不走,以至于被项羽拿个汉王打发掉后,会失态到差点直接翻脸开撕,根本不管这是不是拿鸡蛋碰石头。
为啥?因为关中这个地方实在是太好了——四塞之地,天府之国(没错,第一个天府之国可不是四川),据之便可立足不败,简直就是天生的“龙兴之地”。而且刘邦入关中约法三章的德政,深受故秦地父老拥戴,再加上有项羽火烧咸阳这个反面教材衬托,就愈发的得民心。所以在楚汉争霸中,坐镇长安的萧何才能如鱼得水,前边的主公打没了多少兵马和钱粮,他就能源源不断的补充上更多。

更重要的是,当时大一统的观念并未深入人心。战国诸侯故地之人,向来仍以秦人、赵人、楚人、齐人自居,你老刘突然整出个大汉,让我们都当汉人,凭什么?
所以不如找个屁股坐得最稳的地方,先把基础打好,别的再说。
对于那些心里不服甚至表面上都不怎么掩饰的地区,刘邦采取的办法就是“以天下馈关中,以关中制天下”。具体的手段就是搜刮山东的财富、富户输往关中,同时改秦时的郡县制为郡国制,即将刘姓宗室分封到各地,试图加强控制力度。最后还在函谷关设下关卡,山东人士想要前往关中地区,必须持有朝廷发放的通关文书才能通行,否则哪来的回哪去——从刘邦到王莽,这条规定始终坚挺,从未废除过。
最重要的军队——最精锐、装备最好、待遇最高、数量最多的汉军,始终驻扎在关中,顶多在洛阳那边有点。你可以说这是为了防御匈奴,但实际上防的是谁,难道山东人心里没数?
反正对匈奴可以妥协一下,送点财帛公主啥的。但对山东就没啥好说的了,不服就是干。

典型如汉景帝刘启,直接削藩,削出来个七王之乱。话说刘邦分封了一大堆儿子去东边,本来是指望他们保皇的。可数代之后,这些藩王与长安城里那个皇帝的血缘关系越来越淡,反倒与当地的牵扯越来越深。本来就越看西边越不顺眼了,你还来撩闲,那不反你留着过年?
叛乱七王中,吴(治今江苏沛县)、楚(治今江苏徐州)、济南(治今山东章丘)、淄川(治今山东寿光)、胶东(治今山东平度)、胶西(治今山东高密)都位于河南,即黄河与长江夹着的那片地儿,只有赵国(治今河北邯郸)位于河北。
显然,中原“逆子”河北还在猥琐发育。而先蹦出来的河南则成了出头的椽子,被刘启、刘彻、刘弗陵和刘询等数代汉帝轮番整治,地方势力纷纷瓦解,再也没了桀骜不驯的资本,在此后的近千年里逐渐沦为关西政权的附庸。
河南倒下了,河北的机会就来了,而刘秀的闪亮登场则成了催化剂。

其实刘秀也没办法。除了个汉室宗亲的招牌,他参加这场逐鹿天下的饕餮盛宴的时间比别人晚,本钱都是大哥刘縯赚来的,说白了就是个二世祖,在河南、关中那片根本没有出头的机会。幸亏刘秀运气好,刘玄送来神助攻,一脚把他踹去了河北。
刘玄打发他去河北,本意是发配,结果弄巧成拙,为啥?
话说河南自夏商起就是天下之中,但从周朝关中崛起,自战国至秦汉的近千年间更是成为毫无疑问的ZZ兼经济中心。又因为当时的生产力不行,交通不便,还没科举,所以想当大官、发大财,当然是关中人优先,近水楼台的河南人也能捞到不少汤喝。
而河北作为华夏文明发源地之一,人口经济什么的也不差。但就是离权力中心太远,不受待见也不被信任,只能“上小孩那桌”。故此,在当时才出现了“河南多世家,河北多豪强”这种泾渭分明的利益分配格局。
世家在ZZ上有保障,故能传承个几百年不衰毫不稀罕。那豪强是什么?就是有钱有地有人,甚至可能比世家还富有。但在ZZ上毫无地位和前途,就是做不了大官,尤其是朝廷中枢的大官。

没有ZZ权力庇佑的财富,就是沙筑的城堡,稍来点风雨就可能飞灰湮灭。所以有千年的世家,但豪强能顺利传个两三代都很难。因为只要朝廷一缺钱了,你就是第一个待宰的肥猪。
所以河北土豪们非常缺乏安全感,但在太平年月里却毫无办法,稍微蹦跶一下就得被朝廷大军摁死。可现在朝廷自己乱了,自顾不暇了,土豪们立马就支棱起来了。
因此刘秀本是心如死灰的来到河北。结果一看这地界不但有兵有地有钱,而且一点也不比河南、关中少,简直堪比发现新大陆,那还等什么?赶紧扯开膀子开干吧!
河北土豪有实力但没大义,刘秀有的是大义但就是没实力,于是双方一拍即合就开始“合资建厂”——刘秀抛弃真爱阴丽华以近乎入赘的方式加入河北集团,组建铜马军,然后就开始横扫一切刘氏宗亲,成功“复汉”。
03汉是复了,却从西汉变成了东汉,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国都从长安搬到了洛阳。

为啥?其实这跟刘秀的老家在南阳关系不大。毕竟他祖宗还是楚人呢,还不照样据关中而临天下?说到底,还在于刘秀的发家班底除了他哥留下的几个河南老乡外,几乎统统都是河北人。所以没逼着他定都邺城已经是最大的妥协了,还能容忍刘秀重返长安、还离自己老家那么远?
所以从东汉开始,所谓的士族门阀就开始东移、北上,直到隋唐最顶级的“七宗五姓”里边,除了个陇西李氏和荥阳郑氏外,统统位于河北——其始作俑者,就是刘秀。
当然刘秀也不是那么容易欺负的,其与河北势力的明争暗斗始终未绝,高潮就是度田事件。当然最终在兵强马壮的河北勋贵面前,他也仅是赢了面子却输光了里子。强势如光武大帝尚且如此,谁还能指望他的子孙能有多大的出息?
所以最终东汉可以说就是亡在了一帮河北军阀手里——刘大耳朵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曹老板倒是河南人,但却是靠河北兵起家。甚至割据东南的孙氏,其麾下也不乏像程普、韩当、徐盛、潘璋之流的河北干将。

而一旦品尝过权力的美味,河北人就再也回不到过去那个“淳朴”的土豪时代了。相应的,被分薄了或者夺取了权力的关西人,会甘心?于是这场泾渭分明的东西之争,就愈发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甚至于这股风潮还“传染”给了胡人——五胡和南北朝,整个北方除了北魏勉强统一的那一百多年,始终是在东西对抗。先是来自东北鲜卑人以河北为根基独斗发源于大西北的匈奴、氐羌等族,后又有关中势力的代表宇文泰大战渤海人(今河北景县)高欢。反正北方人都在忙着大内斗,偶尔抽出手来收拾下南朝的北伐兵。至于统一天下啥的,谁有那闲工夫?
直到杨坚把这个活儿给干了以后,反隋反得最坚决的也从来不是以前最喜欢北伐的南方,而仍是老冤家河北,比如差点把新兴的大隋给掀翻了的尉迟迥之乱。杨广继位后,成天跟他叽叽歪歪依然是河北人,具体说就是那些山东士族。所以杨广为啥急不可耐的修运河、建东都,而且还做出了动员了近500万人东征高勾骊这种匪夷所思,哪怕傻瓜都能看出不靠谱的事情来?其实工程和战争都不是目的,这位隋炀帝要干的就是尽可能快的消耗掉山东士族的人口和财富,消除掉帝国最大的隐患。

只可惜他失败了。而且反杨反隋反得最早、最起劲的,还是河北人。
但让河北人失望的是,杨广被干掉后,取而代之的李唐还他母亲的是关陇集团捧出来,这可咋整?继续弄他呗!
于是河北人也推出了自己的“圣人”,那就是窦建德。
窦建德这个人,哪怕是拿今天的标准来看,比之李渊、李世民父子也更像个圣人。
他自律俭朴,不贪财好色,甚至不吃肉。哪怕割据称王之后,依旧如前一般的粗茶淡饭,穿麻布衣服,讲义气。打仗缴获了绢帛从来分文不取,一律散给将士和百姓;攻占杨广行宫俘获的妃嫔宫人秋毫无犯,全部放归与家人团聚;他甚至不杀俘,甭管是隋兵还是唐军,一律“给其衣粮,送其出境”。甚至像李神通、同安公主、李勣、魏徵之类的“大鱼”,都待之以礼,大部分都无条件释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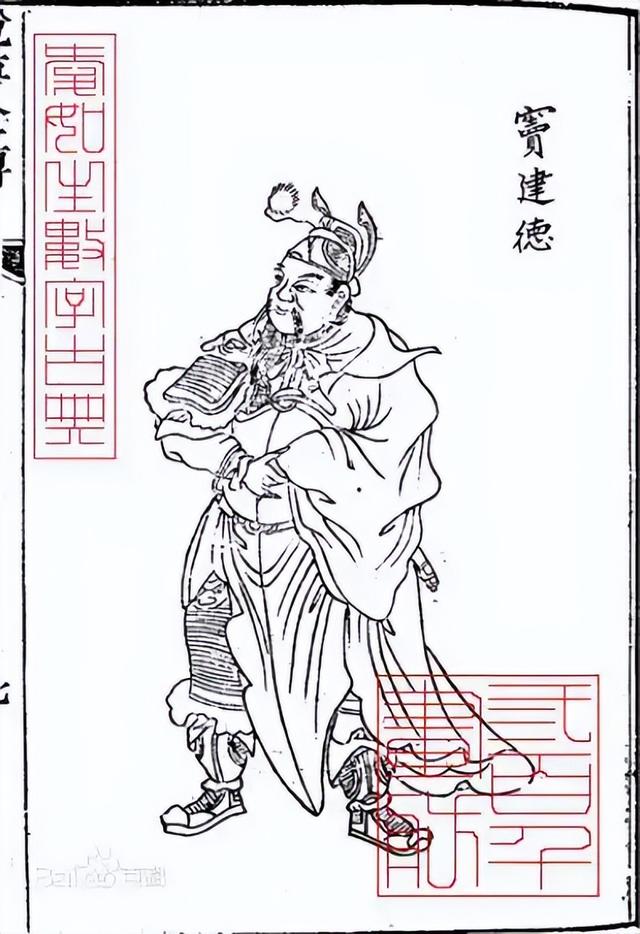
至于说约束军纪,与百姓和睦相处,更是常规操作,能把军纪一向乱糟糟的唐军甩出几里地。
如果当时的百姓有话语权,我想绝大多数理性的人会选择姓窦的而非姓李的当自己的皇帝。所以窦建德被抓住以后,李渊二话不说就把他给砍了——真是不敢留啊!
但杀掉一个窦建德,还有刘黑闼,有徐圆朗,有高开道,反正河北人就是不服,就是干——打个比方,如果说大唐平定河南、陇右的战争烈度是甲级联赛的水平的话,夺取南方就算乙级联赛,拿下河北则属于超级联赛。
所以在彻底扫平天下后,河北就理所当然的成了朝廷的眼中钉,受到了各种“优待”。
首先就是收军权。初唐实行府兵制,说白了仍是种寓兵于民、军民合一的军制。只不过相较于秦汉不再普遍征兵,而是将军户与民户分开,前者只服兵役,后者则要承担所有的税赋与徭役。
府兵制最盛时全国共设633个折冲府,其中关内道就有289府。如果加上李家发家的河东道以及同属西北的陇右道更是达到了488府——这意味着全国将近80%的兵力,都被集中在了关中。这些关西老爷兵们家有几百亩地的一点不稀奇,由部曲或奴隶耕种,自己吃得膘肥体壮后整天锤炼武艺战技。只要皇帝一声招呼,就集结起来出去砍人,包括且不限于突厥人、铁勒人、吐谷浑人、高勾骊人什么的。当然,要是河北人不乖,同样是照砍不误。

而在当时占据全国人口五分之一、经济体量四分之一的河北,仅仅是为了就近御边设置了区区25府,撑死也就两万来人。这就等于被剥夺了武装,朝廷可以予取予求,地方根本无力反抗。
解除了武装,下一步就可以挖掘根基了。都说唐朝皇帝喜欢斗士族,其实斗得最狠的初唐那阵子。从李世民到李治、武则天再到李隆基,天天揪着山东士族的屁股穷追猛打。像在前朝,什么博陵崔、清河崔、赵郡李、范阳卢、太原王能占据朝廷高位的半壁江山,南北朝那会儿更是能跟皇帝坐而论道,一不高兴了就张罗着换一个那种事情,在此时想都甭想。根本原因,就在于河北世家失去了武力这面最坚实的后盾。
04但从开国到开元的一百多年里,河北只是蛰伏,但从未心服。

府兵制最大的问题,就是对朝廷的治理能力和控制能力要求太高。简单说,就是朝廷手里得有地可分,即维持均田制不动摇,这是府兵大爷们能战、敢战还可以战而胜之的根本。
隋初时因为人口增长过快加上朝廷疏于管理,导致府兵人均只能分到十几亩地,根本养不起部曲和奴婢,只能自己种地糊口,哪还有功夫习武操练?这就差点把杨坚吓死,为此他大力推动移民,把大量民户撵出关中,好让府兵有地可分,这才维持住了军队的战斗力。
唐初能维持府兵制的根本,就在于在籍人口只有180万户、720万人。哪怕都统一中原、灭掉突厥,连西域都插进去半只脚的贞观末年,全国也只有210万户、约1235万人——作为一个国土面积超过1200万平方公里的王朝,而且核心领土维持了近30年的和平,这样的人口规模显然是无法想象的,必然是建立在对更加庞大的非入籍人口、即奴隶和部曲的压榨和剥削之下的。
但这显然是无法长期维系的。当武后末年人口突破3000万大关时,府兵制就开始衰败;至开元年间户籍人口达到5000万以上时,连均田制都崩了,这时候李隆基别说打仗了,连找点人护驾都费劲了。
无奈之下,只能募兵。但募兵不像府兵,分点地免个税就打发了,你得给人家发真金白银的军饷。一个兵一年下来二三十贯钱都够呛能养得住,再加上关寨营房、兵械甲马、操练调动、吃喝拉撒,最低限度的50万军队最少得花两三千万贯,你让李隆基上哪儿弄这么多钱去?

没办法,只能把这个沉重的负担扔给地方,遂有了天宝年间的十大节度使。
于是大唐的军队分布就从强干弱枝变成了强枝弱干,地方造反的风险大增,这可咋整?也好整,李隆基想到的办法是从人事上解决问题。
天宝十节度的辖区,基本就是把大唐的边境围了一圈。其中的重点防御方向有两个,其一是西北的安西北庭以及陇右河西四节度,主防吐蕃;其二是东北的范阳平卢和河东三节度,主防的……是啥?
河北三镇中,唯平卢镇位于燕山以北(治今辽宁朝阳),有兵37500人,其中骑兵5500,领契丹、奚两部,辖渤海、黑水等四府,兼统室韦——有这三万来人在,方圆数千里的诸部蛮胡连个屁都不敢放。

就这样的平卢镇,也只能算是偏师。真正的主力,是位于燕山之南、深入河北的更精锐的范阳镇,有兵91400人;至于居高临下以视河北的河东镇,驻军也有55000人。人家真正防备的是谁,你河北人心里真没点B数?
很显然,在李隆基乃至整个关西集团看来,敌在内而非外。那个贡献了大唐近半GDP却脑后始终倔强的生着反骨的河北,才是这个王朝真正的心腹大患。什么吐蕃、回纥、阿拉伯都得上小孩那桌。
所以李隆基治河北的策略,就是ZZ上疏远,军事上震慑,经济上压榨。让河北人即便全身反骨,也没有造反的本钱。
唯一的隐患,反倒是河北驻军。
府兵时代,聚天下之兵于关中。哪个地方反了或地方不靖,就把军队派过去,从来不用担心这些忠心耿耿的关中兵会有什么异心。可募兵就不行了,那是要长期驻扎的,还得靠地方财政养活,所以只能招当地的兵。

李隆基得有多幼稚,才会相信身为当地人的河北兵会忠于那个遥远的关西朝廷?
他能想到的办法,就是给河北三镇安排上最忠心的节度使。比如裴宽、田仁琬、王忠嗣、韩休琳什么的,个个都是如假包换的老关西人,宗族、产业、ZZ前途也都在关西,理论上来说起异心以及被拉拢反水的可能性非常低。
但这么做真的没隐患?比如那个裴宽,出身著名的河东裴氏。而老裴家有个更著名的祖传手艺,那就是“装鸡蛋”——隋末唐初那会儿,裴蕴死忠于杨广,裴寂跟李渊好得蜜里调油,裴矩则在隋唐间反复横跳……反正不管谁输谁赢,老裴家顶多损失个把棋子,总是最后的赢家。
谁敢保证现在的裴家,不再玩一把类似的把戏?
再比如那个人镜魏徵,号称“千古忠直之臣”,不照样仕四朝七主?谁给我当老板,我都是忠的。当然等老板破产时,我忠不忠,就是另一码事了。
05难道李隆基就找不到个靠谱的忠臣了?还真有,比如安禄山。

李隆基信任安大胖,让他坐镇河北十多年,一度一肩挑三镇,最大的理由,恰恰因为这厮是个胡人。
至于汉人嘛,自汉末以来想找个死忠之士——单纯指忠诚于某位皇帝的,简直比三条腿的蛤蟆还费劲。就拿李世民的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来说,一生只仕一主只有长孙无忌、李孝恭(还存疑)、侯君集这区区三人而已。一言不合就换个主子的简直如过江之鲫,吕布那样的三姓家奴穿越过来,都是难得一见的大纯臣,你还指望个啥?
没办法,风气如此。士族门阀制度之下,人人心中都是先顾家,再说国,皇帝还得继续往后排。诸葛亮忠得让人没话说吧?但谁注意到他大哥诸葛瑾在东吴官至大将军、豫州牧?他堂弟诸葛诞在魏国官至太师、征东大将军?琅琊诸葛氏分装鸡蛋的本事,就比河东老裴家的差了?
本质上都是一路货色!

但胡人就不一样。“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观念深入汉人骨髓,可胡人却尚贵种、重血统,颇似今日隔壁三哥家的种姓那种玩意——匈奴单于只能出于挛鞮氏,鲜卑皇帝只出于慕容、拓跋、宇文三氏,柔然可汗都姓郁久闾,突厥可汗都姓阿史那,契丹皇帝都姓耶律,女真皇帝都姓完颜,蒙古大汗都姓孛儿只斤,满洲皇帝都姓爱新觉罗……
就算胡人堆里变异出了陈胜吴广、黄巢李自成,甭管他们再怎么振臂高呼,再怎么许下多么诱人的条件,最终也只能收获一堆白眼——都是狗一样的贱种,还想当人上人?
所以胡人只要降了,当然也不排除野心勃勃之辈,但大多数都是非常认命也非常听话的,起码比当时的汉人强多了。举个例子,李世民去世后,大家伙嚎几嗓子、挤几滴眼泪也就完了,结果突厥人阿史那社尔和铁勒人契苾何力不远千里跑回长安,就为了给他们的“天可汗”殉葬,还是谁都拦不住的那种。最后逼得新帝李治不得不颁下旨意,禁止二人寻死,否则就算不忠。
后来李治临死前,特意下旨令还活着的契苾何力不许殉葬。怎么都死不成的后者不死心,干脆拉来一支亲族,令其世守乾陵(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陵寝)——别当老契苾是说着玩的。南宋时蒙古南侵,契苾氏族人为保乾陵不损与精锐的蒙古大军周旋了一年有余,死伤无数,最后逼得蒙古人发誓不取乾陵杯土,只求过境才算拉倒。

这种事,别说在当时了,历朝历代有几个汉臣能做到?更别提安史之乱爆发后,平叛平得最起劲、保唐保得最玩命的还是胡人,比如铁勒人仆固怀恩,一家四十六口死于王事,连嫁三女代主和亲,堪称满门忠烈;粟特人安思顺跟安禄山可是实在亲戚,而且关系莫逆。可面对大胖的招揽,安思顺不但坚拒,还主动避嫌交出兵权,匹马归朝;龟兹人白孝德本为王室后裔,为平叛主动投军,厮杀半生,至死未得还乡——这种事,又有几个汉臣能做到?
所以唐朝重用胡人的传统,是有根据的,事实证明也是成功的。那安大胖怎么说?还是那句话,被李隆基安排在那个位置上的如果是张大胖、王大胖什么的,没准早反了。在安禄山之前,历任来自关西的河北节度使,要么强硬得跟当地人水火难容,要么软弱得被撵走,要么干着干着立场就眼瞅着要走偏……唯有大胖,坐镇河北近二十年,既没闹出大乱子,屁股也没坐歪,朝廷该收的钱粮分文不少,这是什么?这就是能力,就是忠心啊!
没错,起码在起兵之前,谁也没法说安禄山是不忠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正史、野史所载的这厮各种糟滥破事,大多是先立个奸恶人设,再从结果倒推出来的,或者干脆就是胡编乱造。可以这么说,要是李林甫能再多活几年,大胖十之七八会以忠臣干将的名头流芳青史。
而他之所以造反,纯粹是被杨国忠逼的、李隆基惯的,就这么简单。
06安史之乱是场内战,又不是普通的内战。

别的朝代打内战,也不乏一仗下来歼敌几万、十几万甚至几十万的大场面。但这种仗打个一两次,基本就大局已定——胜方固然士气高昂,势如破竹,败方多半也就半推半送,认栽拉倒。
都不用往上数五百年,没准都是一家人,所以何必打得那么认真、玩命?
但安史之乱不一样。潼关之战唐军19万大军尽墨,香积寺之战双方伤亡近15万,睢阳之战据说张巡歼灭叛军12万,洛阳之战唐军又打没了数万。邺城之战伤亡数字史书不载,但唐军几十万人被打崩,伤亡个几万人不离谱吧?昭觉寺之战又是场二三十万人的混战,史朝义的10万兵就跑掉了几百——天宝年间大唐全国不到50万兵,安史之乱打了八年光是几次重大战役差不多就能把这个数字给打没了。但转过头去唐军或叛军又能拉出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马,再拼个你死我活。
安史之乱打没了多少兵,这个数字现在谁也说不清。但能说清的是八年间大唐的户籍人口从5300万直降到不足1700万,虽然不可能都是在战争中损失的,但也足以证明其惨烈程度。
这得是多大的仇、多大的恨?

别人打仗,哪边战损超过10%基本就崩了,就可以追亡逐北了。要是能战损20%以上还不溃不跑的,都是能在青史留名的强军精兵。可在香积寺那场,唐军和叛军打没了一支部队,就再添上去一支,再打没就再添,反正就是不退、不服,也不搞什么奇谋妙计,就是正面刚,比谁先眨眼。双方就这么当面锣正面鼓的往死里怼,足足怼了8个小时,然后叛军败了。为啥败了?因为叛军兵少,就10万人,而唐军有15万,没预备队往上顶了,这才垮掉。
在这8个小时里,唐军战死了7万人,叛军才6万。要是安守忠能多带几万人过来,这一仗能打成啥样还真不好说,没准就同归于尽了,双方一个人都活不下来。
就是这么大的仇,就是这么大的恨!
而这场内战的结果,看似唐军赢了,其实也就赢了面子。战后田承嗣公然在河北大建特建安史“二圣庙”,朝廷还不是只能当没看着?河北藩镇不高兴了,就不给朝廷纳税,后者又能怎么办?或者干脆河北照旧今日闹明日反,哪怕大多都能平定,但谁敢就把河北藩镇给撤掉?
所以史书只能含糊其辞。因为有些事就没法说明白,一旦说明白了这个嬴来的面子就会被冷酷的现实掰扯得稀碎——平叛之役本是为了削藩,可安史之前天下只有十节度,之后却是节度使遍天下,才最终形成了搞死大唐王朝的藩镇割据。为啥?初衷还不是为了防备河北人再搞一次安史之乱?

所以有没有安禄山、有没有胡人,河北都照样是那副谁都不服的鸟样。不掐住按死,没有安史之乱,也得冒出个张王、李刘之乱啥的,反正结果都一样。
可以说,大唐就是被河北给活活耗死的。
前车之辙,后车之鉴。所以五代的那帮强人们,甭管是朱温、李存勖,还是石敬瑭、柴荣,只要腾出手来,要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屠河北。反正就是杀,不分良莠,更不管善恶,宁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宗旨就是把刺头全干掉,只剩下老实人。
像最桀骜不驯的魏博镇,就先后被屠了三次半,活生生把敢跟大唐天子比肩的魏博牙兵宰了个干干净净。可结果怎么样?都到一百多年后的北宋仁宗朝了,人家照样给你搞出个贝州兵乱。
所以你以为赵家皇帝成天在河北把黄河弄决口,或者成天毁田成林、弄得到处都是池塘、沼泽真是在防契丹人?还有大把的后人觉得这帮当皇帝、重臣的真蠢,孰知人家说的那套,就真是做的那套?
其实真正把河北毁掉的,还是胡人。从靖康起直到朱元璋北伐,河北沦陷三百年,这才彻底完蛋,从隋唐时的富甲天下,变成了需要朝廷“转移支付”的贫困落后地区。
腰包瘪了,腰杆就硬不起来,自然也就闹不起来了。这个影响,哪怕到了今天也不能说彻底消除掉。

有点想当然了
就好比曾国藩的湘军既便也有塔齐布和多隆阿这样的满族将领,咸丰帝仍然认为其为汉族势力防范戒备!反观江南大营的和春,向荣部下就算有张国梁这样的汉族将领,咸丰帝也将其视为满族势力倚靠信任!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