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钟兆云 王盛泽
为预防和消灭传染病尽心尽力
新中国虽然建立了,但旧社会留下的是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全 国各地传染病流行甚广,严重损害了人民的身体健康,人民群众还挣扎 在死亡线上。要建设一个新社会,任务相当繁重。卫生工作关系到民众 的切身利益,中央对此极为重视。早在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就 确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方针,后来又加上“卫生 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
当时中国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每年产妇和 婴儿的死亡人数在600万到950万;肺结核患者估计在1000万以上;天花 患者475万;伤寒、斑疹伤寒、黑热病、血吸虫病等患者达200万至1000 万;疟疾患者约450万;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时有流行。总计各种传 染病患者达三四千万之多,其中可避免的死亡人口在500万至700万。全 国的死亡率居高不下,高的地方达到千分之三十。
这样巨大的患病人数和极高的死亡率,在旧社会是束手无策的,华 佗再生也只有徒唤奈何。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决不会让这种状 况继续下去了。在当时的情况下,单靠治疗要达到消灭或根治的目的, 这既没有条件也不可能,只有采取积极预防的措施,才能解决问题。
对此,傅连暲与卫生部领导人李德全、贺诚、苏井观等人一起,积极 贯彻中央确定的方针,努力采取各种措施,预防疾病。
建国初年,我国许多地区发生自然灾害,每年受灾人口达数千万。 从北方到南方,各种流行病、传染病蔓延很广。中央卫生部坚决贯彻预 防为主方针,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扑灭瘟疫的运动。为此,卫生部 除指导各地迅速建立健全海关、疫区的检疫所、站外,还派出防疫队、医 疗队,奔赴灾区、疫区,帮助人民群众防病治病。仅1950年,中央、各大 区、各省市组织的防疫队就达到125支,队员有5400余人。
南方是各种疫病多发的地区,福建又是鼠疫流行的重灾区,鼠疫一 来,受害时间长,肆虐范围广,死尸枕藉,万户萧疏,人人都“谈鼠色变”。
中央确定张鼎丞担任第一任福建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职务 后,有一次开会时,他刚好碰到同是福建老乡的傅连暲。他们两个也是 老交情了,早在闽西时期,傅连暲对张鼎丞发动永定暴动,创建闽西革 命根据地,后来又担任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事迹就很熟知,并对他 充满了敬佩之情。在延安时期,张鼎丞曾任中央党校二部主任,领导了 二部的整风,受到毛泽东的赞扬。傅连暲也曾经给张鼎丞检查过身体, 并有机会经常在一起详谈。
张鼎丞深知福建人民受流行病残害的惨状,并想到了福建的鼠疫 和其他疾病,他满怀希望地说:“傅医生,福建人民深受其苦,你这位大 部长,要想办法帮助一下,使福建早日消灭疫患。”
当时傅连暲是军委卫生部副部长,他不仅知道福建群众受鼠害之 苦,也知道人民解放军进军南方水网地区后,也受到疟疾、血吸虫病等 的严重影响,这是必须解决的迫切问题。
“我们一定会采取措施的,只不过现在力量有限,主要还是靠地方 和军队自身,我们只能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对福建这个重灾区,我们可以派人去。”傅连暲说。
1950年2月,中央卫生部鉴于鼠疫又在福建流行的严重情况,特将富有鼠疫防治经验的内蒙古防疫队队长、专家萨木勒和他的助手超古浪派到福建,指导防治鼠疫的工作。
他们克服了种种难以想像的困难,深入疫区,现场指导福建各地的 防疫灭鼠工作。张鼎丞对他们非常关心,交代人接待,努力配合他们的 工作,搞好生活。
经过数月的工作,福建鼠疫基本得到控制,取得成效。但是,萨木勒和超古浪却在回北京途中,在福建的建瓯遭到土匪的劫掠,因不愿为土 匪利用,惨遭杀害。傅连暲和张鼎丞对此都深表痛心。张鼎丞指示要做 好收殓安葬工作,并在福建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央卫生部特派代 表参加。张鼎丞亲临大会致祭,他在所送的挽联中写道:
“翰海闽疆共仰 英名垂不朽,疫情匪患定除灾难竟全功。”
表达了对两位烈士的崇高评价和消灭疫情匪患的决心。
中央卫生部成为防疫的总指挥中心,只要哪里出现疫情,哪里的情 况就及时地反映到这里,卫生部立即派出人员奔赴各地。广东省雷州半 岛的濂江、遂溪等地发生鼠疫,傅连暲和李德全、贺诚等卫生部领导研 究决定,立即组织赶制鼠疫生菌苗一百万人份前往供用,接着,又派东 北防疫人员154名,携带药械及宣传品,赶赴疫区协助防治。浙江温州也 发生鼠疫,卫生部又忙活起来,赶紧调派上海检疫所一部分人员前往协 助,并寄去大批鼠疫生菌苗。
此外,对一些地方发生的急性流行病,如脑膜炎、白喉、斑疹伤寒 等,卫生部也分别派遣医务人员和调拨药品协助当地防治。为了充实防 疫力量,卫生部在大连卫生研究所和北京天坛防疫处定制了大量血清 与疫苗。并计划在半年内筹建黑热病防治所,分驻黄河两岸流行地带,开展预防工作。中央卫生部还多次组织卫生大队,包括医师、护士、化验 员、药剂员和助产士等人员,赴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卫生防疫工 作,有力地促进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卫生健康。
特别是美国在朝鲜战场上进行细菌战之后,中华大地更是掀起了 一场轰轰烈烈的、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自东北到海南 岛、沿海到新疆边境,从城市到乡村,全体人民齐动员,人人上阵,开展 了爱国卫生运动,大搞室内外卫生,清理垃圾,疏浚阴沟,大力进行捕 鼠、灭蝇、灭蟑螂等,消灭病媒传播体。昔日杂草丛生、臭水横溢、蚊蝇麋 集的农村也旧貌换新颜。
在这一运动中,中央卫生部门不仅是指挥机关,而且进行了技术方 法的指导,还开展了督促检查。先后组织了两次全国各地的大检查,并 组织各区的爱国卫生运动参观团,互相参观,互相学习,将发现的模范 典型和爱国卫生运动的经验及时地推广到全国。
1952年1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决定,把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 国人民卫生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各级防疫委员会一律改称为爱 国卫生运动委员会。从此,爱国卫生运动逐渐转为卫生部门的经常性工 作,成为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的一个主要内容。
新中国的卫生事业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甚至得到世界人 民的瞩目和认可。在奥地利维也纳召开的世界医学大会上,由16位医学 专家、学者组成的中国医学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他们在会上介绍了新 中国在短短三年内所取得的伟大成就:“在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工作 上,全国已组织了17835处接生站,训练改造旧接生婆约12.7万人;全部 县、区都建立了卫生基层组织,初步形成了农村卫生工作网;全国培养 了大批高级的、中级的、初级的医药卫生人员,医药院校、专修科、医学 技术训练班等有了很大发展;在工矿卫生方面,在少数民族地区卫生方 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代表团的报告赢得一阵阵响亮的掌声。
1958年11月,傅连暲领导的中华医学会,鉴于全国防疫工作的状况,在上海专门召开了全国寄生虫病学术会议。会议总结和交流了我国 寄生虫病防治的学术成就和有效方法,确定了此后的研究和攻关方向。 专家们踊跃发言,出谋划策,提出很多很好的建议。这次会议为在我国 加速消灭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等五大寄生虫病起 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有一次,钟惠澜的办公室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沉静。 “喂,我找钟惠澜院长听电话。”
话筒中传来略显焦急的声音。 “我就是钟惠澜!”
“喂,我是傅连暲。”傅连暲对着话筒大声说。
钟惠澜与傅连暲有过不少接触,但在他的印象中,傅连暲在什么时 候声音总是很沉稳的,今天肯定有什么事情,他急问:“噢,是傅部长,有急事 ? ”
“是这样,云南思茅地区发现恶性流行病,已有人死亡,当地医务人 员说法不一,难以确定,病情正在蔓延,情况比较危急,想请你这位专家出马,帮助治一治。”
云南边陲,历来被称为瘴疠之区,特别是有的少数民族地区,地处 亚热带,有大面积的森林、荒地和沼泽地,是蚊蝇的孳生地,也是疫病猖 獗之地,死亡率很高,流传着“只见娘怀胎,不见儿赶街”的说法。
“好的,我马上准备。”
“有你去我就放心了,祝你马到成功。”傅连暲寄予希望。
钟惠澜是我国著名的黑热病专家,对这些病症很有研究,傅连暲算 是找对了人。钟惠澜带上助手,赶到云南思茅后,当地群众奔走相告: “北京的大专家来了,我们的病有救了。”
钟惠澜会同当地医务人员,冒着受感染的危险,深入当地检验,确 诊属于恶性疟疾流行,采取了相应的治疗措施,控制了病情的蔓延,给 老百姓带来了安宁的生活。
毛泽东主席在《送瘟神》诗中写道: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 ……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 烛照天烧。”
这是对中国医务工作者的最好的勉励。
中西合璧,相得益彰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卫生事业也是如此。要接管城市的大医院,要 将它改造成人民的医院,医务人员紧缺成为一个大问题。
著名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出生于厦门鼓浪屿一个基督教家庭,曾就 学于北京协和医学院,并赴英国伦敦医学院和曼彻斯特医学院进修深 造,到奥地利维也纳进行医学考察和美国芝加哥医学院进修。在北京协 和医院,与钟惠澜、吴阶平、曾宪九、胡懋华等一起工作,成为知名专家。
计划生育工作开展后,由于涉及到人工流产措施,深受基督教影响的林 巧稚极不理解。 一天, 一辆小车接林巧稚和她的学生到她治疗过的病人家去做客,这种事在当时是比较平常的,但下了车后,她发现原来这是 北京市市长彭真的家,卫生部副部长傅连暲也在座。
林巧稚听过彭真作报告,傅连暲在开会时也见过,她一下子正不知 说什么好,只见彭真笑嘻嘻地伸出了手:“林大夫,欢迎你来做客。”然后 又指了指傅连暲,“你看还请了一位专家作陪呢。”
“听说林大夫是厦门人,我们还是福建老乡呢。”傅连暲笑着说。虽 然傅连暲当时是她们的“顶头上司”,但除了开会见个面,平时接触交谈 也极少。
“我的家在厦门鼓浪屿。”林巧稚回答。
“真是老乡见老乡,大家喜洋洋。”彭真一说,引来一阵笑声。
林巧稚一看他们和蔼的笑脸,心中的拘束感马上就消失了。
饭桌上,大家轻松愉快地边吃边谈。
“听说,你最近心里不太愉快,有些想不通的问题,能不能说出来听 听呀?”彭真看着林巧稚,关心地问。
林巧稚没有想到彭真会一下子问到这个问题,脸刷地红起来,同时 感到有点惊奇:“您怎么知道的,是谁向您汇报的?”
彭真笑了笑:“你别管是谁说的,只要回答有没有这么回事呀?”
林巧稚点了点头,道:“对,我是有些想不通的地方,他们让我站出 来划清界限,开头我是怎么也想不通!”
原来,由于这些医学专家或多或少地带有过去的思想影响,对新中 国还存在一些疑问。再加上在做他们的争取工作时,我们有些同志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从而引起一些专家的不满。
“林大夫真是心直口快,怎么想就怎么说,这是很可贵的品质。至于 有想不通的问题,可以慢慢去想。”彭真和蔼地说。
“ 一些事逼着我不得不想,但我不像她们这些年轻人,”林巧稚指指 一旁的学生叶惠芳,“她们接受得快,我暂时还做不到这一点。”
“是啊,要一下子适应这么大的转变,是非常不容易的,要有一个过 程。我那时参加革命,也有许多事情感到新奇,只是后来在毛主席等领 导同志的帮助下才慢慢明白了。”傅连暲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开导林巧 稚 。
“傅医生从一个基督教徒走上革命道路,从此坚定不移地跟党走, 这个转变也是够大的了,你们可以多交谈交谈。”彭真说。
“什么,傅医生是基督徒?”林巧稚吃惊地看着傅连暲。
“是的。我原来是汀州福音医院院长,是毛主席把我带上了革命道 路。”傅连暲肯定地点点头。
“我也是出生于基督教之家呀。看来这两者是可以相容的啰。”林巧 稚脸上渐呈兴奋之色,“最近听了多次的报告,慢慢地感到思想有点转 弯了。”
“想通了一点,就有一分进步嘛!"彭真接着说,“都想通了,问题也 就彻底解决了。”
林巧稚郑重地点了点头。
这次会谈后,傅连暲又跟林巧稚聊过多次,做她的工作,使她的思 想有了转变。不久,林巧稚走上了协和医院的讲台,她解剖了自己,解剖 了协和,讲了青年时期纯真的理想,讲了在旧社会里见到的妇女悲惨的 命运。
“我现在是看清楚了,新出来的太阳比什么都好。我爱这明朗的天 空和在这明朗天空下边的生活。”林巧稚充满感情的话语和真情,感动 着台下的每一个人。
“谢谢你,林大夫,感谢你为我们作了一场非常生动的报告。”正在 台下听讲的著名剧作家曹禺,激动地奔上讲台,拉着林巧稚的手说。后 来曹禺以林巧稚的报告内容作为素材,写了一个有名的剧本叫《明朗的 天》,影响很大。
经过各方面做工作,中华医学会团结了一大批医学卫生专家。傅连 暲关心专家教授们的工作与生活,这些专家教授也都视傅连暲为挚友, 推心置腹地与傅连暲谈心, 一些不愿与本单位领导谈的话也都能向他 诉说。逢年过节或傅连暲的生日,他们也总要到傅家去看望他。
每逢节假日,或有些专家患病了,傅连暲也经常亲自登门探望,有 时委托学会副秘书长傅一诚代表前往慰问。据傅一诚介绍:傅连暲与医 学界许多专家教授,如钟惠澜、林巧稚、张庆松、张孝骞、诸福棠、黄家 驷、吴阶平、宋儒耀等等都有广泛的交往,并建立了深深的友谊,这充分 体现了党的知识分子政策。
傅连暲对于与老中医的交往也是非常重视。“团结老中医”,是在中 国革命的历程中总结出来的卫生工作的一条基本方针,在根据地,这是 十分行之有效的经验。傅连暲利用自己既是卫生部门领导又是医生的 特殊身份,广交中西医朋友,广泛进行中西医团结和中西医结合工作, 吸收中医专家参加中华医学会,积极开展中西医交流。
早在1950年初,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为了团结中医,提高中医的科 学技术水平,特邀在北京的一些中医人士召开座谈会。到会的有中医师 赵树屏、于道济、潘兆鹏等28人,以及对中医学术素有研究的医师孟昭 威、李涛、力嘉禾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彭泽民亦应邀出席指导。
但一些中医人士因为对中国共产党还不了解,对我们的政策知之 甚少,并且抱着些许怀疑,因此没有接受我们的邀请,不参加这次座谈 会。其中有一位是知名的老中医,过去经常给国民党高层人士看病,与 一些国民党的要人有密切的往来。
对于这位老中医没有参加座谈会的事,也有不同的反映。有的同志认为,这个人看来挺反动,受旧社会的影响很深,架子很大,我们也不要 买他的账,俗话说得好,“缺一味甘草照样下得了方子”。
傅连暲在参加革命之前,作为一个自由职业的医生,对知识分子的 特点有所了解,参加革命后,接受了共产党的教育,经过学习和自我思 想改造,更有深刻的切身体会。他觉得这位老中医没来参加座谈会事出 有因,不应过早地下结论。他打听了这位老中医的住处后,轻车简从,亲 自上门拜访。
当傅连暲敲开一座古老的四合院,报上了自己的名字后,这位年近 花甲的老专家心中一阵忐忑不安。虽然他近来很少出门,但他对新中国 的卫生工作还是了解一些,也听别的医生讲过。他知道傅连暲在不久刚 被任命为卫生部副部长,也可以说是中共的高级干部了。现在傅连暲突 然来到自己的住处,他既感到吃惊又有点惶恐,生怕出什么事情。
“部长光临寒舍,未能远迎,请……”他一下子来了一句过去的熟套 套 。
傅连暲不等他说完,就摆了摆手,接过他的话,亲切地说:“不要客 气,我今天不请自来,做了不速之客,还请先生海涵。”说话间,傅连暲也 学他的样子,把双手在胸前拱了拱。
两人落座后,老先生又问:“不知部长今天登门所为何事?”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事,只是慕老先生的大名,想拜访拜访,随便聊 聊。”
听到这里,老先生心里才安定下来,知道他不是兴师问罪而来。
闲聊了一会儿之后,傅连暲切入了正题:“北京刚解放,新中国成立 不久,现在千头万绪,国家正是用人之际,我们希望老先生能够出来帮 助工作。”
“我已经是年近花甲的老朽了,没有什么用了。”对方似有隐衷。
“先生身体还康健,正可以发挥你的影响,为新中国,为百姓出力。
我们党的政策你可能也了解一些,就是要团结所有的力量,建设强大的新中国,包括一切愿意贡献力量的人士。”傅连暲恳切地动员。
“我为许多国民党高级人士看过病,难道你们也放心吗?”老先生见 傅连暲没有一点架子,说话也诚恳,终于把心中的担心说了出来。
“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我们知道你的情况,不然就不会找你了,共 产党是信任你的。不管过去如何,只要今后为人民做事,就站在人民的 一边了。我在参加革命以前,也曾经给国民党地方军阀和当地地主豪绅 治过病,但一直都受到党的信任。我们希望你能把高超的医术贡献给人 民 。 ”
傅连暲的诚意,使这位老中医慢慢化解了心中的结,消除了顾虑, 十分感动,终于愉快地走上了工作岗位。
傅连暲从一个生活优裕的教会医院院长,甘冒风险献身于出生入 死的革命斗争,从一个基督教徒转变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这确实是鲜 见的。医学界里的许多高级知识分子,对傅连暲的经历都很感兴趣,很 多人喜欢倾听他的体验,希望从中得到启发。
而傅连暲作为党的高级干 部,能很好地贯彻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在他周围团结了许多医学专 家、学者。在党的政策感召下,经过傅连暲等卫生部门领导的工作,许多 著名的老中医都焕发了精神,参加到建设祖国的卫生事业之中。
北京中 医界的四大名医:萧龙友、施今墨、孔伯华、蒲辅周,都相继出山,并且与 傅连暲交往日深,成为好友。
当时,萧龙友因对旧社会不满,借医为隐, 把自己的住所取名为“息园”,别号“息翁”。解放后,他有感于共产党的 政策和诚意,又出来工作,并改别号为“不息翁”,虽然年已八旬,但老当 益壮。他们都为祖国中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1953年11月,中华医学会总会召开中西医学术交流委员会,借以推 动中西医学术交流和提高。傅连暲在会上说:“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人 数很多,与群众联系密切,为广大人民特别是农村人民解决了许多疾病 问题。中西医不仅在政治工作上团结,在学术上也要交流,互相帮助提 高,取长补短,更好地为人民健康服务。”
傅连暲支持选举著名中医彭泽民当委员会主任,他自己以卫生部副部长之尊,和萧龙友、孔伯华、施今 墨、赵树屏一同担任副主任。
委员会成立后,组织了多次中西医学术交流座谈会,座谈会一般由 中医主持,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先后讨论了大黄、半夏、黄连、常山、当 归、益母草、枯痔散等中药的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以及各种中医疗法, 取得很好的效果。
傅连暲对待医学专家、知识分子,总是信任有加,尽力保护,大胆任 用 。
有一位医学博士,当过国民党的军医官,为我所用后又出了一起医 疗事故,因此公安部门认定他是钻入革命队伍肆意搞破坏的反革命分 子。事情反映到傅连暲那里,他主张具体分析。傅连暲曾经和这个人谈 过话,了解到他原来出身清苦,在日本学医时受尽歧视,是靠个人努力奋斗,苦心钻研,才取得博 士学位的。他在国民党军队 医院工作,一直当医生,只 是埋头治病,没参与过任何 带有反动政治色彩的活动。
因此,傅连暲认为,这 样的人应该保护,让他发挥 专长,不应该定为反革命分 子。至于医疗事故,确实与 他有关,但不是政治事故, 而是责任事故,应该受到批 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这 个人后来一直在自己的岗 位上兢兢业业地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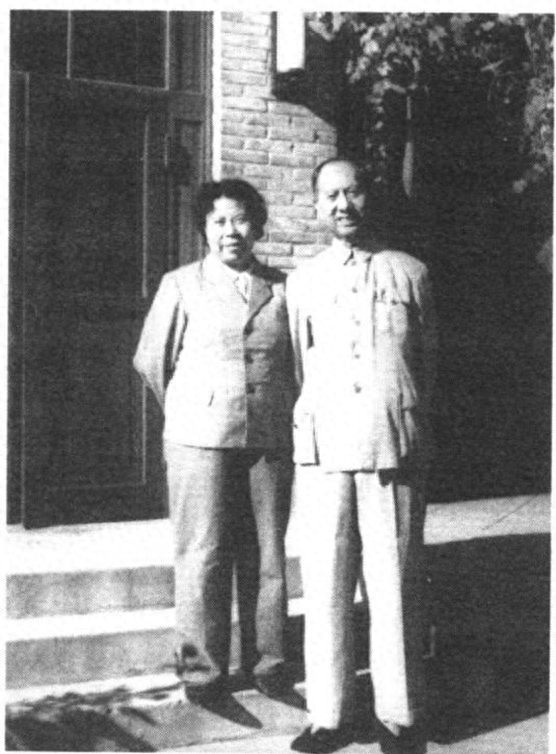
傅边暲70岁生日时与夫人陈真仁留影

1954年傅连暲与夫人陈真仁及女傅维芳、子傅维暲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