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权力有多种行使方式,其中刑法手段具有谦抑性,一般性的调整更多是通过民事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甚至还可能通过教育、宣传等非法律手段进行。
 国家何时应当用刑法维护共同善?
国家何时应当用刑法维护共同善?(一)犯罪与共同善
我将从犯罪的本质出发,阐述为什么严重贬损人类尊严这一侵害共同善的行为应当用刑法规制。

一般认为,犯罪首先是一种公共不当行为(public wrong doing),也就是说,一种道德不当行为,只有具备了公共性,才可能成为犯罪。
而对于公共性有两种理解方式:
一种是“受害人模式”,即当道德不当行为侵害了共同体的利益,或其行为表达了对共同体所珍视价值的蔑视时,共同体成为受害者,因此有权动用刑法进行规制和惩罚。

这种理解模式实际上将共同体等同于私法上的被侵权人,因其遭受侵害或侮辱而有权做出反应。
但这一解释与刑事法律制度的运作是冲突的:国家无权选择是否启动刑事程序,打击犯罪、启动刑事审判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司法机关的职责,而非权利。
也就是说,国家之所以动用刑法,不是因为其有权利选择这么做,而是因为其有责任必须这么做。

因此,作为公共不当行为的犯罪,只能被理解为应当由共同体负责惩罚的道德不当行为,而不是理解为针对共同体的不当行为。
这一定义实际上将我们引向了一种报应主义的刑罚观。
接下来的问题在于:第一,何种行为应受惩罚?第二,何种行为应由国家进行惩罚?

本文无法完整全面回答这两个问题,在此将结合“共同善”概念初步阐述,旨在说明为什么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应当由国家惩罚。
这里首先对惩罚下一个最大公约数意义上的定义:任何一种惩罚,都蕴含一定程度的道德谴责,并包含痛苦或其他通常被认为不利的后果。
本质上,惩罚是一种表达,即对公共不当行为的一种回应:

将被惩罚者隔离在共同善之外,使他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从共同善中建立完整人生规划从而实现个人福祉的机会,这种隔离是对他破坏共同善的恰当回应。
任何一个共同体的共同善都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是构成性的或第一性的,即任何良善生活都不可缺少的普遍性价值,缺少此种价值则共同体必然瓦解,个人福祉无法实现;

第二类是非构成性的或第二性的,即不影响共同体的存在,但对共同体有益的价值。
不尊重第一性的共同善的故意行为,通常都应当受到惩罚。
例如,夫妻忠诚是婚姻的构成性共同善,如果一方以出轨的形式表达了对该种共同善的不尊重,行为人就应当遭受道德谴责,并承受某种不利后果。

那么,何时应由国家负责任进行惩罚?
当某种公共不法行为严重到表达了对政治共同体有责任捍卫的重要价值的侵犯时,国家有责任对其进行惩罚,以表达对行为人的谴责和对共同善的捍卫。
而侵犯政治共同体构成性共同善的行为显然是严重的公共不法行为,因为其威胁了共同体的根基,损害了每个个体的福祉。

而根据之前对共同善的阐释,尊重人类尊严源自实践合理性的要求,是人类福祉的内在组成部分,更是任何共同体都必须遵守的第一原则。
因此,人类尊严属于构成性或第一性的共同善。
所以,严重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是对政治共同体之共同善的严重侵犯,国家有责任对其施以惩罚,将之隔离于共同善之外,以回应该严重公共不当行为。

(二)侵犯自主性(automy)?
1.拉兹的立场
对此可能有一种反对意见。
有学者认为,虽然国家有责任维护实质的人类善,辅助公民追求个人福祉,但基于对自主性价值的保护,不得使用刑罚手段干涉不会对他人产生实质性损害的道德不当行为。
例如侮辱尸体这一类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虽然是对共同善的严重侵害,但并未侵害任何人的自由和权利。

国家用刑法干预会贬损行为人的自主性,使之无法追求自身的福祉,因此是不正当的。
这种理论以自主性价值为基础,重构损害原则,反对法律道德主义,被称作至善主义的自由主义立场。
拉兹是这一立场的代表。

拉兹与德沃金的区别在于,他不反对甚至支持国家对个体道德生活的积极介入,但他主张这种介入应当是非强制性的,应当通过鼓励、教育、谴责等方式进行引导。
因此我们有必要仔细审视其论证。
拉兹认为,政府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人民过上追求人类福祉的生活。

之所以要防止损害,是因为伤害侵害了自主,而自主是人类福祉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自主唯有在追求有价值的目标时才是有价值的,这就要求政府积极作为,创造有价值的机会,减少无价值的机会,从而维护个体自主。
自主原则是一种至善主义原则,因此政府可以为了他人或某人将来的更重要的自主而证成对此人的强制,但同样基于对自主的保护,不能以其他理由对个体进行强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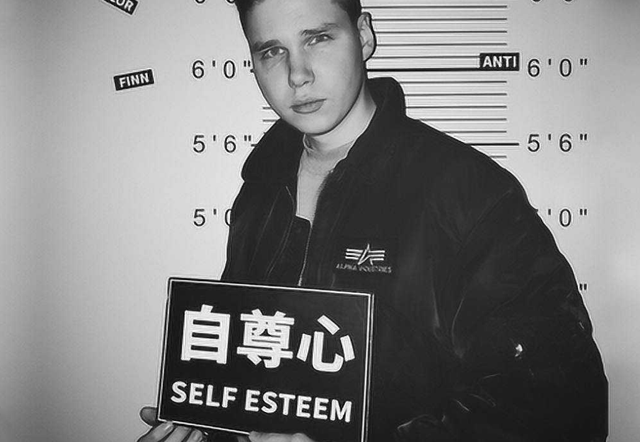
也就是说拉兹并不反对推行正当的伦理价值是政府的目的,仅仅反对以强制作为手段推行,因为这侵犯了自主的价值。
在拉兹看来,自主是人类福祉的内在组成部分,其体现的是这样一种理念:人应当是自己生活的创造者,在某种程度上掌控自己的命运,通过连续的决定塑造自我。
实现自主的价值需要满足三个条件:适当的心智能力、充分的选择范围以及独立性。

基于对自主的强调,拉兹的至善主义理论并没有倒向法律道德主义立场。
他认为,政府虽然应当努力维护良善的伦理环境,但不应当使用刑法手段,除非被强制者自身侵犯了他人的自主。
因为强制是将他人当作物的表现,是一种对待他人的不适当方式,损害了他人的独立性。

而独立性是自主的一部分,自主具备重要的内在价值,因此用强制手段推行无害伦理是不正当的。
据此,拉兹提出了基于自主的自由观,以自主价值作为伤害原则的基石,提出了伤害原则的修正版本。
在他看来,伤害原则的目的是保护人的自主,因此仅允许政府依据以下两种目的使用强制:一是防止对自主的侵害,二是强迫人们采取必要行动以增进他们自己的选择和机会。

就侮辱尸体行为而言,拉兹会同意国家有责任采取各种非强制手段帮助纠正行为人的道德错误;
但同时他会基于对个体自主的保护,反对将此类行为犯罪化,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自主才能限制自主,侮辱尸体行为并不构成对他人自主的侵害,因此国家不能够对其使用强制。
拉兹的观点与前述德沃金的观点有一定相似性,但相对而言更加温和。

一方面,拉兹承认国家的至善主义角色,反对的仅仅是强制的手段而非推行道德这一目的;
另一方面,他将自主归于人类福祉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独立于人类善的绝对权利,并将独立性作为自主价值的一个方面,这就降低了独立性的理论地位。
但他反对用法律推行无害道德这一观点决定了他的反法律道德主义立场。

2.对拉兹的反驳
我认为,拉兹的反法律道德主义立场存在重大缺陷,本文所阐述的法律道德主义立场更具备融贯性和理论说服力。
首先,拉兹对自主价值的论述是不融贯的。
拉兹一方面主张自主是人类福祉的内在构成部分,但另一方面又认为自主是一种工具性价值。

只有当人们致力于追求可接受的和有价值的目标和关系时,自主的生活才是有价值的,也就是说,当自主无助于人类福祉的实现时,自主本身并不值得追求。
出现这种矛盾的根源在于,拉兹一方面坚持至善主义理论基础,认为国家应当致力于促进人类福祉,一方面又想捍卫自由主义的信念,担心国家过度干预。
但这样反而削弱了其理论的论证力度。

可以确定的是,既然拉兹理论的根基是客观的人类福祉,那么当一种自主选择的生活不能促进人类福祉的实现时,自主必然是无价值的。
如果自主具有内在价值,那么就意味着自主能够成为独立的规范性行动理由,但显然自由选择本身不能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实质性的指引。
罗伯特·乔治(RobertGeorge)指出,拉兹实际上是混淆了自主和实践合理性。

后者才是人类福祉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客观的基本善,自主仅仅是实现实践合理性的一个条件,不具备内在价值。
前文已述,在自然法传统中,实践合理性就是个体运用理性去决策、选择生活方式、塑造个人性格的状态。
实践合理性本身就是基本善之一,是人类福祉的一部分,能够成为独立的行动理由。

可见,如果拉兹的自主指的是具有强规范性的实践合理性,那么在很多情形下,对选择为恶的个体进行强制就不侵犯个体的自主性。
因为这些恶行多半违反“在每一行动中尊重每一基本价值”这一要求;
如果拉兹的自主指的是“自由选择”本身,那么他就不能融贯地主张自主具备内在价值,能够作为伤害原则的基础。

第二,对伦理不当行为进行法律强制不一定侵犯自主。
这一理由与前文反对德沃金的第二个理由是一样的。
法律不可能保护任意的选择,因此一个合理的自主概念不能等同于自由选择本身。

而要充实自主的概念,必然会倒向“实践合理性”这一概念,而实践合理性允许对一些伦理不当行为进行强制。
前文已述,此处不再重复。
因此,拉兹基于自主性价值的反法律道德主义论证是失败的,一种融贯的至善主义理论必然支持法律道德主义。

也就是说,拉兹混淆了自主与实践合理性,前者本身不具备内在价值,而是实现后者的一个条件,不能成为独立的行动理由。
因此,不能以尊重自主为由反对以刑法这一强制性手段回应严重贬损人类尊严的道德不当行为。
由于严重贬损人类尊严的行为违背了实践合理性最根本的要求,动摇了人类生活的根基,严重侵害了共同善。

因此国家有责任对之施以惩罚,将行为人隔离于共同善之外,以表达对此类严重道德不当行为的回应。
 结论
结论本文论证的重点在于说明只有借助新自然法理论框架才能为侵犯人类尊严行为的入刑提供最佳辩护,进而捍卫法律道德主义犯罪化命题。
在当代,大多数理论家都认可人类尊严的根本重要性,但什么是人类尊严的规范性本质,如何尊重和捍卫人类尊严,仍然存在较大争议。

本文提出,在对贬损人类尊严行为的犯罪化问题上,我们会在两个层面遭遇人类尊严:
第一个层面的问题是,侮辱尸体行为本身是否侵犯人类尊严;
第二个层面的问题是,即使第一个问题成立,将侮辱尸体行为犯罪化本身是否贬低了行为人的尊严,损害了其伦理独立性。

只有当第一个问题回答“是”而第二个问题回答“否”时,侵害人类尊严的行为才能被正当犯罪化。
自由主义虽然在第一个问题上可能给出肯定回答,但由于其固守国家中立原则或自主性价值,在第二个问题上亦会持肯定立场。
因此无法解释侮辱尸体罪的正当性,本文通过对德沃金和拉兹理论的分析与反驳说明了这一点。

当然,自由主义者可能声称,人类尊严是一个例外,由于人类尊严是如此基础和重要,即使无法依赖于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亦能够将侵犯人类尊严的行为正当犯罪化;
或者进一步主张自由主义原则上就不受限于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
但问题在于这一主张如何在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下得以融贯解释。

自由主义者如果试图捍卫侮辱尸体罪的正当性,又不诉诸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则势必主张一种较为厚实、蕴含了较高道德要求的合理性观念。
认为由于某些道德不当行为具备高度的非理性,因此对其施加干涉并不损害其伦理独立性,而这将导致自由主义自身立场向至善主义的倾斜。
也就是说,此时的自由主义实质上已经成为一种法律道德主义,法律道德主义者将很乐意看到这一结果。

或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范伯格这一典型的自由主义理论家方才固守损害原则和冒犯原则,明确反对将私下的侮辱尸体行为犯罪化。
与之相对,新自然法理论明确主张人类尊严是实践合理性这一基本善的内在组成部分,因此属于最重要的共同善。
而在国家权力边界问题上,持鲜明的至善主义的立场,主张国家可以采用包括强制手段在内的各种方式辅助和引导个体的道德观念,以维护和促进共同善。

因此,基于新自然法理论的法律道德主义最为融贯和合理,可以避免自由主义面临的内部不一致性难题,是一种最佳的法律道德主义形态,从而为侮辱尸体罪提供正当性基础。
在证立侮辱、毁坏尸体罪的同时,法律道德主义也为侮辱、毁坏尸体罪提供了规范性的认定标准,提高了入罪的门槛。
该罪针对的是对人类尊严严重贬损的行为,也就是说,该行为必须能够体现行为人贬损人类尊严的态度。

因此,有些行为,表面上符合毁坏尸体罪的主客观要件,但却是由当地特殊丧葬风俗所致,体现了对死者的尊重,则不成立本罪。
例如西藏部分地区存在天葬习俗,依其宗教观将尸体放置于空地上任鸟啄食。
若行为人出于尊重死者的理由采取此类行为,则不成立侮辱、毁坏尸体罪(当然这在具体案件中要经过非常复杂的认定和推理)。

但这并非是说要成立本罪必须基于明确的贬损人类尊严的目的,只要行为人有意对尸体进行侮辱和分解。
同时并非基于任何正当理由,就是对尸体所象征的人类尊严的蔑视,应当入罪。
最后要说明的是,有一种反对意见认为,主张法律道德主义会危害思想自由,导致专制,成为统治者强制推行自身价值偏好、干涉公民生活的借口。

这是不成立的,第一:法律道德主义并不主张惩罚思想,而只惩罚对共同善严重侵犯的公共不当行为;
第二,法律道德主义要求在推行道德时对相应的善和道德规范进行实践理性推理,只有通过实践理性推理证成的道德真理才可能被推行。
同时,还需要与其他价值与规范进行权衡,并非认为各类道德都应当被强制执行。

可见,法律道德主义是一种合乎中道的主张,捍卫一种温和的有限政府观念。
因为其一方面反对对国家的权力界限施加一种过于狭窄的限制,另一方面主张公民的自由仍然是国家在考虑法律强制时的一个重要权衡因素。
同时,法律道德主义要求任何国家行为都必须为自己进行理性辩护,只有在前提为真且论证有效的情形下才能使其行为正当化。

综上,本文结论是,损害原则与冒犯原则不足以穷尽一切犯罪化正当依据,以共同善为核心建构的法律道德主义立场能够被证立,并能为侮辱尸体罪提供充分的辩护。
公众对于侮辱尸体罪深思熟虑的判断,最终得以与尊重人类尊严这一抽象的道德原则达成一致,实现直觉与抽象原则之间的反思平衡。

